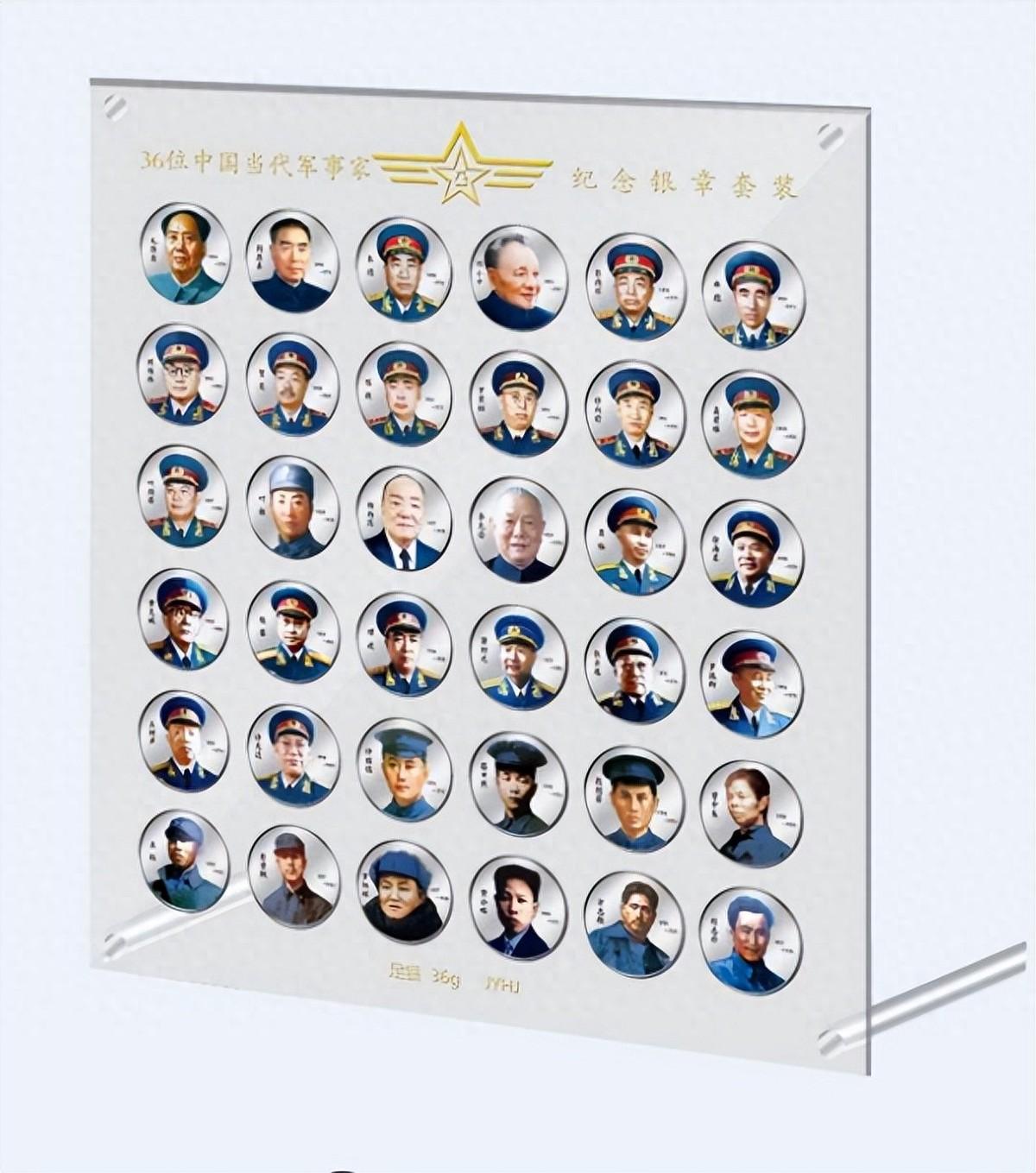这位开国上将,55年授衔后长期不受重用,混的还不如一些中将少将 1955年9月27日晚,北京西郊。授衔仪式刚结束,灯火照着王建安胸前的新肩章,金星熠熠,他却没露半点兴奋。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的军旅道路并未因这颗星而坦途。 王建安出身湖北黄安,小学没毕业,却凭着偷听私塾读书认得不少字。1926年大革命浪潮最汹涌的时候,他误投吴佩孚的部队,很快发现军阀世界与“救国”二字相去甚远。两个月不到,这位脾气直的汉子扔下步枪,回乡拉起六十名庄稼汉搞自卫队。中共鄂东特委得知此事,派人去谈,三杯苞谷酒后,一份入党誓言在油灯下写下。 参加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连番恶战,王建安从班长升到团政委,用的是一股不要命的冲劲。1933年,他兼任红三十八军八十八师师长和政委,连打几场硬仗,把国民党“六路围攻”撕开口子,被前方指挥部称作“能打也会管”。 转折在1937年。中央清算张国焘问题,波及不少人。许世友因“红四方面军系”背景被指责,怒而欲走,王建安差点与他一道翻山。关键时刻,他写信给中央检讨。自此,两人心生嫌隙。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后,他们又被派去同一战场——同桌吃饭,谁也不先开口。毛泽东后来打趣:“让他们在枪声里磨合,比坐办公室吵架强。” 1948年初夏,解放济南前夕,王建安已在前线画作战图。许世友赶到,抬眼看见他,沉默片刻,只说一句:“干这一仗再算账。”最终配合默契,用十天攻克济南。淮海战役里,王建安与谭震林围堵杜聿明集团,纵横千里,三野首长把歼灭战的“收口”任务交给他,硬是堵得敌军插翅难飞。 抗美援朝时,他任志愿军九兵团政委,驻防东海岸高地。1953年美韩夏季攻势,九兵团伤亡剧增,他直接出现在前沿指挥壕,一声“跟我上”,把动摇的火力点重新顶住。那一年他才42岁。 然而回国不久,“高饶事件”掀起波澜。王建安曾和饶漱石在根据地日夜并肩,被列入排查名单。组织没给定性,却把他调到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实际权责受限。很多人纳闷: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为何只在副职转悠? 更尴尬的是1964年到1973年。几位同龄的中将、少将陆续进了大军区正职,王建安却连手头的副职权限都被层层削弱。有人打趣:“老王的星星亮,坐的椅子矮。”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只是摆手:“少说闲话,好好干活。”一句话,没半分抱怨。 1975年秋,中央军委顾问会议。叶剑英握住王建安的手说:“这些年你不计得失,难得。”很多年轻干部听成了表扬,但老人们心知肚明,这是对一段被埋藏往事的注脚。王建安没多解释,只举杯敬老帅,笑着说:“我是党的人,往哪儿放都能发芽。” 进入八十年代,王建安被调到中央纪委,负责军队系统纪律检查。他办的第一起大案,牵涉某军级单位走私汽油,涉案人员错综复杂。有人劝他“别太较真”,他一句冷飕飕的回击:“纪律松一分,部队垮一寸。”案子查清,四名师职军官被开除军籍,震动不小。 1984年退居二线时,王建安已满73岁。告别仪式很简单,没有列队,也没有军乐。他提着笔记本回黄安旧居,把几十年作战心得整理成12万字手稿,只写战术、政工,不谈个人得失。他坚信,历史自有评判。 有人说他坎坷,有人替他不平。可在老兵眼里,王建安始终还是那个不怕死、不抬价的火线汉子。至于官大官小,他自己早看淡——在枪林弹雨里抱过炸药包的人,最明白什么才是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