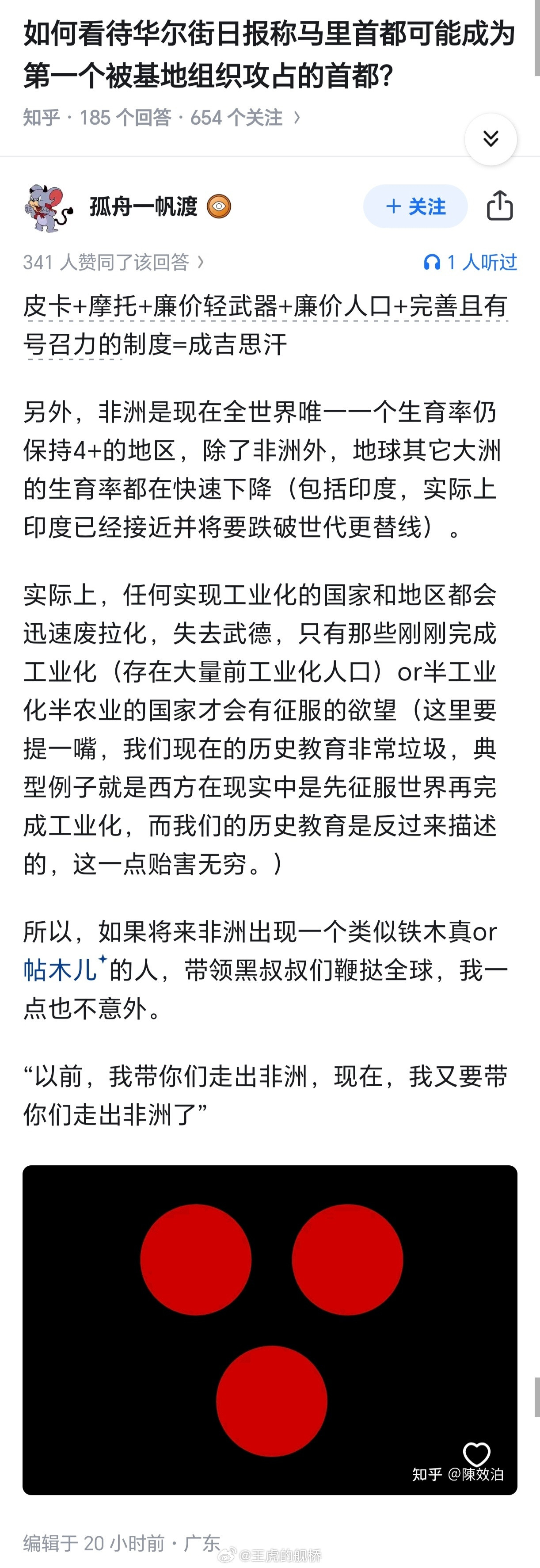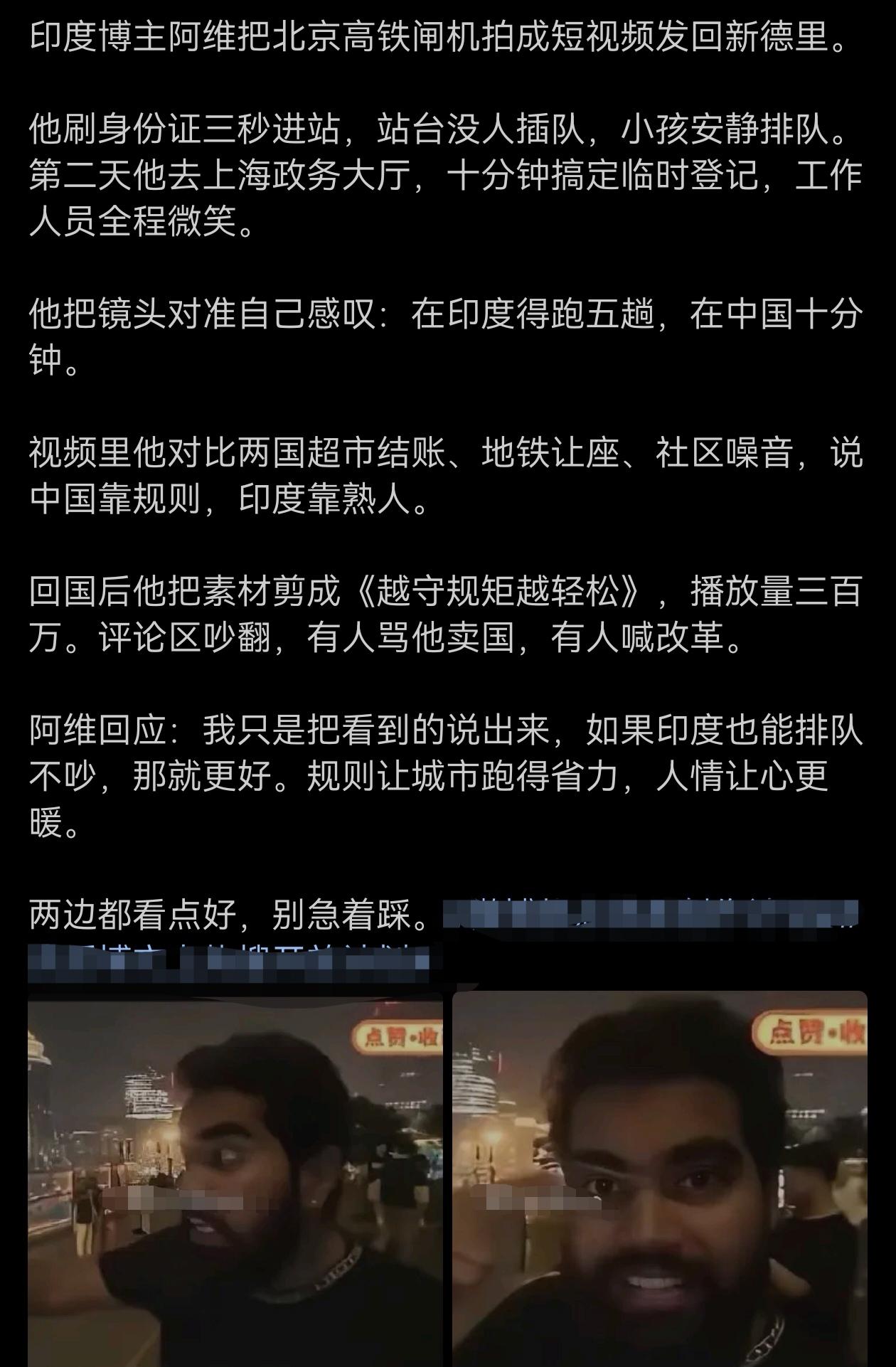李显龙在新加坡当了20年总理,如今以国务资政身份去伦敦开会,直接放话:中国老了,印度经济未来可能超车。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背后是新加坡和印度越走越近的现实。 李显龙的讲话中,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他提到的“老龄化”和“年轻人口”。他说,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可能会受到制约。 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早已不是纸面上的预测,而是正在深刻影响经济运转的既定事实。 2024年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10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22.0%;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更是突破2.2亿,占比达到15.6%。这组数据已经远超联合国划定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正式迈入新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更能直观反映人口红利的消退轨迹。2024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5798万人,占比60.9%。这个比例比十年前下降了近8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曾经,中国靠着充足且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核心承接地,“世界工厂”的称号背后,正是庞大的人口红利在提供支撑。 如今,这种支撑力的减弱已经在部分行业显现,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劳动力成本更低、人口结构更年轻的东南亚及南亚国家转移,李显龙敏锐捕捉到这一现象,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判断中。 李显龙拿印度的人口结构做对比,这番对比看似直接,却精准点中了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一个热点。印度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超8亿,这个数字比中国同年龄段人口多出近千万。 更值得关注的是,印度35岁以下人口占比超过65%,这样的人口结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都十分少见,构成了潜在的人口红利储备。 但人口红利从来不是“人多就行”的便宜事,这一点李显龙没明说,却藏在他“可能超车”的表述里。 “可能”两个字的背后,是印度当下绕不开的短板。2025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印度那8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真正实现正规就业的比例还不到45%。剩下的劳动力要么挤在没保障的非正式岗位,要么处于隐性失业状态。 更关键的是,印度的技能培训体系有明显缺口,仅有不到20%的年轻劳动力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而中国这一比例早已超过80%。这意味着印度大量年轻人口目前还只是“人口资源”,没能转化成支撑高端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 李显龙敢在伦敦公开为印度“站台”,核心原因是新加坡和印度之间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早已不是外交辞令里的“友好伙伴”,而是落实在一笔笔投资、一个个合作项目里的利益捆绑。 新加坡是印度在东盟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这一地位在2024-25财年进一步巩固,新加坡占印度与东盟十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7.83%,在区域合作中扮演着关键枢纽角色。 投资领域的数据更能说明双方关系的深度。过去二十五年,新加坡对印度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748亿美元,占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接近24%,连续多年稳坐印度最大外资来源国的位置。 2024年8月,印度和新加坡在新德里开了第三届部长级圆桌会议,印度外交、商工、财政等多位核心部长集体出席,和新加坡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带领的代表团深入沟通,议题涵盖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化等关键领域,足见双方对合作的重视。 没过多久,印度商工部在2024年9月放出了一个标志性动作。印度计划在全球多国开设投资促进办事处,首个机构就选在新加坡落地。 印度商工部长高耶尔说得很明确,新加坡办事处会成为东盟企业投资印度的专门联络点,为跨国合作提供精准服务。他直言,这一步是印度加强和新加坡及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双方合作从高层对话落到了企业服务的实处。 新加坡这么看重印度市场,本质是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新加坡国土小、资源少,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全球贸易和区域枢纽地位,马六甲海峡的航运安全更是它的经济命脉。每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货轮里,有60%都在为中国运货,这种高度依赖让新加坡一直有战略顾虑。 一旦中国在能源、制造业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程度的自主可控,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降低,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货轮数量可能会减少,新加坡的枢纽价值就会受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扶持印度成为区域经济新力量,就成了新加坡平衡区域格局的重要办法。李显龙在伦敦的发言,本质是一场面向全球的“战略喊话”:既向国际资本传递“印度有投资潜力”的信号,也鼓励印度更积极地参与区域事务,从而形成对中国的制衡。 这种制衡能让新加坡在中美印三角关系中获得更大的周旋空间,继续保持“左右逢源”的枢纽地位,这正是小国生存智慧的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