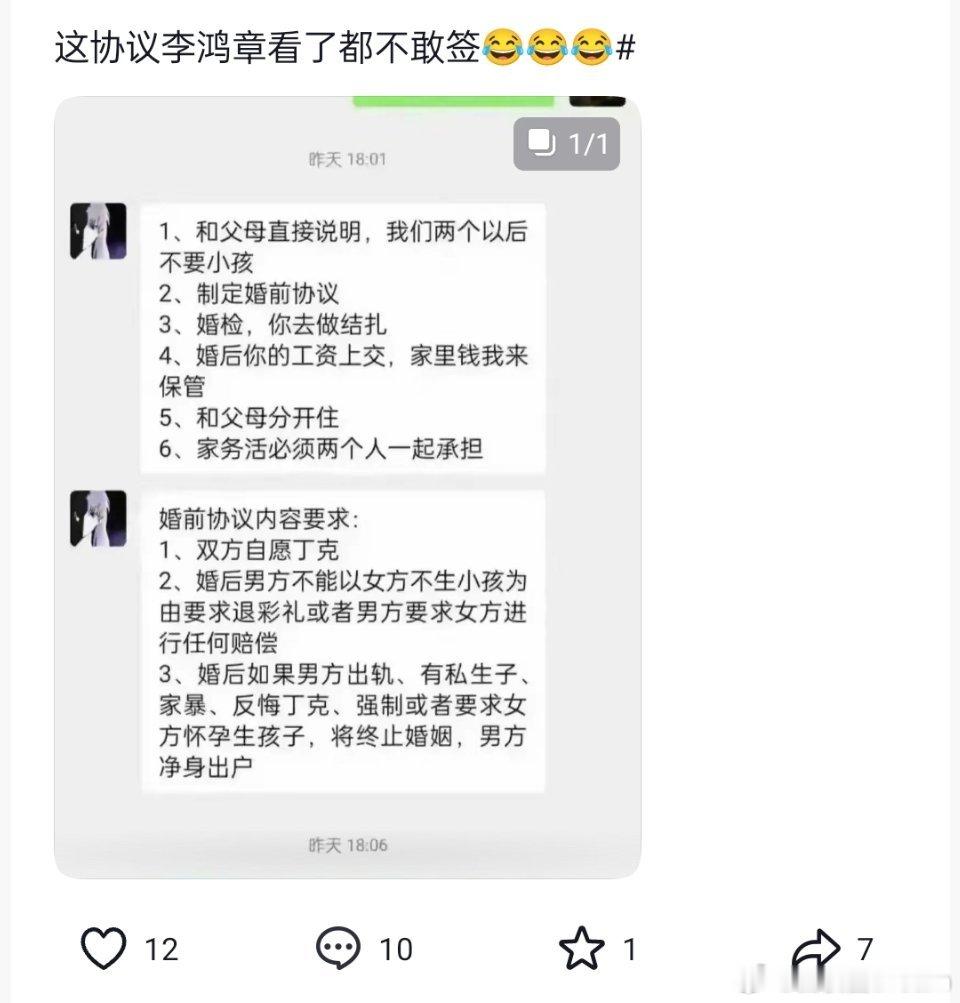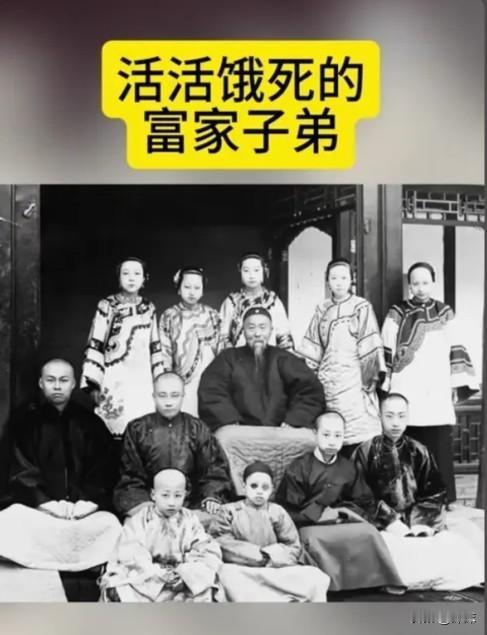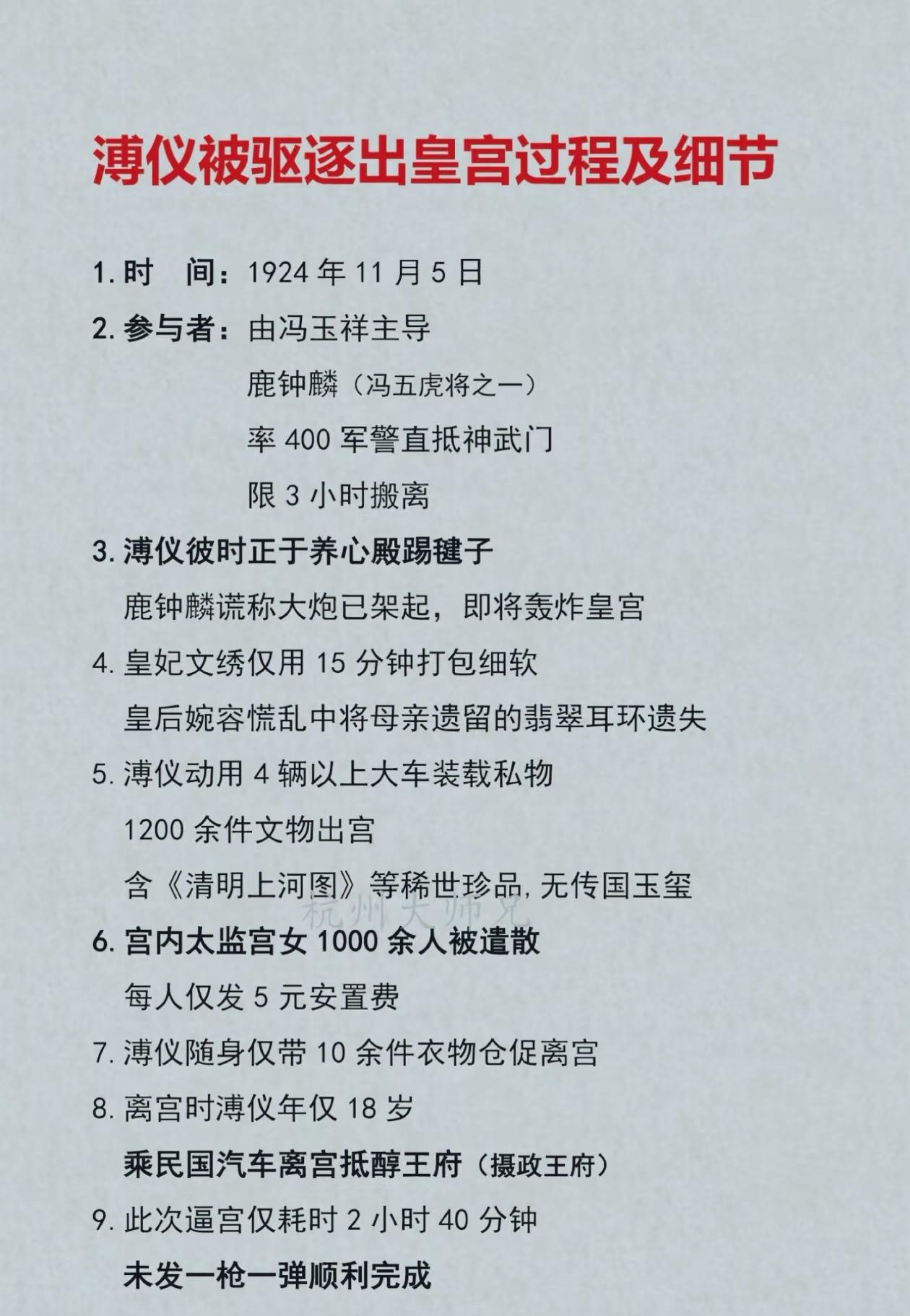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给子孙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没想到,52年后,他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竟因为穷得买不起食物,活活饿死了,死后,他的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草草埋葬了事。 根据清末留学先驱容闳的记载,这笔私产高达4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换算到现在至少价值300亿人民币。 这些钱可不止是码在银库里的现大洋,更多是扎在各地的实业根基——安徽、江苏两省的良田连成片,光安徽境内就有三万多亩;上海公共租界的石库门洋房占了半条街,南京夫子庙旁的商铺、当铺半数挂着李家招牌;天津、武汉的钱庄握着流通命脉,漕运线上的货船首尾相接,连宫里流出的官窑瓷器、历代名人字画都塞满了十几个库房。 长子李经方作为主要继承人,分到的更是精华中的精华,上海静安寺路的三层洋楼带着两个足球场大的花园,安徽芜湖的万亩良田每年收的租子能堆成银山,苏州还有一片茂密的山场,更别提南通大生纱厂的股份、武汉码头的栈房。 这些家底足够让他这辈子衣食无忧,可他对1910年出生的独子李子嘉,硬是宠成了不知人间疾苦的纨绔。 李经方是老来得子,妻子是一位英国人,这种欢喜让他对儿子有求必应,李子嘉住洋楼、穿西装,从小跟着洋人教英语和马术,零花钱装在雕花檀木盒里任他取用,买条西洋猎犬花的钱够寻常百姓过三年安稳日子,他不用学管家业,不用懂谋生技能,唯一的“功课”就是怎么把钱花出去,一身少爷病被养得根深蒂固。 16岁那年,李经方撒手人寰,葬礼上李子嘉还披着麻戴孝哭唧唧的,转头就从家里牵出英国猎犬,揣着一叠银票闯进了上海的赌场,第一次上桌就赢了几百两,他觉得这钱来得比收租还容易,从此赌场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白天在“大世界”赌坊里推牌九,晚上就去“长三堂子”找花魁消遣,为博美人一笑,当场拍出3000大洋买下整条街的烟花,夜空亮得跟白昼似的,管家跪着求他收手,他却嗤笑一声:“我李家缺这点钱?”连后来染上花柳病,双腿溃烂流脓,都让人抬着轿子去赌,纱布渗血染红椅垫也浑不在意。 成年后掌家,他更是把糟蹋家底的本事发挥到极致,芜湖临江别墅雇了二十多个佣人,还养着专属戏班,每天晚上摆流水席请人听戏,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赌瘾越来越大,跟上海滩的流氓大亨对赌时,一夜间输掉芜湖十里洋场的产业眼睛都不红,转头又扛着家里的古董字画去当铺换钱接着玩。 赌场的刺激还填不满空虚,没多久又沾了鸦片,家里专门辟出烟房,天天躺着吞云吐雾,身体垮了不说,家产败得更快,母亲痛斥他,他竟嘴硬说“我有田有房饿不死”。 1937年淞沪会战打起来,上海的名流富商纷纷打包金银细软往内地逃,李子嘉却留在日占区里照样豪赌,日本人占了他的洋楼,他就搬到鸦片馆暂住,用最后一点家底跟汉奸、鬼子赌钱,赢了就接着抽鸦片,输了就卖身上最后一件值钱东西。 这时候他早把田契、房契偷出去抵押光了,族中长辈气得联名登报跟他断绝关系,母亲彻底心寒,带着最后一批珠宝返回英国,临走前丢下一句“你连你祖父一根头发都比不上”,唯一陪伴他的姨太太,也趁他睡着卷走最后三根金条和翡翠镯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喃喃自语,才明白钱比人走得还快。 到1948年,38岁的李子嘉成了芜湖街头的“三无人员”——没房子住,没一分存款,更没正经营生。身上衣服补丁摞补丁,鞋子露着脚趾头,只能靠捡烟屁股、讨饭过活,曾经的锦衣玉食全成了过眼云烟,走投无路时,他想起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厚着脸皮找上门求助。 左巨生自己也不宽裕,只能偶尔给口剩饭剩菜,让他不至于立刻饿死,1953年的寒冬来得特别早,芜湖街头飘着冷雪,没人注意到蜷缩在破庙里的李子嘉已经没了气息。 43岁的他,终究还是因为买不起食物,在饥寒交迫中咽气,死后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没有,邻居看不过去,找了张破草席裹住他的尸体,抬到城外乱葬岗,找个空旷地方草草埋了,连块刻名字的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