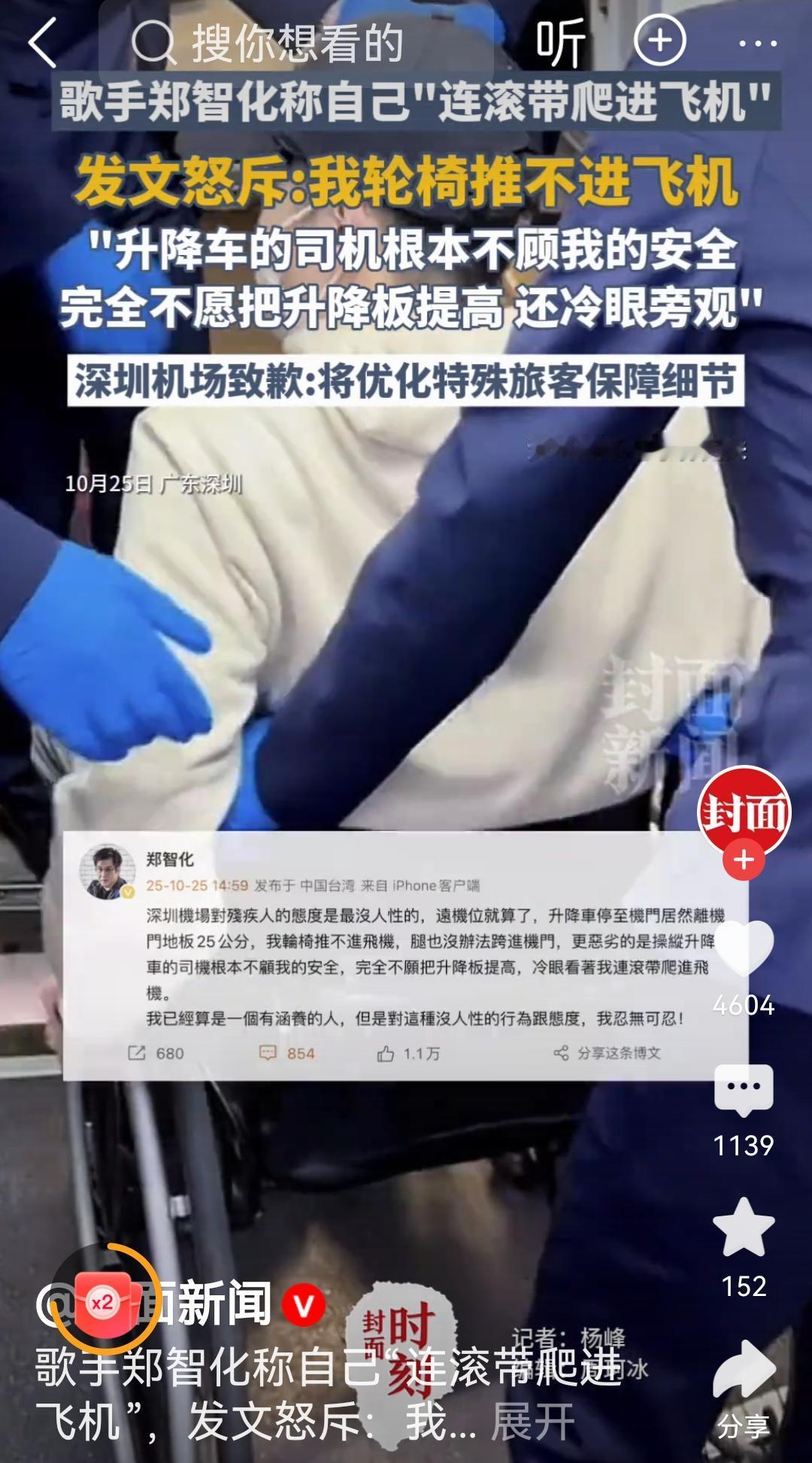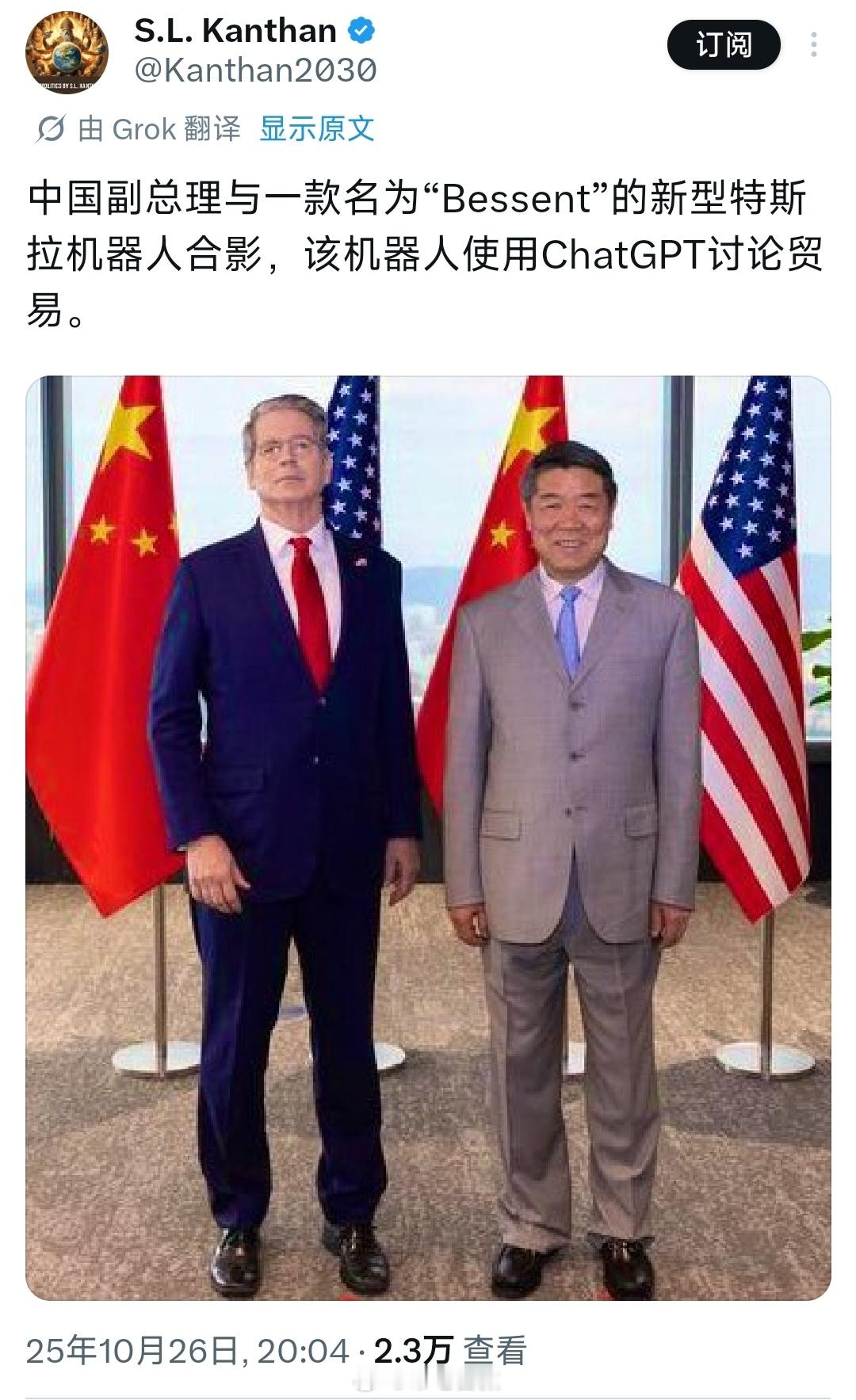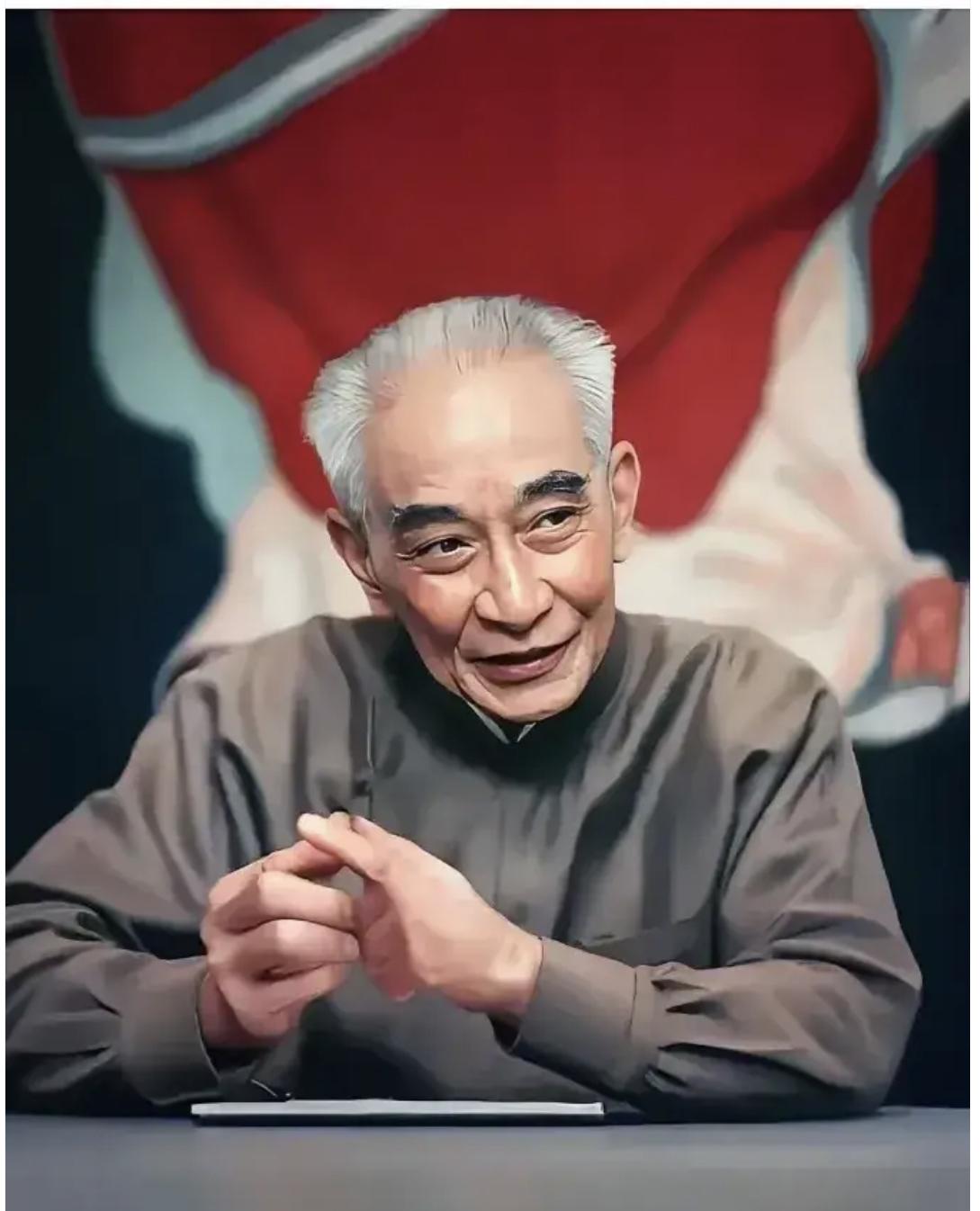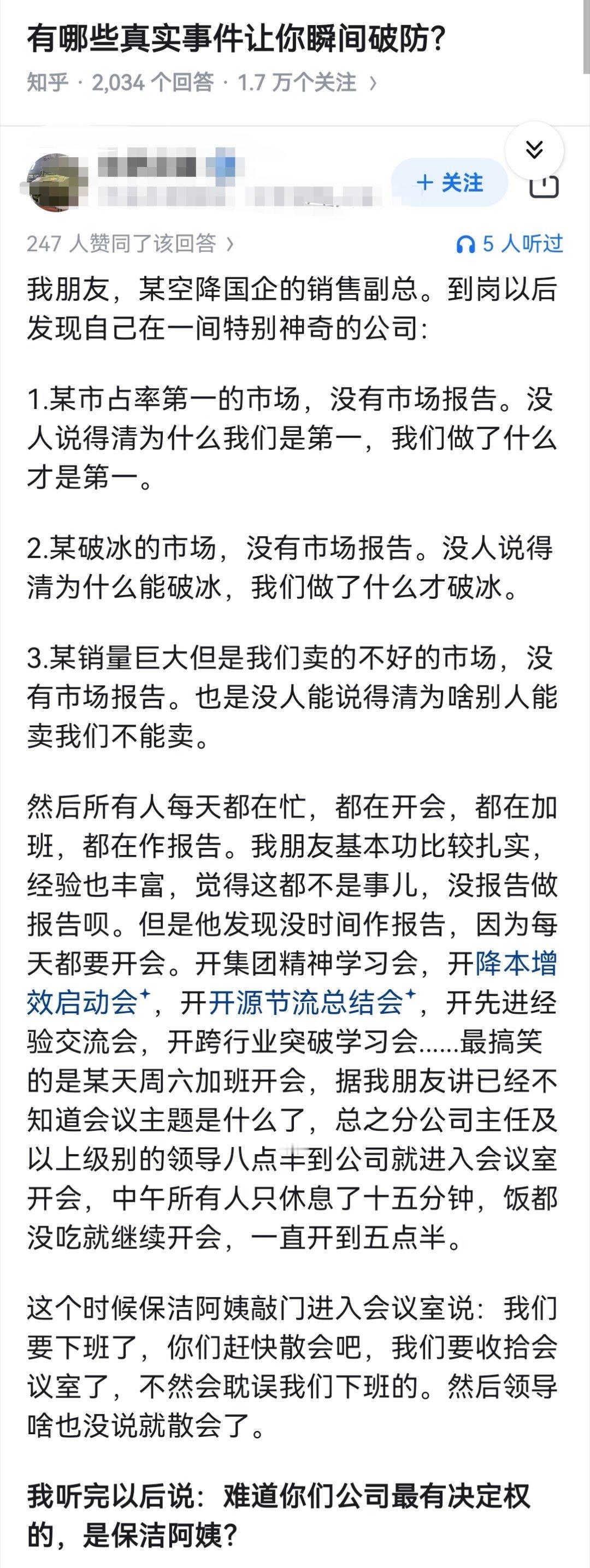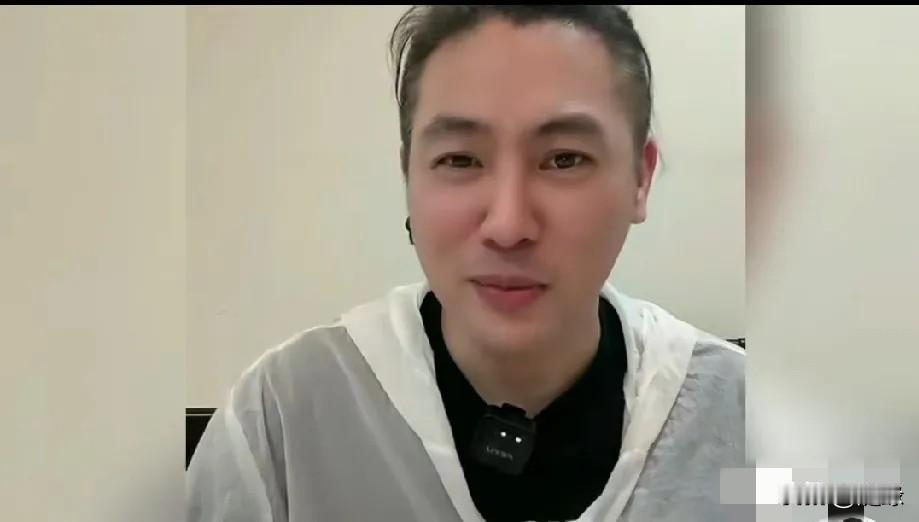那个被“世界第一美少年”毁掉一生的人,走了 伯恩·安德森,伦敦少年印象 这个被困在1971年威尼斯镜头里的男人,终于不用再带着那张“惊世骇俗”的脸,和全世界的凝视较劲了。享年70岁,对他来说,或许更像一场迟到半世纪的解脱。 说起来,他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带着股残酷的讽刺。1970年,15岁的伯恩还在瑞典街头帮人送报纸,因为一张路人拍的照片,被导演维斯康蒂从3000个少年里揪了出来。没人问他想不想当演员,只盯着他那双“像浸了月光”的眼睛,还有侧脸线条——后来我们都知道,这成了《魂断威尼斯》里的塔齐奥,成了“世界第一美少年”的开端。 可美这东西,在他身上从来不是礼物,是枷锁。拍电影时,导演不准他跑、不准他晒太阳,怕“破坏了美的形态”;试镜时被要求脱衣服,理由是“要确认身体线条配得上角色”。电影一上映,更疯了——伦敦首映礼上,女王盯着他看了半分钟,媒体的闪光灯能晃瞎眼;去日本宣传,粉丝追着他剪头发当纪念,经纪公司逼着他一天赶七场活动,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最恶心的是谣言。因为导演的情人嫉妒他,到处说他“吸毒成瘾”“车祸身亡”;1976年他卷入一场谋杀案,明明是证人,却被媒体写成“嫌疑人”,理由是“这么美的人,肯定不清白”。就这么着,欧洲影坛的门,对他彻底关上了。 没人关心他本来是谁。他5岁没了爹,10岁妈自杀,跟着亲戚长大,送报纸时最大的愿望是“能有个自己的小房间”。可“美少年”的标签一贴,谁还听他说这些?他试着蓄胡子、晒黑,想把那张脸藏起来,结果被人说“自甘堕落”;去剧院当清洁工糊口,被认出来后,人家笑他“可惜了这张脸”;后来他学钢琴,录了日语专辑,可听众还是只盯着封面,没人在乎他弹得好不好。他后来在采访里说:“如果早知道拍那部电影要付出这么多,我宁愿一辈子送报纸。” 命运对他的狠,还不止这些。1986年,他9个月大的儿子突然没了呼吸,医生说是婴儿猝死综合征。他抱着孩子的尸体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后来妻子跟他离婚,他开始酗酒,把自己关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公寓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世界还在谈论“塔齐奥”,可他连活下去的力气都快没了。 好在晚年总算松了点劲,甚至悄悄捡回了曾经被夺走的“热爱”。2004年,瑞典本土导演找他拍《邪恶》,没让他演美男子,而是给了个戏份不多的“校工”角色,穿粗布衣服,脸上带着生活磨出来的糙感。他后来笑着说:“第一次有人没盯着我的脸,只问我‘这个角色你想怎么演’。”那部电影后来拿了奥斯卡提名,他没去走红毯,只在首映礼后台给工作人员递了杯咖啡,像个普通剧组职员。 除了演戏,他还把钢琴变成了生活的锚点。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社区中心,他每周三下午会教三个孩子弹琴,其中有个失明的小姑娘,他会握着孩子的手慢慢找琴键,嘴里哼着瑞典老歌。有邻居拍过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毛衣,头发乱糟糟的,和孩子凑在钢琴前笑,完全看不出“世界第一美少年”的影子。他还重新录了音乐,2018年出了张纯钢琴EP,封面是自己拍的窗外雪景,没印名字,只写了“给冬天的歌”,最后只在小众音乐平台上发了,没做任何宣传。 2020年,有记者在威尼斯偶遇他,他跟着一群年轻人在巷子里逛,手里拿着甜筒,脚步慢悠悠的。被问起重回这里的感受,他指着《魂断威尼斯》里曾取景的酒店说:“以前觉得这地方像监狱,现在看,阳光挺好的。”那天他没聊过去,只说最近在学陶艺,捏了个歪歪扭扭的杯子,打算送给教钢琴的小姑娘。 今天再看《魂断威尼斯》的片段,还是会被少年塔齐奥惊艳——海风掀着他的白衬衫,回头一笑,连阳光都软了。可现在再看,心里多了点疼:那不是什么“美的化身”,是个15岁的孩子,被强行推到聚光灯下,用一生偿还了那几分钟的惊艳。 伯恩走了,这下他终于不用再被那张脸困住了。以后再有人提“世界第一美少年”,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个头衔背后,是一个男人一辈子的挣扎——他曾被美摧毁,最终却用自己的方式,找回了比美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