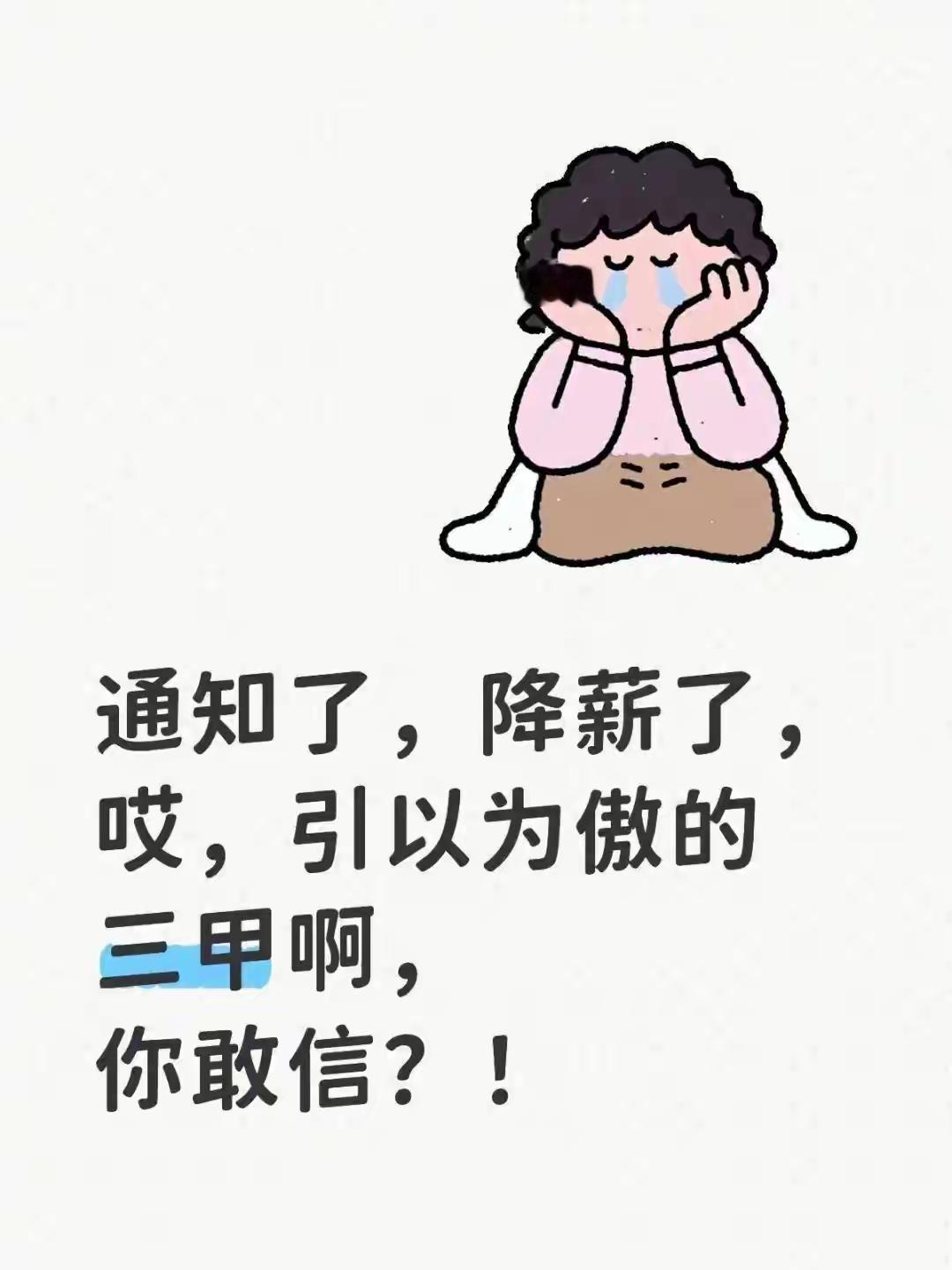同门二叔得了脑淤血,在icu抢救了7天,二婶做主不治了,前天拉回了家,看样离走没几天了。 二叔今年58岁,两口子开了个五金店,前几天整理货时倒在了货架前,抢救了7天没有好转。 没人知道二婶这个决定是怎么熬出来的。二叔和她开这家五金店快二十年了,当年两人从国营厂下岗,攥着凑来的八千块钱盘下这个小铺面,货架都是二叔自己焊的。 这几年网购冲击得厉害,散客越来越少,夫妻俩全靠给周边老住户上门修水电、换锁芯补贴收入,店里的货压着大半积蓄,账户里常年就几万块周转金,那是给老母亲买药和应急的钱。 二叔倒下那天,二婶正在给客户配水管零件,听见货架倒塌的声响跑过去,人已经趴在一堆螺丝刀和水管中间,脸憋得发紫。送医路上她手一直在抖,反复摸口袋里的银行卡,那里面是刚收的工程款,不到两万块。 ICU的门槛一跨进,每天的费用清单就像石头砸在心上,7天下来,刚凑的十万块眨眼见了底,其中三万还是跟外甥借的。 医生把话说得很实,不光是初期的三四十万,真成了植物人,后续的护理、康复、并发症治疗都是无底洞。 有医院做过统计,这类患者后期每年的费用能到几万甚至几十万,护工费、康复器械、抗感染药物,哪一样都省不下。二婶托人问过,就算有医保报销,自费部分也不是她家能扛的,五金店那点利润,连房租都快覆盖不住了。 那些天,二婶白天守在ICU外,晚上就去店里收拾,货架上的零件还按二叔的习惯摆得整整齐齐,最上层的灯泡是上周刚进的货,他说年底前肯定能卖完。 她试着给远在外地的儿子打电话,刚说两句就掐了,孩子刚工作还着房贷,不能让他背上这笔债。亲戚们来了几个,有人劝她再想想,说“钱能借,人没了就回不来了”,可没人真的把钱递到她手上。 她不是没犹豫过。有天医生提了句“脊髓电刺激促醒手术”,说能降点费用,可那也得一万多,关键是医生补了句“二叔这种情况,就算促醒成功,也大概率留后遗症”。 她趴在ICU的玻璃上看了半天,二叔浑身插着管子,监护仪的声音滴滴答答,没有一点要醒的迹象。 她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二叔修完水管回来冻得发抖,说“等攒够钱就关店,带你去南方住几天”,那笔钱,到现在也没攒够。 决定放弃的那天,二婶在医生办公室签了字,手劲大得笔尖都断了。她没跟任何人吵,只是把二叔的换洗衣物叠得方方正正,跟护士反复确认“拉回家不会疼”。 有人背后说她心硬,可没人知道她夜里抱着二叔的旧工作服哭,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修水管时客户给的几颗糖。 这根本不是“孝不孝”的选择题,是普通家庭撞在医疗现实上的无奈。医生在日记里写过,面对重症,家属要在尽孝和理性间找平衡,可对二婶这样的家庭来说,平衡早被钱和预后压垮了。 医学能延长生命,却填不满普通人家的钱包,更给不了百分百好转的承诺。那些喊着“砸锅卖铁也要治”的人,多半没体会过砸了锅也凑不够钱的绝望。 把二叔拉回家那天,街坊邻居都来帮忙,有人给搭了临时的床,有人送了热水壶。二婶坐在床边,给二叔擦了擦手,轻声说“店里的货我会慢慢清,你别操心”。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货架的零件上,亮得晃眼,可那个总在货架间忙碌的人,再也站不起来了。 这事儿里没有恶人,只有生活的沉重。三四十万和“八九成植物人”,两个数字就锁死了一个家庭的选择。医学的进步该让人更有底气,可对太多普通人来说,大病面前,底气早被高昂的费用磨没了。我们总说“生命无价”,可现实里,很多家庭都得给生命算一笔账。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