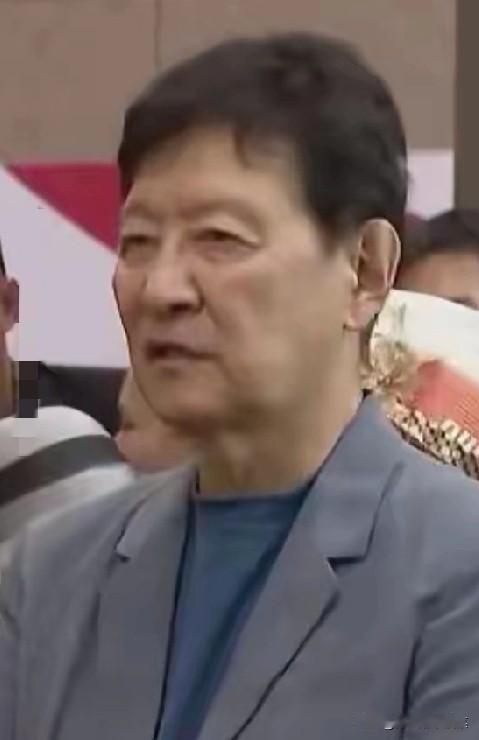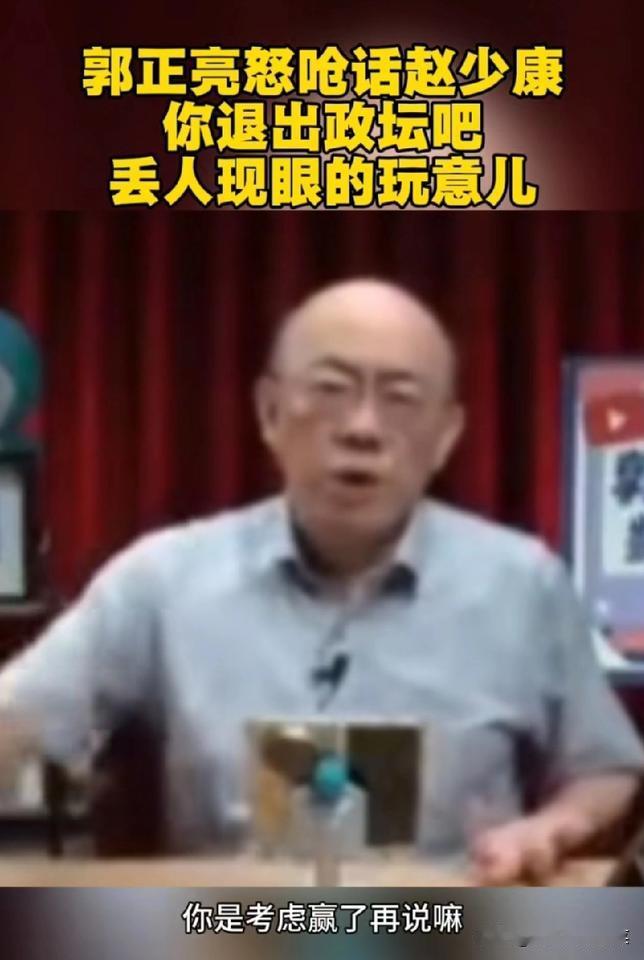1982年3月,李登辉长子李宪文在台大医院病逝,李宪文病逝后,院方本来要把遗体移到太平间。没想到李登飞突然抱起死去的儿子,走向太平间。 主要信源:(中时新闻网——祖代父职 享受四代同乐) 台大医院长廊里的消毒水气味混合着窗外的雨腥,1982年3月的这个午后,日光灯在湿滑的地砖上投下清冷的光。 李登辉的西装下摆掠过墙角的绿漆扶手,他抱着儿子逐渐僵硬的身体走向太平间,皮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产生回响。 怀中的李宪文鼻咽癌晚期造成的消瘦让西装显得空荡荡的,领结还保持着入院时精心打好的温莎结。 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生前最爱在书房摆弄地球仪。 从日本留学带回的桐木书匣里,还收着他在早稻田大学整理的笔记,纸页间夹着几片已经脆裂的樱花标本。 当他在文化大学政治系任教时,总喜欢用钢笔批改作业,墨水渍常染在指节处,像淡淡的胎记。 张月云第一次在图书馆遇见他时,他正对着《朝日新闻》做剪报,金边眼镜滑到鼻梁中部都浑然不觉。 确诊鼻咽癌那年,李宪文刚完成对原田钢《东亚政治结构》的译稿校订。 病房的床头柜始终摆着未完成的论文提纲,止痛针的药效间隙,他还会挣扎着记下几行思考。 婚礼上的白西装是临时改小的,癌细胞侵蚀让他瘦得撑不起原本的礼服。 喜宴的香槟杯沿还留着淡红的唇印,那是咯血后匆忙补妆的痕迹。 张月云在产房待产时,李宪文正接受第三次放疗。 他隔着监护室的玻璃窗看新生儿录像,化疗留置针在苍白的皮肤上格外刺目。 女儿满月照被做成胸针别在他病号服前襟,金属扣针时常勾到心电图导联线。 与此同时,台北仁爱路的官邸里,李登辉正在批阅关于农业改革的文件。 钢笔尖在"稻米保价收购"条款处停顿,墨迹晕开成云朵状。 秘书送来病危通知时,他刚签完提拔年轻技官的人事令,签名笔划还带着往常的沉稳力道。 医院来电那刻,书房座钟的报时鸟恰好弹出,咕咕声与电话铃音奇妙地重叠。 太平间的不锈钢柜门闭合时,反射出窗外雨中模糊的101大楼轮廓。 多年后当李登辉站在同一个窗口签署"戒急用忍"政策文件时,总会无意识摩挲西装第二颗纽扣——那是儿子葬礼时丧服上掉落的备用扣。 张月云后来设计的每套西装内衬都绣有李宪文名字缩写,针脚细密如病历卡上的医嘱字迹。 蒋经国召见李登辉讨论接棒事宜那日,士林官邸的茶席上摆着应景的菊花茶。 白瓷杯沿的热气氤氲中,李登辉注意到蒋经国颤抖的手指在杯柄留下湿痕。 书房墙上的"亲爱精诚"匾额新补过金漆,但"诚"字右下角的虫蛀痕依然隐约可见。 当话题转到两岸关系时,窗外的九重葛突然被骤雨打落花瓣,黏在玻璃上像血滴。 这些记忆碎片最终都沉淀在李登辉晚年日本访问的旅途中。 当他在京都金阁寺看到池中倒影时,忽然想起儿子幼年临摹《鸟兽戏画》的涂鸦稿。 和纸边缘的铅笔印被岁月磨得模糊,就像历史对每个人的评价都终将失去非黑即白的鲜明界限。 唯有太平间那日的消毒水气味,穿越数十载光阴依然清晰如昨。 李登辉晚年独处时,常对着书房里那架老式录音机发呆。 那是儿子生前用来录制日语学习磁带的设备,按键上的字母已经磨损。 有时他会按下播放键,听着磁带转动的沙沙声,仿佛在等待那个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成为父子之间跨越生死的特殊对话。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