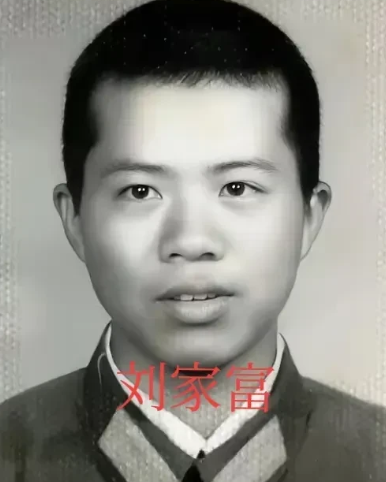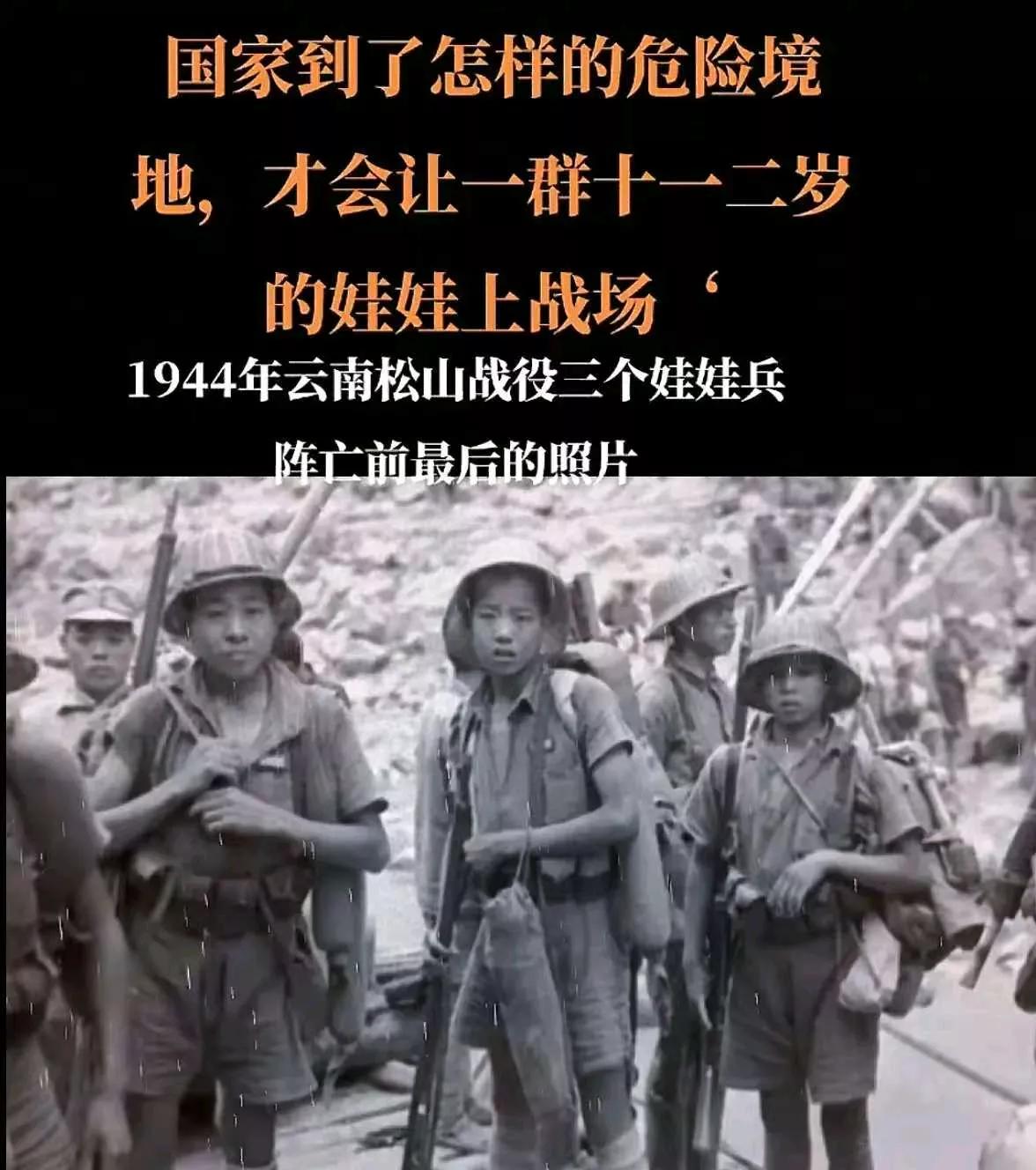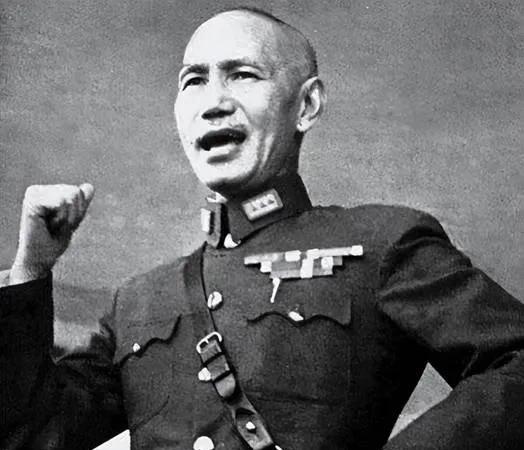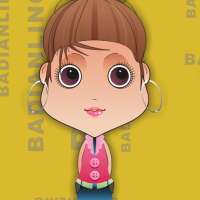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老山前线者阴山作战打响前31师师长廖锡龙在董干勘察战场地形时的一幕 山里常年起雾,者阴山的雾尤其顽固,夜里像棉絮一样罩下来,湿得能顺着眉毛往下滴水。 1979年那个三月,边境还没有彻底安静,中国军队大部队开始往回撤,战斗的尾声该是落幕的时候,可偏偏在者阴山,留下了一场小得几乎被忽视的战斗。 阵地交给了一群公安边防警察守。 帽子上的国徽闪亮,但那会儿没人去分这些身份,反正是穿绿衣服的人,扛着枪,就得顶在前面。 刘凤良,一个副站长,带着几十号人爬上1250高地。 挖工事的民工在他身后,锹镐落地的声音在雾里听得清清楚楚。谁都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高地会在几天后被敌人盯上。 3月12日凌晨,毛毛雨拍在脸上,冷得像针。 黑压压的雾里传来低沉的轰鸣,先是炮弹,一阵接一阵,把山头炸得像被火舌舔过,连帐篷都被掀飞。照明弹冲天而起,瞬间白得刺眼。 有人慌得连手榴弹保险都没拉开就甩了出去,啪嗒一声掉在脚边,幸好没炸。 那是新兵,才来七十多天,连枪声都没习惯过。 刘凤良站在阵地上,眯着眼盯着下方的黑影。 雾里突然有鸟群惊飞,他立刻喊了一句:“准备!”敌人果然摸上来了,一个加强连,分成几股。 可他硬是让大家忍着,等到距离近得能看见敌人的脸时,才一声令下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扑过去,手榴弹在敌群里炸开花。山上几十个人,打得山下几百人抬不起头。 那一夜,有人倒在泥里。炊事班的许跃本不该出现在前线,可他死死咬住战友的肩膀,不肯让人背他下阵地。孟庆云双脚被炸得血肉模糊,还在喊要死守到最后。 报务员杨朝云被炸昏,醒来时手里还攥着手枪,迎面就是两个敌兵冲过来,眼看要完了,刘凤良从侧后杀出,一枪击毙机枪手,副射手慌了,掉头逃跑。 阵地撑住了,敌人反复扑上来,始终没能踏上主峰一步。 天亮时,敌人丢下尸体和武器,慌乱撤退。我方也有人再没能下山,几个年轻的名字留在了石头缝里。那一战被称作“中国武警第一战”,可在当时,谁顾得上这些称号。 高地还在,就算胜了。 五年后,边境又紧张起来。 1984年春天,老山、者阴山成了中越对峙的焦点。这一次,轮到野战军的大部队接手。31师奉命出击,战役命令一条条传下来,不再是小股部队临时顶上的拼杀,而是正规的体系作战。 董干,一个名字普通的小镇,被选作前沿集结点。 泥泞的山路上,全是往返的军车和背着装备的士兵。廖锡龙,那时是31师师长,披着一件厚重的大衣,带着参谋们爬上山头。照片里,他蹲在地图前,手指点着几条山道,赵宗岐站在一旁,作训处长郭伟涛也在,几个年轻的脸庞带着紧绷的神情。远处的山谷里,雾像旧时的被褥,沉甸甸地压在地形线上。 勘察,不是摆姿态。 者阴山、老山一带的地形密不透风,山谷深,草密,敌人修的工事藏在林子里,像毒刺一样。侦察兵冒着风险潜入敌后,捕俘、画图,把情报送回来,再在这类山头会议上讨论。 哪条路能穿插,哪一侧容易被包抄,都得一一确认。 廖锡龙盯着地形图,脚下踩着泥,指头在地图上一划,就是一条穿插路线,也是几百人要用血去开辟的方向。 这一刻,与1979年的阵地守卫形成了鲜明对照。 那时候靠的是血性和临场反应,现在靠的是火力准备和体系配合。炮兵要打到分秒不差,工兵要在雨林里劈出路,通信兵要在断电断线的情况下保持联络。每一个环节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收复战铺垫。 战术的演进,就在这片山岭上写下了清晰的痕迹。 1979年,十几个人靠一股狠劲把山头守住;1984年,上万人在统一部署下展开攻坚。两场战斗之间隔着五年,却像同一本书的两章,一章写热血与偶然,一章写缜密与必然。 人物也在这条线索上连缀起来。刘凤良的名字留在武警的史册,他代表的是一群初出茅庐却敢死守的青年。廖锡龙在董干的背影,预示着他之后的步步攀升。 他不再是战斗的亲历者,而是决策者,他要对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负责。 赵宗岐,那时只是个侦察处长,带着侦察兵在丛林里摸爬滚打,后来成了将军。 不同的人物,在同一片山岭留下不同的痕迹。 者阴山就这样成为了一根线,把公安边防和正规野战军串在一起,把新兵的慌乱与将领的冷静放在同一个地理坐标里。 它是边境上的一个高地,也是记忆里的一个节点。 风声依旧,山路依旧,雾还是那样厚重。照片定格的那一刻,几个人蹲在地图旁,身后是灰蒙蒙的山谷,脚下是被雨水泡软的泥土。 几十里外的者阴山上,石头缝里还留着五年前的血迹。 就停在这一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