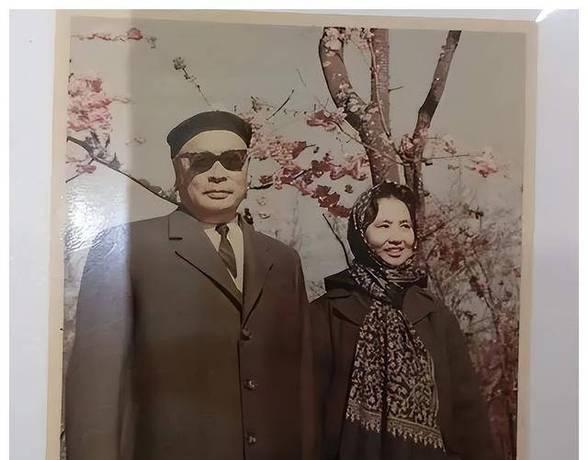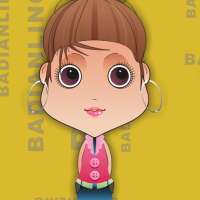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他毛泽东的威信是很高,可是他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我就不信了,苏区离开毛泽东就过不了日子了,红军就打不了胜仗了,开玩笑!”凯丰 满腹牢骚。 1935年初,贵州遵义,天湿,地冷,风卷着山里的雾气打窗纸,那些走了几千里的红军干部裹着军大衣坐在窄小的会场里,呼出的白气都没散干净,争论就已经炸开了。 凯丰站了起来,他那个时候年轻,气性重,话一出口便是带刺的。 “毛泽东的威信是很高,可他坚持的那套路线,我不信苏区离开他就过不了日子,红军就打不了胜仗了,开什么玩笑。” 这话一出,空气都像凝固了一下。 他不是平头百姓,他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说出这种话,在那个时间点,不啻于在冰上跳舞。毛泽东没有立刻顶回去,只是盯着他看。 后来有人说,那天毛泽东问了他一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这本书几章?第一篇讲什么?”凯丰愣在原地,一句话都挤不出来。 这个场面,版本很多。 有说毛当场反击,把他问得下不了台;也有说他情绪一上头,自己踩了空。 无论哪个,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那间屋子里,绝大多数人已经隐隐觉得,毛泽东该回来指挥红军了。只有极少数人,像凯丰,还在死死捧着博古和李德,仿佛那是一张已经褶皱却不能松手的旧地图。 其实凯丰也不是外行,他只是走错了一步——不是军事判断的问题,而是信任。 他信那两个人,信得太久,舍不得放。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家境一般,但自小脾气倔,脑子快。 少年时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就跟着学潮四处跑,后来去了武昌高师,又远赴苏联的中山大学深造。 那时的留苏干部回来后都有些自负,他也是。 他讲理论,讲得头头是道;写社论,一支笔能当十杆枪使;但上战场他就怯。 他自己也知道,他那点军事素养,不够红军指挥一个班。 可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指着毛泽东说你不行,他赌的是人气,不是事实。 会后,他被撤了职,调出军事口。当时的政治空气没有那么宽松,那样的错误,不算轻。他一开始还辩解几句,过不了几天就自己把话收了回来。 “我不是反,我只是想说……是不是也该看看别人的方案。” 他没再继续讲下去。 后来红军扭转战局,毛泽东一步步拿回主动权。 凯丰没出声,他看着,他是个会看风的人,但这次他不是跟风。他是真的服了。 张那边闹分裂,他第一个站出来写文章批评。那篇文章写得很辣,笔锋像刀子,把张的“小算盘”写得清清楚楚。毛看了,说了一句:“这个人还行,转过来了。” 整风的时候,他成了主持人之一。 1942年延安那场干部大会,他站在台上,面色沉静,话不多,手不抖。 他开场介绍完,就请毛泽东讲话。 毛讲的是《反对党八股》,点名批形式主义那一套,也批了“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理论家”。凯丰听着,一句没漏。 他知道毛在讲什么,也知道讲的是哪一类人。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窑洞外,抽了半根烟就掐灭了。 他没再讲自己错了什么,但谁都看得出来,他在变。他从一个“死讲主义”的人,变得开始听人说话,听群众说话。 1943年,他拟了个宣传方案,说想借毛主席五十大寿的机会,搞一波系统宣传,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他觉得,这时候该立个旗了。 毛回信说:“现在是困难时期,生日决定不做。至于我的思想,自觉还未成熟,不是鼓吹的时候。” 凯丰读完信,把纸收进抽屉,什么都没说。 有人问他毛怎么回的,他只笑了笑,说:“主席这个人,比我们谁都清醒。” 再往后,凯丰去了东北,办报纸,搞教育,做宣传。 他从不抱怨,说自己调离核心圈。他清楚自己错过了那次站队,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被永远接纳。 但他能干,他守规矩,他不乱说话。 他写的文章还是那么利落,讲话一如既往有逻辑,不像个被冷落的人。 他没有孩子,晚年住在北京,常戴顶呢帽,走路略微驼背。 1955年病倒,诊断出问题时已无力回天。他躺在医院那张白床上,说了一句:“还没做完的活太多了。”邓小平给他写了悼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这不是礼貌话,是实话。 一个曾经在生死关头说错话的人,最终能留下一句这样的话,说明他这一生,扳得回来。 这人最后一次出现在毛泽东讲话中,是整风后的一场内部总结会。 毛点了他,说:“凯丰同志,是个改得快的人。” 没谁再提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话。也没人替他解释什么。 只是过了很多年,有人路过延安旧址的干部大会会场,看到主持人那张旧照片,轻轻说了一句:“他也曾顶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