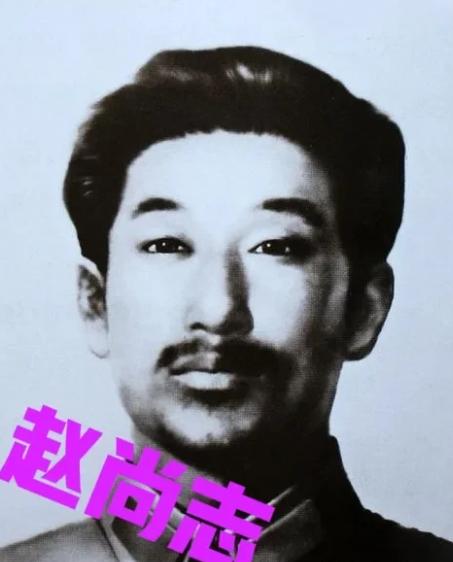“1942年,渔夫陈根土携妻儿逃难时,撞见了日军,为了保护妻儿,他只好独自载他们过江。可奇怪的是,船刚到江水中心,他就发出诡异的笑声,然后唱着山歌纵身一跃跳入了滔滔江水之中。” 衢江中心炸开的木船碎片里,混着十六顶日军军帽。 而制造这场“意外”的渔民陈根土,此刻正潜游回岸。 这个在衢江上漂了半辈子的普通渔夫,用一次决绝的沉船,完成了对家仇国恨的终极清算。 陈根土的家,在衢江怀抱中的江心洲。 那是个巴掌大的小岛,四面环水,土地金贵。 岛民世代靠水吃水,陈根土也不例外。 一条旧木船,一张渔网,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他住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妻子阿莲操持家务,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玩耍。 日子清苦,但陈根土有副热心肠。 打上来的鱼,自家留点,剩下的常分给岛上孤寡。 而他在去衢州城换盐巴粗布,总不忘给东家老人捎把菜,给西家孩子带块糖。 衢江的水养人,也养出了他朴素的善良。 然而,1942年的战火,却烧到了衢州。 这座扼守四省咽喉的古城,成了中日军队反复争夺的炼狱。 枪炮声日夜不停,日军不仅用枪炮,更丧心病狂地撒播鼠疫。 瘟疫在城中蔓延,陈根土的父母,没能逃过这场人为的灾祸,在病痛折磨中相继离世。 国仇,叠加上刻骨的家恨,像毒刺一样扎进陈根土心里。 战局日益吃紧。 装备劣势的国军部队,在日军猛攻下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衢江北岸。 江心洲,这个弹丸小岛,因扼守江心,成了双方都想控制的水上要冲。 陈根土蹲在自家破船边,望着对岸的硝烟,听着伤兵痛苦的呻吟隐约传来,心如刀绞。 他在衢江上讨生活几十年,闭着眼都能摸清水下的暗礁和急流。 自己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为国流血的年轻生命在岸边挣扎,他坐不住了。 一天凌晨,天还没透亮,陈根土把船推下水。 他攥紧船桨,对抹泪的阿莲只说了句:“我去北岸接伤兵,你看好娃。” 江面上子弹“嗖嗖”地飞过,而陈根土伏低身子,凭着对水路的熟悉,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一趟,两趟,三趟,他记不清往返了多少次。 每一次靠岸,都背起伤兵,安置在摇晃的船舱里。 船板被血水浸透,滑腻难行。 有一次,一枚未爆的炮弹就落在船边,幸得一名战士眼疾手快将他扑开。 最终,他拼死救回了八十多名伤兵。 岛上的乡亲们,妇人熬粥,男人卸门板当担架,连孩子都帮忙递水。 不久,衢州城破,日军兵锋直指江心洲。 小岛已非安全之地。 陈根土收拾了点烂家当,带着妻子和两个幼子,准备渡江逃难。 结果船刚离岸,被十几个日军发现了。 后面跟着个翻译官,翻译官威胁陈根土必须载他们过江,否则全家性命难保。 陈根土看着吓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和妻子,只能妥协“走!” 船行至江心,小船剧烈摇晃。 日军挤在狭小的船舱里,骂骂咧咧。 翻译官坐在船头,死死盯着船下的漩涡。 突然,他扯开嗓子,唱起了渔歌。 日军面面相觑,翻译官疑惑地问他唱什么。 陈根土没有回答,吼出一句“一道见龙王!”,用尽全身力气,抡起船桨,狠狠砸向旧船底! 船底随即裂开一个大洞! 船上的日军猝不及防,尖叫着扑向破洞试图堵漏,但船体迅速倾斜。 就在船只倾覆的刹那,陈根土扎进江水里。 他憋着气,向下潜游,避开漩涡。 头顶上,传来日军绝望的呛水和挣扎声,很快便归于沉寂。 等他精疲力竭地爬上对岸时,江面上只剩下漂浮的军帽、和几缕血丝。 阿莲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陈根土却坐在泥地上,哑着嗓子说:“哭啥?咱活下来了。” 1943年,日军撤退。 陈根土带着家人回到江心洲。 家园已成废墟,赖以生存的渔船早已沉入江底,只能重新扎竹筏度日。 他的事迹在岛上悄悄传开,乡亲们敬佩地称他“英雄”,他却连连摆手:“啥英雄?就是个打鱼的,护着自家人罢了。” 战后的日子,比战时更艰难。 鱼少了,米贵了。 1944年冬天,竹筏无法下水,断了生计的陈根土,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一天,他喝了点烧酒,走到江边,蹲在厚厚的冰面上。 雪越下越大,等乡亲们找到他时,人已经冻僵了。 或许,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看到了自家娃在江边奔跑,看到了阿莲低头补网的模样,看到了那十六顶军帽沉入江底,看到了父母在天之灵的慰藉。 如今,在江心洲,老人们偶尔还会提起陈根土。 “他咋就那么傻?自己死了,娃咋办?” 他们或许不明白,有些选择,无关傻与不傻,只关乎骨头里的硬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