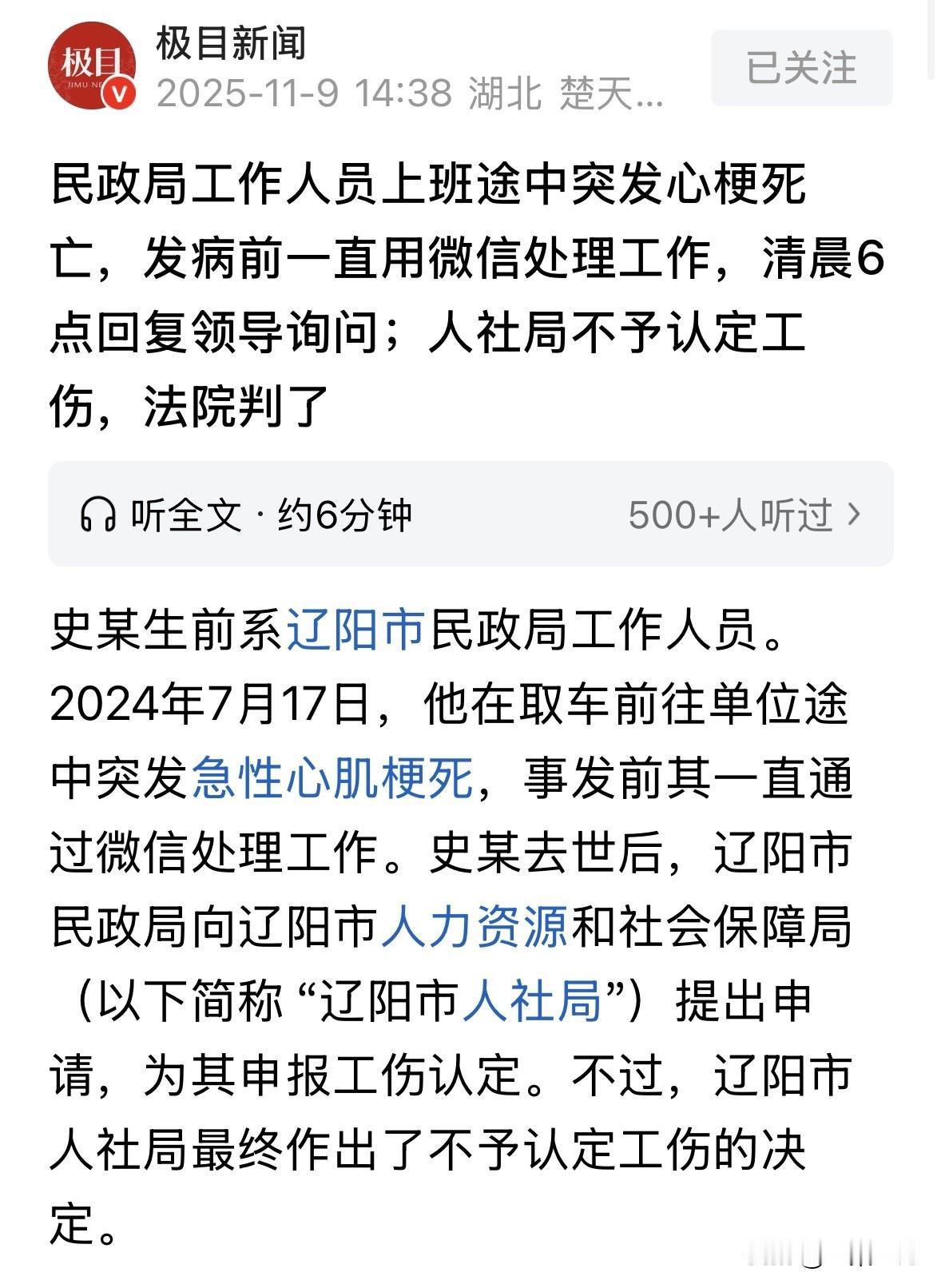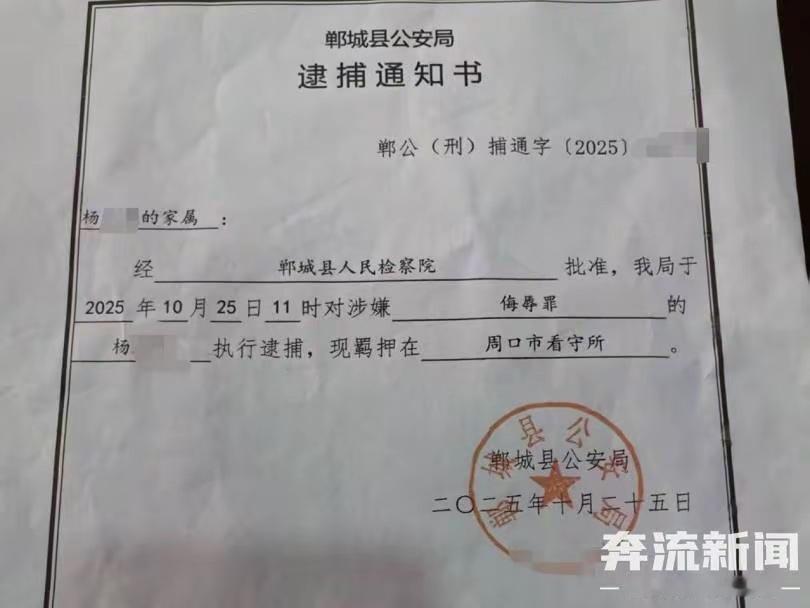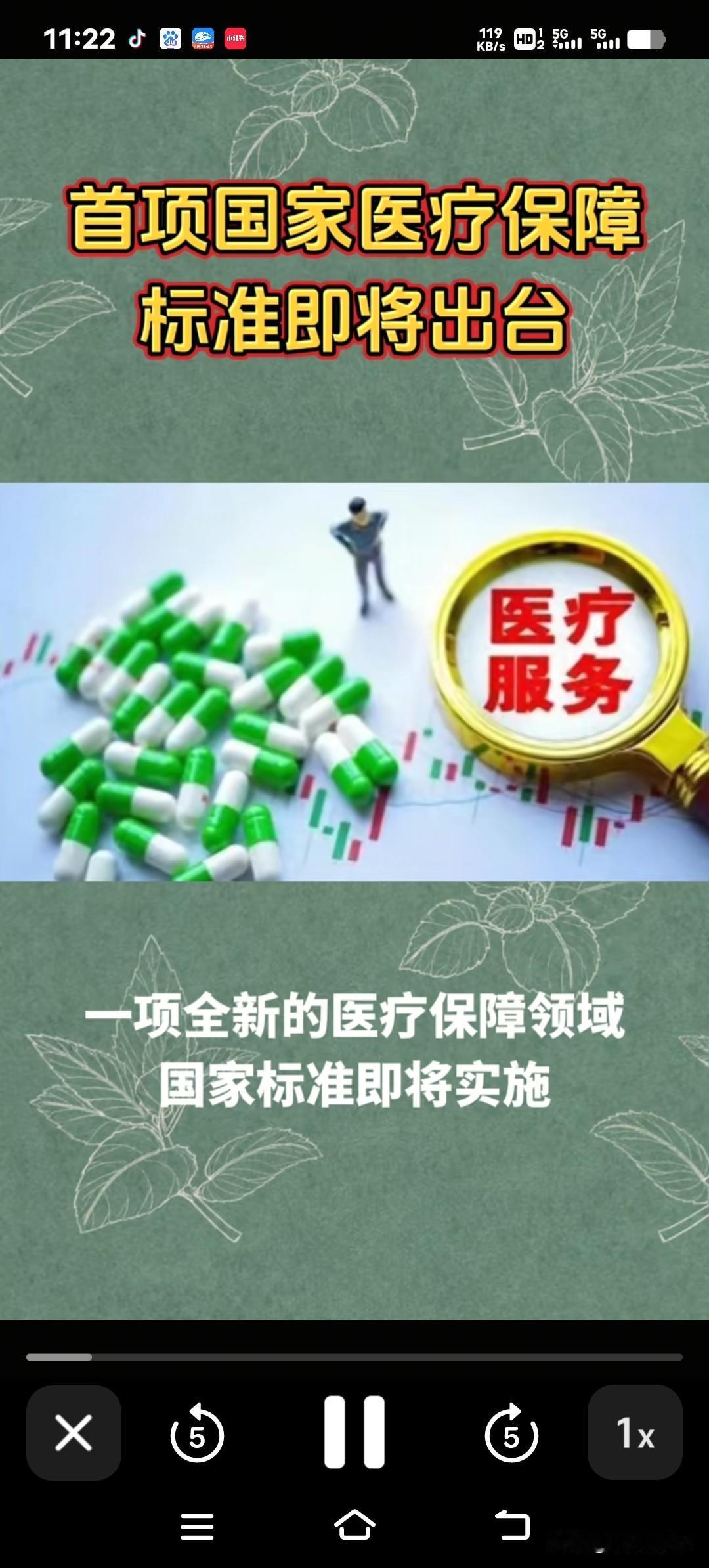辽宁辽阳,男子是民政局工作人员,这天,他凌晨6点多就开始在手机上处理工作,然而,就在他准备取车出发单位时,竟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去世了,单位为他申报工伤认定,人社局认为男子非工作时间死亡,不予认定工伤,家属不服,认为男子是上班途中死亡的,且生前一直在处理工作,凭啥不算工伤?家属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该认定,重新作出决定,人社局提起上诉,二审判决亮了。 2024年7月17号,清晨6点03分,大多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民政局工作人员老史的手机屏幕亮起。 他一看,是领导刘局的微信,对方问他:今天去灯塔几点碰头?还有谁一起? 刚起床的老史立刻回复:我问问孙某。 接着,他随手就把对话截图转给了同事孙某。 6点20分,孙某的回复弹出,说昨天跟刘局说了没定时间,今天去吗?你问问刘局。 老史紧跟着追问:科里都去灯塔对吧?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就没再回复。 此时,老史正走向停车点准备上班,然而,走着走着,他突然在一家超市附近倒下了。 6点41分时急救车赶到,7点20分出车送医,只可惜,老史还是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没救回来, 老史去世后,所在单位找出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微信记录,向人社局递交工伤认定申请。 材料里显示,从接到领导询问到突发疾病,老史全程在协调工作。 所在单位认为,现在大家下班后基本都是要用微信继续沟通工作的,手机就相当于一个移动工位了。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只要在工作时间和岗位突发疾病死亡,就该算工伤。 然而,人社局在10月10号的一纸决定却泼了盆冷水:不予认定工伤。 人社局的理由很直接,说老史病发时既没到单位,也没坐在办公桌前,非工作时间死亡,不属于工伤。 这让老史的家属无法接受。他妻子百思不得其解,丈夫出门前还在处理公务,如今竟成了“与工作无关”?手机里工作不算工作,那什么算? 家属不服,把人社局告上法庭。 那么,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这件事?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职工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传统认定中,“工作时间”以单位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为限,但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结合现代通讯技术特征进行实质审查。 史某虽在清晨6点突发疾病,但案发前持续通过微信与领导、同事沟通工作事宜,且该行为具有“经常性、连贯性”特征,他日常存在下班后线上处理工作的惯例。 法院据此认定,线上办公时段应视为工作时间的合理延伸,突破了“朝九晚五”的机械认定。 法条原意中“工作岗位”指向固定办公场所,但本案将“工作岗位”扩展至“工作状态”。 史某虽未到达单位,但他在取车途中仍通过微信履行工作职责,处于“工作准备状态”与“工作执行状态”的衔接环节。 法院认为,当职工处于“为工作目的而移动”的状态时,应视为工作岗位的延伸,符合“视同工伤”的立法保护初衷。 法院最终判定:人社局根本没查清三个关键问题。 老史发病时微信办公算不算工作时间?突发疾病和工作有没有关系?他是否存在长期远程办公的惯例? 2024年底,一审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决定,要求人社局重做认定。 人社局不服上诉,坚称“上下班路上出事本来就不算工伤”。 但二审法官依旧认为,手机早成了第二办公室,你们不查清他是否常态性线上办公就草率决定,站不住脚。 人社局败诉的关键在于没有履行全面调查义务。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4条,行政机关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人社局仅以“未在单位场所发病”为由作出否定认定,却未核查史某微信工作记录的真实性、未调查其日常线上办公的频率与内容,导致“主要证据不足”。 法院借此强调,工伤认定需综合审查“工作关联性”证据链,包括通讯记录、同事证言、工作日志等,形成完整证据闭环。 2025年11月3日,中院维持原判。 有人说,人社局怕以后巡视、巡察被追责,通过一审判决作为工作依据是对的,但提起上诉就不厚道了,都是打工人,人已经死了,在允许范围内照顾一下也是理所当然! 也有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人社局一审输了还要二审,其实也是为了尽职免责,虽然工伤保险不用他们出,但也要看好上面的钱袋子。万一在巡察巡视时被认定为把关不严,那么个人就要受处分。另外,现在滥诉的原因也和起诉费太低有关。看似降低了起诉成本,但也为投机分子留下了空间。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一案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