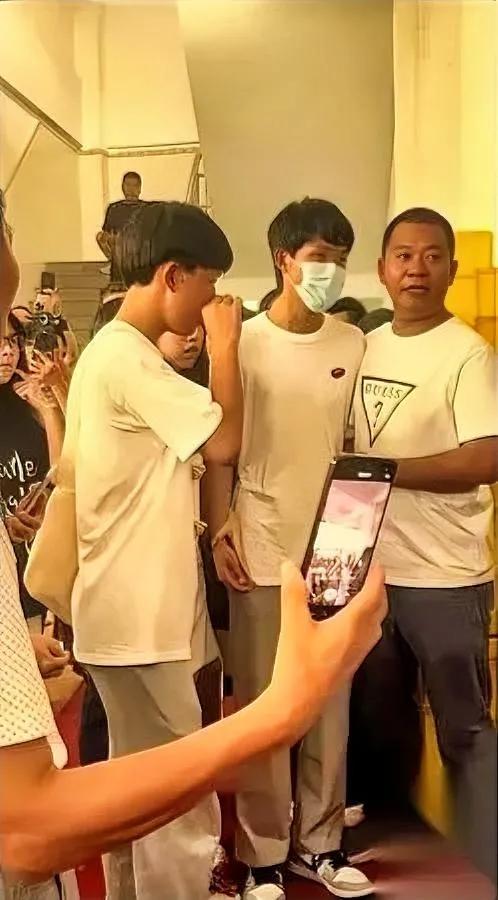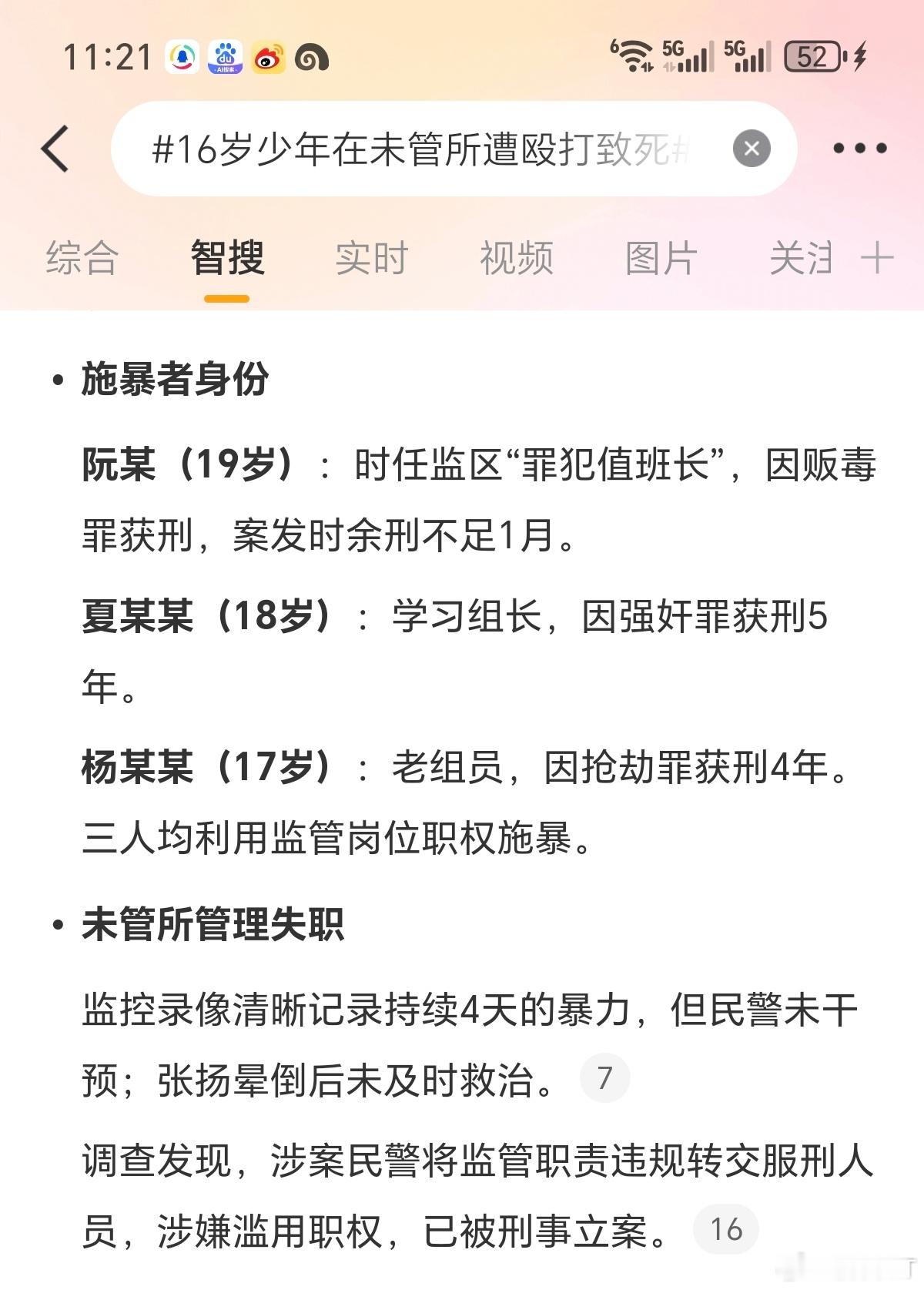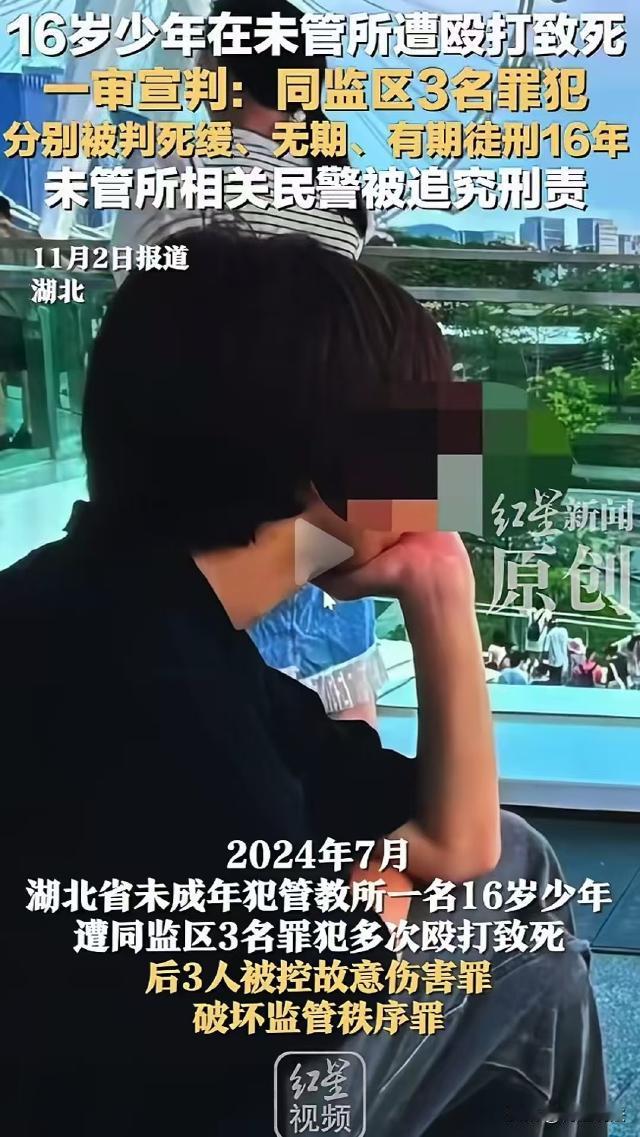四川成都,24岁的陈某,因为一时贪念和冲动,从“嫖资纠纷”变成了“持械恐吓”,最终被法院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2000元。 2025年2月27日晚上,陈某下班回到出租屋,心情烦躁、无所事事。浏览手机通讯录时,他无意间看到一个陌生却漂亮的头像——那是他曾短暂聊过天的女子袁某。陈某心血来潮,给袁某发了一条信息:“有时间吗?出来玩。”袁某回道:“有空。”接着两人开始谈价。袁某开价3500元,陈某嫌贵,讨价还价后以3000元成交。对方发来地址:“来我这。” 陈某洗漱、更衣,带上现金便匆匆出门。到达袁某的出租屋后,两人几乎没有寒暄,直接发生关系。事后,陈某把3000元现金递给袁某,自己坐在床边休息。袁某随后进入卫生间洗澡,屋内恢复了安静。 此时的陈某,心中忽然闪过一丝不甘。他想到自己一个月工资也不过四千多,辛苦工作换来的钱就这么没了,越想越心疼。目光不经意落在床头柜上的包上,他看见那叠刚刚付出的现金露出了一角。那一刻,他的理智开始动摇。 他轻轻站起身,确认袁某仍在浴室后,伸手将钱拿回口袋,动作干净利落。表面若无其事,准备离开。袁某擦着头发走出卫生间时,注意到陈某神情慌乱,便本能地去翻包。果然,3000元不见了。她立刻质问:“钱呢?是不是你拿的?” 陈某假装镇定地说:“没拿,你自己看清楚。”袁某不依不饶,挡在门口不让他走。情急之下,陈某掏出一根随身携带的电棍,一边打开电流声一边威胁:“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想清楚。”刺耳的电流声让空气都凝固了。袁某被吓得退后几步,不敢再阻拦。陈某迅速逃离出租屋。 冷静下来后,袁某越想越气,最终选择报警。警方接警后很快锁定陈某行踪,并电话通知他前往派出所。陈某在讯问室中承认了全过程,辩解称:“钱本来就是我的,我只是拿回而已。” 然而,他的这番解释在法律面前并不成立。 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认为,陈某虽然最初给钱是自愿行为,但当他在袁某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取回钱款,这一行为已构成“盗窃未遂”。更为严重的是,当袁某要求归还时,他不仅拒绝,还使用暴力威胁,这种“暴力胁迫以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刑法中,抢劫罪的本质是以暴力或胁迫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不要求财物必须属于他人所有,只要行为人非法剥夺他人占有即可。本案中,即便陈某原本给的钱属于他自己,但在付出后,钱已转化为袁某合法占有的财产。陈某若想主张返还,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而非以胁迫手段“夺回”。 法院经审理后认定: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威胁行为阻止被害人追索,其行为构成抢劫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元。 从表面看,这似乎只是一次“嫖资纠纷”,但法律视角下,行为性质已截然不同。陈某之所以被定罪,不在于他“嫖娼”,而在于他以暴力手段夺取他人合法财物。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对“抢劫与抢夺”“盗窃与抢劫”的区分非常严谨:若行为人在秘密窃取财物后被发现,为抗拒抓捕或控制继续持有财物而施暴,则构成抢劫;若施暴发生在窃取前或没有控制财物目的,则另当别论。陈某恰恰符合前者,因此定罪合理。 这一案件,也折射出一些社会现实问题。首先,年轻人法律意识淡薄,对行为边界模糊。陈某以为“钱是我的,我拿回来没事”,却忽视了财产占有转移后的法律属性变化。其次,情绪冲动是犯罪的常见导火索。陈某因一时不甘,未经过大脑思考,结果从民事纠纷滑向刑事犯罪。 在司法层面,法院量刑时已综合考虑陈某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因此未作重判。若其在威胁中造成实际伤害,刑期可能达三年以上。 从社会层面看,这起案件还提醒人们警惕网络交友与金钱交易带来的风险。袁某的行为虽然本身涉及违反治安管理,但在法律关系上,她的财产权仍受保护。刑法的立场是“违法不等于可以被侵权”,哪怕双方行为本身存在道德瑕疵,也不影响刑事保护的适用。 陈某最终在法庭上流泪悔过:“我只是太冲动了,没想到会是抢劫罪。”但法律没有“冲动免责”,它只承认理性与后果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