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27日,69岁的蔡廷锴回到家乡罗定,距离他上次回来已隔16年之久 你猜他下车时第一动作是啥?不是跟迎上来的干部握手,而是弯腰蹲在路边,粗糙的手掌狠狠捏了一把家乡的黄泥土,指缝里全是碎土粒,他凑到鼻尖闻了闻,声音有点发颤:“还是这股子土腥味,16年了,没忘!”那天他穿的是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中山装,领口还补了块不太显眼的补丁,跟当年在淞沪战场指挥十九路军时的戎装比,简直像换了个人,可腰板依旧挺得笔直,眼神里的劲没减半分。 来接他的有公社干部,还有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其中一个叫陈阿福的,一看见他就扑过来攥住他的胳膊,眼泪直接掉下来:“廷锴啊!你可算回来了!当年你带我们打鬼子,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蔡廷锴也红了眼,拍着陈阿福的手背,一个劲问:“家里咋样?娃们都好?当年你腿上的枪伤没落下病根吧?”陈阿福说:“托你的福,都好!就是去年闹灾,粮食紧了点,不过公社里正组织种冬麦,日子能撑住!”这话让蔡廷锴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来他跟干部们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乡亲们真日子,别跟我整那些虚的。” 他先回了老宅,那是座青砖瓦房,院墙爬满了牵牛花,门框上还留着当年他参军时贴的“保家卫国”红对联痕迹,只是颜色褪得快看不见了。推开吱呀响的木门,屋里摆着一张旧八仙桌,几条长凳,都是他小时候用过的老物件。他摸着桌子边缘的包浆,跟跟在后面的乡亲说:“当年我就是在这张桌上,跟我爹学写‘人’字的,他说做人得像这字,站得稳,行得正。”后来才知道,这老宅这些年一直没人住,公社特意派人定期打扫,就怕他回来时没个念想——这份心,蔡廷锴记在心里,后来他自己掏腰包,给公社捐了笔钱,让修修村里的小学,说“娃们读书不能受委屈”。 下午他去了村头的晒谷场,那会儿乡亲们正忙着翻晒刚收的红薯干。看见他来,大家都围过来,有个叫李婶的,塞给他一块还带着热气的红薯干:“廷锴叔,你尝尝,今年的红薯甜!”蔡廷锴接过来就咬了一口,边嚼边点头:“甜!比我在广州吃的还甜!”他蹲在晒谷场边,跟几个老农聊收成,问一亩地能收多少红薯,有没有足够的种子留到来年。当听说公社在推广新的红薯种植技术,产量能提两成时,他高兴得拍了大腿:“好!就该这样!不管是打仗还是种地,都得讲方法,不能蛮干!” 有人提起当年淞沪抗战的事,问他:“廷锴叔,当年你们才几万人,咋就敢跟日本鬼子硬拼啊?”蔡廷锴放下手里的红薯干,眼神一下子亮了:“咋不敢?他们占我们的地,杀我们的人,咱中国人要是怂了,还有啥脸见祖宗?那时候我们十九路军,个个都抱着‘死也不后退’的劲,上海街头的老百姓给我们送吃的、送弹药,连娃们都拿着小旗子喊‘加油’,有这股子民心,咱就不怕打不赢!”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都静下来——这哪是在说过去的事,更像是在跟乡亲们说:不管遇到啥难,只要人心齐,就没有跨不过的坎。 你有没有听过家里长辈讲抗战时期的故事?是不是也有像蔡廷锴这样,出去闯天下,却始终惦记着家乡的人?我后来听罗定的老人说,蔡廷锴那次回乡,没住公社安排的招待所,就睡在老宅的旧床上,每天早上都跟着乡亲们去田埂上转,晚上跟大家在晒谷场聊天,直到月亮升到头顶才回去。走的时候,他跟乡亲们说:“我虽然在外头,但根在这儿,以后我会常回来看看的。” 蔡廷锴这辈子,从带兵打仗到建国后参政,心里装的从来都是国家和百姓。他回乡不是为了摆“大官”的架子,而是想真真切切看看乡亲们过得好不好,能不能帮上忙。这种“不忘本”的劲,比任何光环都珍贵——毕竟,一个连家乡泥土都记挂的人,心里装着的,肯定是整个民族的牵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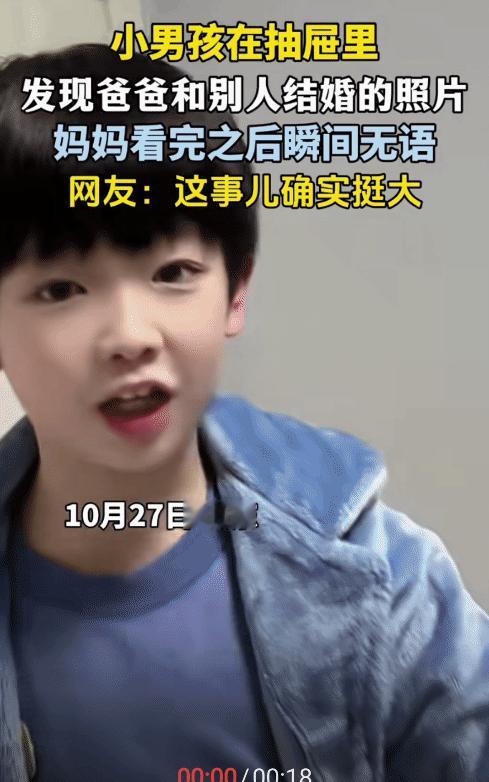



22号
罗定种麦?
用户10xxx14 回复 10-30 14:57
那时候生产队冬种会种一次,到春分后收割!一直到分田到户后不种了!
用户13xxx27 回复 10-30 14:58
当时全个肇庆地区都有种,我老家封开偏远山区都种过(六十年代的)
用户10xxx34
广东人叫小孩为娃?看出写作人不是两广人吧
用户17xxx34
有一段时间,冬天种麦,种蚕豆,种紫云英的都有,只是产量不高,然后去粮所换大米。
鸽子飞翔
广东人一口北方口音?
用户65xxx00
怎么看着像瞎编的?
用户10xxx25
明显AI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