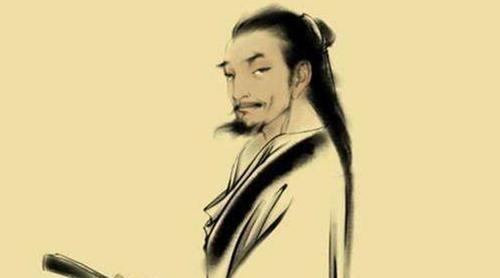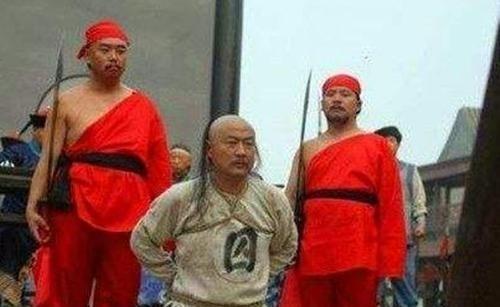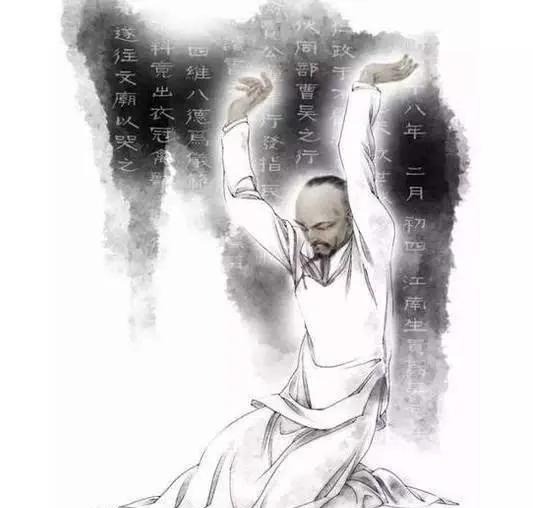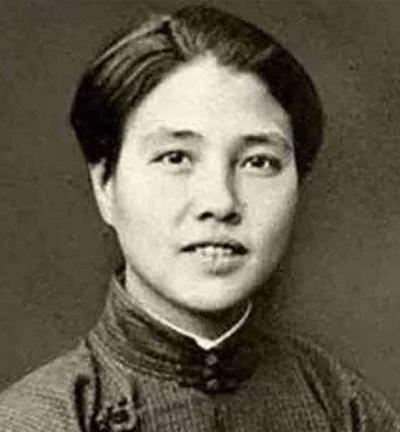1661年,金圣叹被判处死刑,刑场上,他对刀斧手神秘一笑,“我耳朵里藏了银票,只要你先砍我,钱就是你的咯。”刀斧手大喜,刀起头落,还真滚出两个纸团,打开一看,脸都绿了。 说起金圣叹这个人,搁在明清那会儿,绝对是个不走寻常路的家伙。生于1608年,苏州吴县人,原名叫金采,后来自己改成金人瑞,字圣叹。家里条件还行,书香门第,从小就泡在书堆里,脑子活络得不行。明朝末年,清军南下,天下乱成一锅粥,他倒没想着从军或者钻营官场,就一门心思搞文学,评书批注,搞得风生水起。结果呢,活到53岁,就因为一桩哭庙案,给清廷砍了脑袋。这事儿搁现在,估计得上热搜,民间还流传他临死前那段耳朵藏纸团的段子,说是“好疼”两个字,戳中了多少人的笑点和感慨。 先聊聊他的科举路子吧,这部分最能体现他那股子倔劲儿。明清科举,考中了就能飞黄腾达,他偏不买账,四次乡试,全是零蛋,还把自己搞进黑名单。第一次,题目是论语里“吾岂匏瓜也哉,焉能击而不食”,意思是孔子不想当无用之物。别人正儿八经议论,他直接画了个和尚拿剃刀的图,意思是出家避世才对头。考官一看,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刷下去。第二年,题目“四十不动心”,出自孟子,讲人到中年别为外物乱了方寸。他呢?卷子上密密麻麻写三十九个“动”字,墨汁都快把纸浸透了。阅卷的官员差点吐血,卷子直接报废。第三次,“西子来矣”,本该谈西施救国,他写打油诗,东门不开西子不来,南门不开西子不来,北门不开西子不来,只有西门开了西子才来。考官读完,摇头叹气,这秀才秀到家了。第四次,他学聪明了,改名金人瑞,收起花招,正经作答,总算中了秀才。从此,他对科举彻底死心,觉得那套东西就是骗人的玩意儿,不值一提。 中了秀才后,他也没去当官,就窝在苏州,专心批书。这事儿干得风生水起,他自封“第六才子”,推崇六部书:《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搁那时候,经史子集才是正道,小说戏曲被当成闲书,他偏要抬高它们,说这些才是真才子之作。尤其是《水浒传》,他批了前七十回,后三十回直接删了,觉得那是后人续的,格调不对,英雄气没了,就剩狗血。结果呢?这版水浒在清代传了三百年,成了最流行版本,书坊印得飞起,街头巷尾的茶馆里,闲汉们边喝茶边议论梁山好汉的窝囊样儿。他对《西厢记》也下狠手,批得细致入微,每句都圈点,戳中了多少读者的心窝子。批《庄子》时,他直言这书比儒家那些玩意儿接地气多了,能让人看透世事。《杜诗》他也评,搜罗遗漏,编成集子,影响不小。说白了,他这人就是个推手,把白话小说从街头小报地位,硬生生拉到文学殿堂,开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河。书一出,苏州书肆门庭若市,士子们争相买,边读边叹,这家伙的眼光真毒辣。 不过,他这性子太狂,树敌不少。清廷入关后,江南士人还念着明朝旧事,税赋重,官吏贪,怨气冲天。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的灵柩从北京运到苏州,沿途士民哭灵,本是悼念,谁知苏州十八个秀才,带头在文庙哭诉,控告巡抚朱国治和按察使任维初贪污仓粮,克扣百姓,害得乡民饿死。朱国治这人,履历上写得花团锦簇,其实手黑心狠,江南奏销案里就捞了不少油水,这次哭庙直接定性为“哭庙逆案”,抓了十八人,秋后问斩。金圣叹那天正好没去现场,他在家批书呢,但早年批注那些书,戳中清廷痛处,地方官恨他入骨,顺藤摸瓜把他也抓了。审讯时,他咬牙不认,拷打也没松口,判了斩立决。这案子闹大,苏州士林震动,清廷借机敲打江南,杀了十七人加金圣叹,总共十八颗脑袋落地。朱国治和任维初呢?非但没事儿,还升了官,继续收税,百姓苦哈哈的日子没个头。 说到他死的那天,民间传得神乎其神,说他临刑前对刽子手许诺耳朵藏银票,先砍他钱就归你。刀落头掉,纸团滚出,一个“好”字一个“疼”字,合起来“好疼”。这故事听起来解气,戳中了砍头这事儿多疼的荒诞感。但考证起来,这多半是后人编的段子。史料里没直接记载,最早见于清代野史笔记,传了三百多年,成了金圣叹的招牌笑谈。真实情况是,1661年8月7日,西门外菜市口,他和那十七人一起跪地,监斩官一挥旗,刽子手们上手,血溅当场。他的头被悬城门示众三天,苍蝇嗡嗡,路人绕道。家人遭株连,儿子金旭捧着遗稿,四处抄书卖钱,勉强糊口。苏州士子从此噤声,文坛冷清了好一阵。 这案子搁清初文祸里,算一桩典型。清廷刚稳江山,怕江南反骨,哭庙案成了杀鸡儆猴的把戏。金圣叹没真参与哭庙,他那批书里隐隐有反清味儿,早被盯上。杀了人,书却没死。他的第六才子书,越传越广,《水浒》删节版成了清人读物标配,里面那股子英雄末路的酸楚,读着读着就想起明亡的影子。《西厢记》批本,教人怎么在规矩里偷着乐,影响了后世多少戏曲家。甚至《庄子》,他批得通俗,街头小贩都能看懂,世事如梦的调调,帮了不少人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