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5月,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回乡探亲,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上将率领几百名老战士迎接。陈副局长含泪讲:“当年的事我难辞其咎,应该承担责任。”陈司令也是泪水连连,回答:“老首长啊,我们欢迎您回乡看看。” 说起当年的陈昌浩,那可真是天之骄子,意气风发。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材生,24岁回国,很快就成了鄂豫皖苏区的核心领导,和徐向前、张国焘并称“三驾马车”。他那时候有多猛?黄安战役,城久攻不下,陈昌浩竟然亲自带着手枪,登上了我军唯一一架飞机“列宁号”,飞到县城上空往下扔迫击炮弹。 这一炸,不仅炸懵了敌人,更把红四方面军的士气提到了顶点。所以,在老部下心里,陈昌浩一度是“军神”一样的存在。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两万多精锐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这本是一步关乎全局的战略大棋,谁也没想到,竟成了一场悲壮的远征。 在河西走廊,西路军孤军深入,面对的是兵力、装备、补给都占绝对优势的马家军。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不对等的血战。关于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发生了著名的“徐陈之争”。 徐帅从纯军事角度考虑,认为敌我悬殊,应避实击虚,速进新疆。而陈昌浩呢,他手里握着中央的电令,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凉州地区建立根据地,以策应河东的战略全局。 很多人后来复盘,都说徐帅的意见更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但咱得设身处地想想陈昌浩的处境。就在不久前,他因为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跟随了张国焘,犯过严重的路线错误。这个“思想包袱”太重了。所以,当西路军面临抉择时,他表现出了对中央指示近乎“刻板”的忠诚,坚决执行命令,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我们今天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评价他。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服从中央的战略部署是天职。他的坚持,恰恰源于他对党的一片赤胆忠心,一种急于在政治上证明自己“再也不会犯错”的迫切心情。只是,这份忠心,在残酷的战场现实面前,付出了太过惨痛的代价。 西路军最终兵败,两万多人,回到延安的不足千人。这对陈昌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兵败后,他辗转回到老根据地,想拉起一支队伍,没成功。最后历尽艰辛回到延安,等待他的是审查和批判。不久,他因严重的胃溃疡,经中央批准,于1939年赴苏联治病。 这一去,又是十三年。 原以为只是治病,没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困在了异国他乡。据他儿子陈祖莫后来的回忆,那段日子极其艰难。战争时期,他甚至要去采石场做苦力糊口,饿到胃病复发。后来情况好转,他被安排从事翻译工作。 就是在莫斯科那间只有十二平米、三口人挤一张床的小屋里,陈昌浩倾注心血,主持编撰了新中国第一部大型《俄华辞典》。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政委,把所有的才情和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个字一个词的枯燥工作中。或许,只有在这样的埋首劳作中,他才能暂时忘却河西走廊的炮火和数万将士的冤魂。 1952年,陈昌浩终于回到祖国,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从统率千军万马的方面军总政委,到一名副部级的学者型干部,这个落差不可谓不大。他默默接受了这一切。因为在他心里,西路军的失败,是他一生都卸不下的十字架。 所以,我们再回看1962年那场催人泪下的重逢,就能明白那两句对话的分量。 陈昌浩的“我难辞其咎”,是他压抑了25年的自我审判和公开忏悔。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没有提中央的电令,没有说客观的困难,只是把所有的责任,一个人扛在了肩上。这是一个男人,一个曾经的统帅,对自己袍泽的交代。 而陈再道的“我们欢迎您回乡看看”,则代表了幸存下来的老部下们的态度。他们没有忘记这位老首长曾经带领他们创造过的辉煌,更能理解他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艰难抉择。这句看似平常的家乡话,实际上是一种宽恕,一种接纳,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同志情谊。它告诉陈昌浩:“老首长,我们从未当你是罪人。” 可惜的是,历史的残酷性,常常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场回乡的短暂慰藉,并没有成为陈昌浩人生的转折。几年后,风暴骤起,当年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那封“密电”旧事被重新翻出,陈昌浩再次受到冲击。 1967年7月30日,不堪受辱的他,选择服药自尽,结束了自己复杂、悲壮又令人扼腕的一生。连骨灰都没能留下。 直到1980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在追悼会上,给出了“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评价。这份迟到了13年的公正,总算告慰了那颗饱受创伤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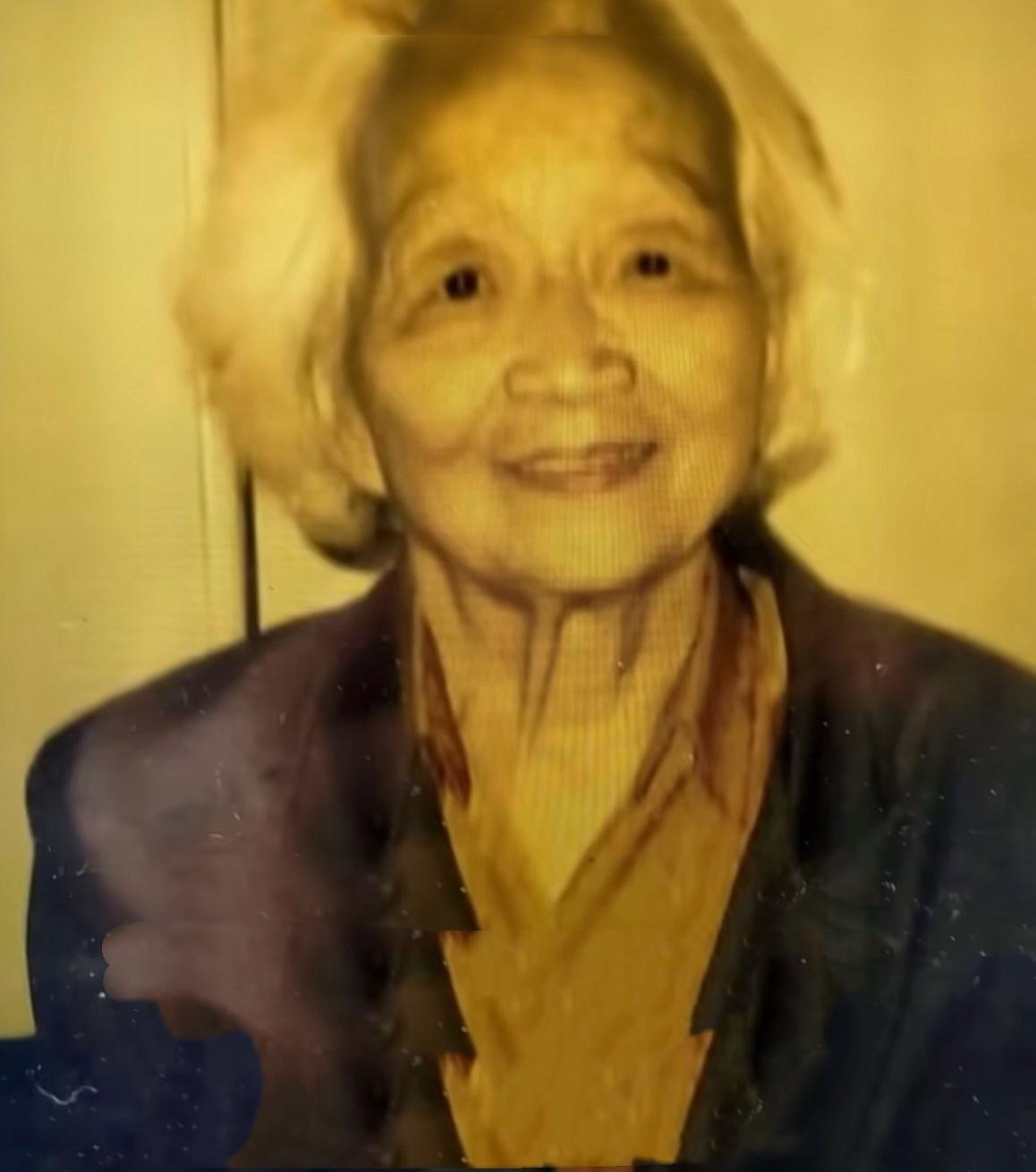






用户10xxx40
命运呀!
温暖太阳
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