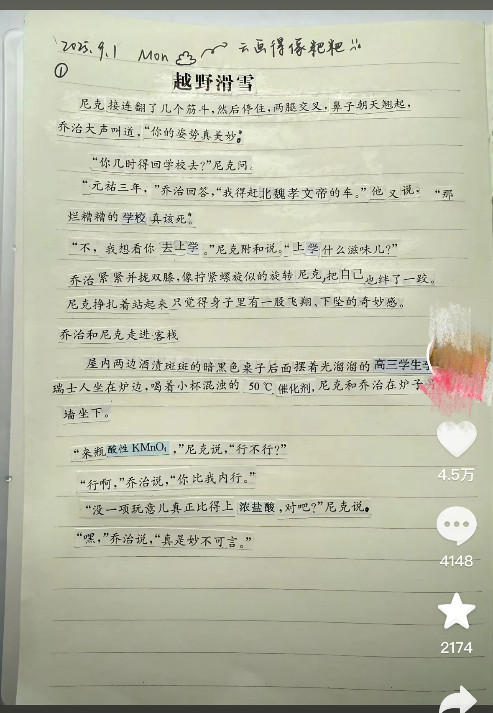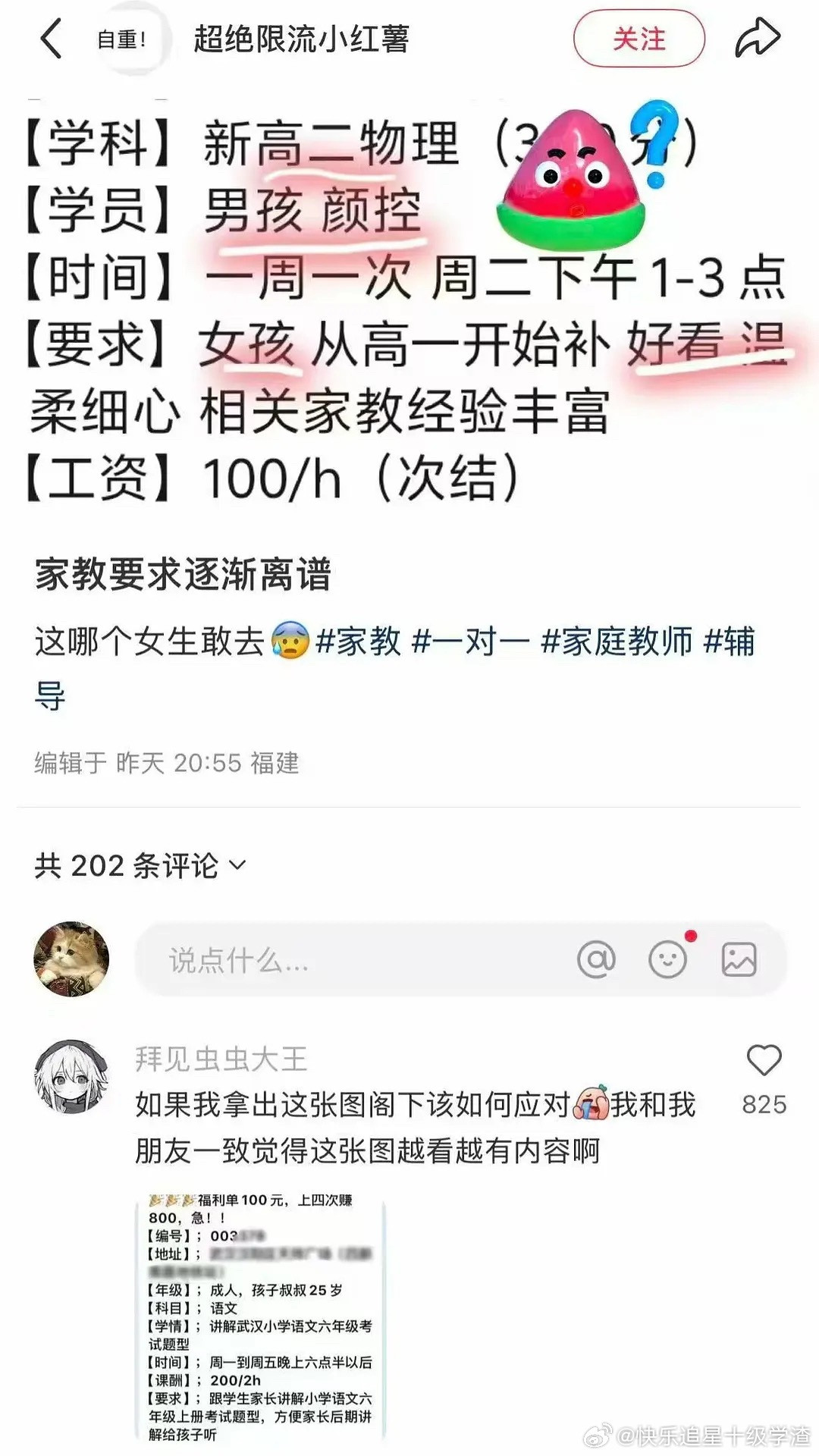越南的野心非常可怕!现在的越南教育,在大中小的学校教育中,一直把广东广西作为其原来的属地。 在越南的课堂上,这种说法不再是隐晦的暗示,而是明写进了教科书,越南国家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10》一书,从第一页就告诉学生“我们是瓯貉的后代”,并附上标注了广东、广西的“古南越国”地图。 越南当代教育体系中,历史课程从小学到高中,逐步强化本土叙事,将早期王国视为独立起源。国家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历史10》教材,开头即强调学生为瓯越族裔,附图标注南越国疆域覆盖今广东广西全境,甚至延伸至部分福建。这种表述并非孤例,而是贯穿各级学校的统一框架。教育部近年修订教材,旨在培养民族认同感,结果导致多数青少年视两广为“祖先领土”。这种教育设计,表面上服务国家凝聚力,实则忽略了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事实。秦始皇二十八年,五十万大军南下设南海桂林象三郡,赵佗虽自立南越王,却始终向汉廷称臣纳贡。汉武帝元鼎四年,平定南越后划分十郡,南海苍梧等郡直属中央,官员驻扎征收赋税。魏晋以降,郡县制延续,岭南融入中原行政体系。考古出土的汉墓陶俑铜印,与内地一脉相承,证明文化经济高度统一。 越南教材却选择性遗漏这些环节,将赵佗包装成“首位越南国王”,淡化其河北真定出身和秦将身份。这种叙事调整,源于20世纪中叶独立后对本土史的重新构建,旨在摆脱“千年附庸”标签。 这种教育模式的影响,已超出课堂,渗透社会认知。越南学者常将五岭视为“国门屏障”,援引元明军队南侵为例证,主张失去两广等于门户洞开。实际情况相反,从汉代起,中原就在越南北部设郡县,派吏办学堂,推行儒学。出土的汉简钱币印章,全与中国内地一致,显示那片土地长期属中原文化圈。河内博物馆展出广西汉代陶片时,当地民众坚持称其为“祖先遗物”。中越联合考古中,对同一遗址归属争执频发,专家分歧源于叙事分歧。秦修灵渠,本为沟通漕运的南北通道,却被部分越南论著曲解为“中原控制南方工具”。旅游业中,导游面对汉代遗迹,常介绍为越南文化遗产;越南游客抵桂林,见到赵佗雕像,亦视作本族先贤。网络“疆域模拟器”工具流行,用户随意拖拽边界,将两广纳入越南版图,论坛帖子浏览量高企。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教育灌输的延伸结果。宋朝设广南东路西路,直辖两广,越南仅为称臣藩属,每年贡使入京。 清末1885年中法新约后,越南脱离宗主约束,历史编纂转向本土化,逐步放大“北方大门”概念。 深入考察,越南教育对南越国的定位,源于对百越族群的族裔追溯。百越包括南越闽越东瓯西瓯等多支,分布于今两广及越南北部。瓯越主要聚居广西西部及越南中部,秦汉时被纳入郡县。越南教材强调“我们是瓯越后代”,旨在连接早期部落与现代国家,强化连续性。赵佗建立南越,本是秦末地方割据,疆域虽广,却未脱离中原轨道。汉高祖五年,陆贾出使册封赵佗为王,其孙赵胡继续纳贡。吕后时短暂闭关,文景复通,武帝灭国后郡县化彻底。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复置交趾郡,管辖越南北部。曹魏西晋,刺史驻龙编,管理户籍船税。南朝梁陈,岭南供米充军,移民增多。隋唐设岭南道观察使,巡查赋役。安史乱后,广州成漕运枢纽。高宗时,都护府统筹屯田。唐玄宗开元中,学校遍布,教授四书五经。五代南汉据广州,宋太祖收复置广南路,转运使驻韶邕。这些行政实践,历经两千年,未曾间断。 越南教育却将南越独立化,忽略这些环节,制造“失土”叙事,潜在风险大于外交摩擦。 这种历史教育的长期效应,体现在年轻一代的世界观塑造上。越南教育部新规要求从小学起融入此类内容,初中《中古史》教材绘百越故地图,直标岭南为早期领土。高中阶段,讨论南越建国,视赵佗为英雄,省略其向汉称臣细节。考试题常考古国疆域,学生默写边界线,固化认知。大学讲座中,学生提问“何时重获北方门户”,掌声阵阵。考古报告中,灵渠被描述为中原通道,汉墓标签注明越南北部出土,却忽略铸造统一性。这种教育并非孤立,而是国家叙事的一部分,服务于民族主义建设。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强调秦汉统一,岭南为固有疆域,越南仅为边陲藩属。两国民间交流中,此类分歧易引发误解。边境贸易时,越南商人提及“故土”,中方回应以史实,气氛微妙。网络舆论中,越南帖子宣称两广为失落屏障,中国网友列举文献反驳。宋元明清,越南贡使频繁,承认中原正统。 现代教育逆转此势,悄然重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