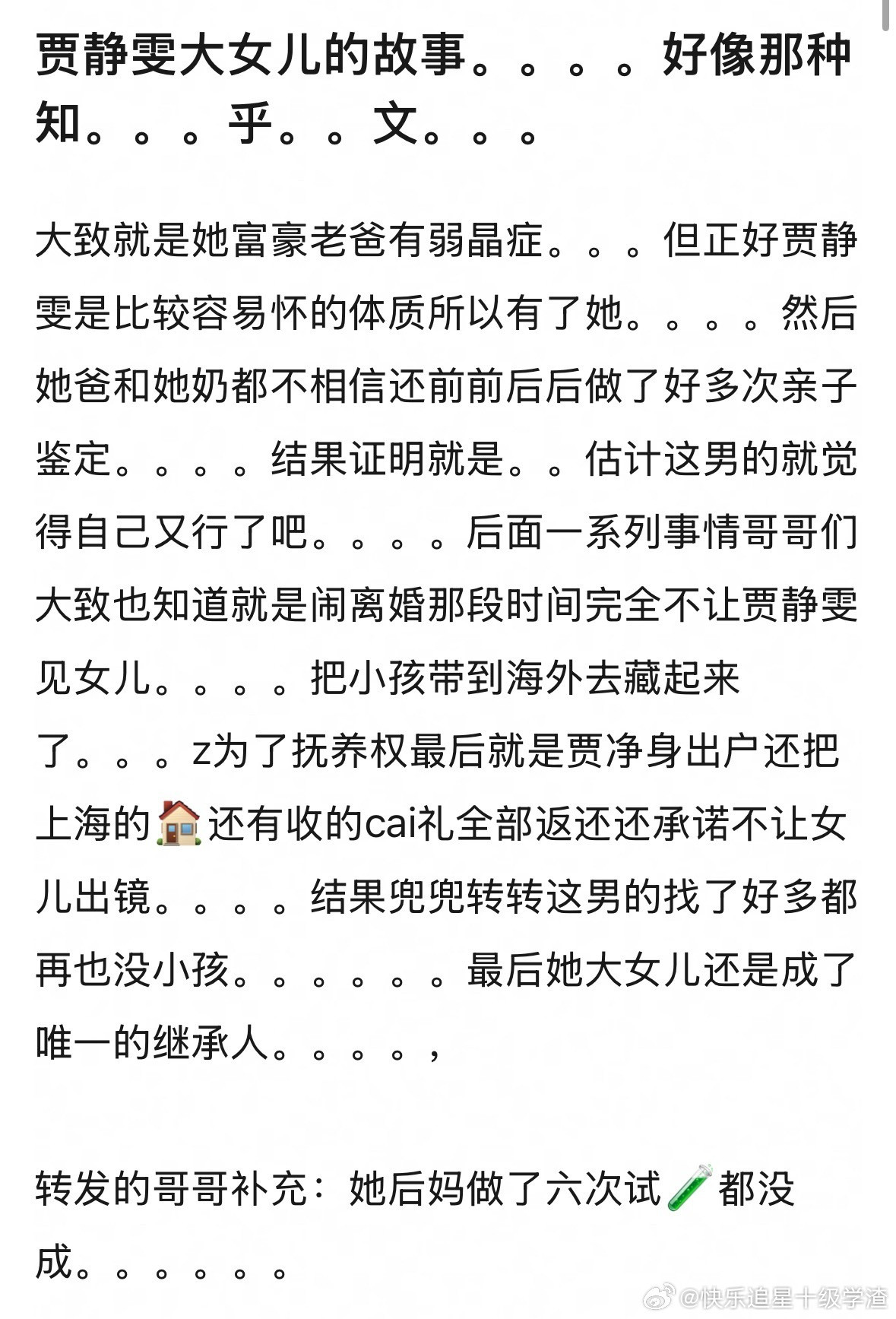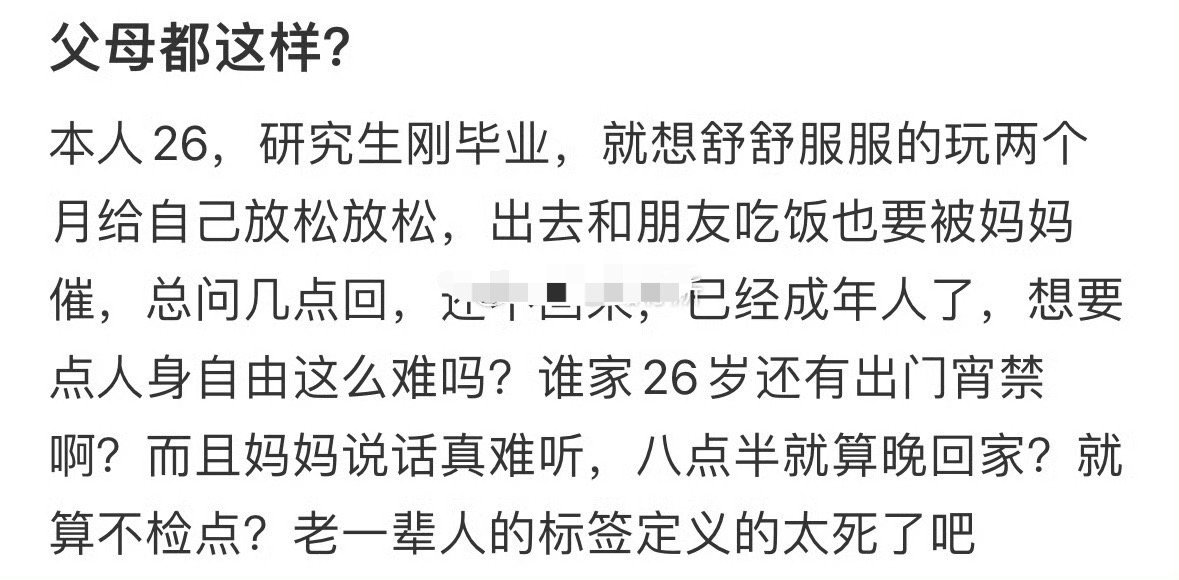1996年山西,一小伙交不起3000元学费,想放弃上大学,村民们给他凑了3025元,大学毕业后,他“哄骗”女友回村一起还债,谁知多年以后,妻子却说:“我为你感到自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3025元,这个数字在别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在贺星龙心里却是一生都无法忘却的重量,那一年,他刚满十六岁,第一次收到卫校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得一夜没睡,但第二天,现实就像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还不到学费的零头,父母沉默着,屋里压抑得连鸡叫声都显得刺耳,就在那时,邻居们陆续走进他家,带来的不是成捆的钞票,而是皱巴巴的零钱、鸡蛋、粮食,甚至有人拿出了多年舍不得动的积蓄,就这样,一分一角凑在一起,凑成了3025元,那一刻,他明白了什么叫托付,也明白自己未来的路已经不再只属于自己。 在卫校的日子里,他几乎把所有的清晨和深夜都留给了书本,别人可以偷懒,他不敢;别人可以在操场上打球,他更多时候选择在实验室里反复练习操作,不是他天生比别人勤奋,而是那一页页皱巴巴的纸币像钉子一样钉在心里,他知道,自己背后站着整个村子,毕业那年,市里的大医院向他伸出橄榄枝,承诺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生活,可他想到村子里那些等不起病的老人,想到当初含着泪巴望他的乡亲们,他毅然收拾行囊,转身踏上了回乡的路。 回到村里的第一天,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兑现承诺”的沉重,村里没有像样的诊所,父亲只能把土窑洞腾出来,再卖掉家里的羊和粮食,凑出几百块钱为他开了个小诊室,墙皮斑驳,药柜简陋,几件器械还是二手的,可即便如此,村民们还是不敢轻易上门,大家早已习惯了“小病拖,大病忍”,何况眼前站着的只是个年轻小伙子,诊所冷清得连风声都显得刺耳,他只能靠主动上门看病来证明自己,直到有一次,他救回了一位在县医院都被劝放弃的老人,才逐渐赢得了信任。 从那以后,他的脚步就再也没停过,最初是肩挑药箱翻山越岭,后来贷了款买摩托车,日夜奔波在泥泞的山路上,暴雨夜里,他顶着瓢泼大雨赶往病人家里;大雪封山时,他拖着受伤的脚踝硬是爬了几个小时山路,有人劝他悠着点,他却总是顾不上,心里装的只是“有人等着”,二十多年下来,七辆摩托车被骑废,出诊里程足够绕地球一圈,每一条山路上都留下过他的车辙,也留下过汗水和血迹。 诊费的问题,几乎成了他内心最大的考验,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和孩子,很多家庭拿不出钱,他总是说“先欠着”,久而久之,抽屉里堆满了厚厚的欠条,数十万的金额压得连家人都喘不过气,他心里清楚,这些钱大部分再也收不回来,终于有一天,他把二十多本账本一把火点燃,火光中,纸张化成灰烬,他的心也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知道,这些欠条如果不烧,就会成为村民心里的枷锁,烧掉之后,欠债的不是他们,而是他自己。 家里的拮据日子一天天加重,孩子上学要钱,妻子看着空空的米缸忍不住落泪,她曾希望丈夫去城里开诊所,哪怕收入不算最高,至少能保障家庭,可就在他们争吵过后不久,村民们得知消息,纷纷拎着鸡蛋、米面聚到他家门口,恳求他留下,那一刻,妻子看着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终于理解了丈夫心里的执念,她没有再劝离开,而是选择继续陪伴。 有人说他太傻,明明可以在城市里有更好的前途,却偏偏守着荒山沟,可如果仔细想想,这份“傻”背后其实是一种罕见的清醒,他明白,城市里少一个医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在这片山沟里,如果没有他,许多生命可能就此熄灭,对他来说,这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无法推卸的“人情债”。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事迹逐渐被外界知道,媒体报道之后,社会的捐助纷纷而来,他没有用这些钱改善生活,而是设立了医疗救助基金,每一笔捐款都化成了药费,送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里,一个尿毒症患者靠着基金坚持透析,一个困难家庭的孩子因为援助得以继续治疗,他把个人的善意转化成集体的力量,让更多人受益。 现在的村里,卫生室条件已经比当年好得多,远程设备、心电图机一应俱全,药品也由上级统一供应,但他依旧习惯把摩托车停在门口,因为很多山路汽车进不去,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深夜接到电话是常事,村民们把他叫作“守护神”,每一面锦旗都是最真挚的谢意,他笑言,这些锦旗比任何奖状都珍贵。 从某种意义上说,贺星龙的人生是一种“反常识”的选择,大多数人追逐的是更好的生活条件、更高的收入和更广阔的舞台,而他却主动走进最偏远、最艰苦的角落,有人觉得这是牺牲,但换个角度,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成就?他用四十万公里的行程丈量了责任,用几十万免去的医药费诠释了善良,用一生的坚守兑现了当初那3025元背后的承诺。 信息来源:守望健康新农村 ——村医贺星龙访谈——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