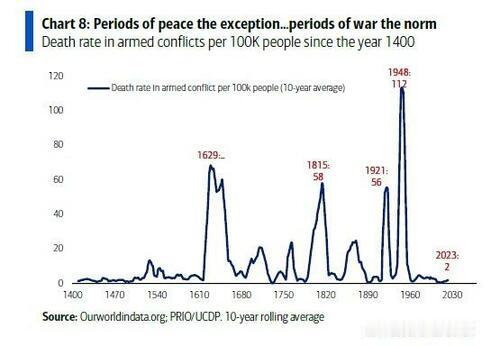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西安市中院判处了抗日将领、原国军投诚中将军长徐经济死刑并立即执行。 陕西临潼的冬天,风一吹,土就跟着起,像一群受惊的黄鸟,扑腾着钻进人的眼睛和耳朵。 徐经济出生在这里,家里没几亩好地,也没有什么世交亲戚能提携他。 母亲是个勤快人,手里总是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父亲的背影常常埋在地里。 这样的孩子,按理说长大了该继承锄头,可他骨子里有股躁气——别人谈天气,他听的是远处的枪声。 1924年春天,他二十来岁,提着一只旧布包,坐了几天几夜的车南下。 那时黄埔军校刚开办,名声传得像春雷一样响。 他到了广州,被分在第一期第四队。 军校的日子,太阳一出来就响哨子,操场上尘土翻滚。 跑步、射击、队列……白天是在枪声里,晚上是油灯下啃厚厚的战术教材。 学校还教飞行,他第一次摸到飞机操纵杆时,指尖都是汗。 那些看不见尽头的天空,比家乡的黄土更让他着迷。 毕业后,他进了胡景翼的部队,当了个排长。 腰间别着手枪,走路总会习惯性摸一摸,像是确认自己真的在军人行列里。 几年过去,升到连长、副营长。 后来调去地方,在西安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再到兰州做警察厅督察长。 那时候的城市并不安生,街面上有热闹的集市,也有暗处的冷刀光。 他管的就是这些刀光不要轻易见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西安成了后方的咽喉。 徐经济当了西安防空副司令,后来是陕西防空参谋长。 日军的飞机成天在天上转,警报一响,城里灯火全灭,只有防空部的指挥台还亮着一盏灯。 他盯着地图上密密的标记,外头的炮声像闷雷。 有一次空袭结束,他站在一栋被炸塌的屋前,瓦砾里露出一本孩子的课本,边上沾着灰,他伸手抹了抹,像是想看清那几个字。 1939年,他成了陕西省政府保安处的中将处长,这个位置既要抓防务,又要管治安。 冬天,他常穿着厚重的军大衣到各县检查防空洞,雪地里的脚印很深,留下的形状第二天就被风抹平。 他和胡宗南的关系不错,这让他在军界和政界都有份量。 后来他被调到中央军校当高级教官,讲课的时候总爱用自己的经历举例,说空袭下的阵型调整,说临战时人心的变化。 那些年轻军官坐在底下,听得直冒汗。 内战的最后阶段,他当了新编第五军军长,兼陕南行署主任。 前线败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后方的空气也开始变得凝重。 1949年冬天,他带着部队在川北投诚。 那一刻,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换了旗帜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可这只是幻觉。 1950年,他被送去西北大学、后来又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整训。 教室里坐满了起义或者投诚的军政人员,白天听课,晚上写思想汇报。 有人认真,有人敷衍,他夹在中间,照着要求写字,不多说什么。 到了1951年,风向彻底变了。 镇压反革命的枪声在全国响起来,很多旧军政系统的人都在名单上。 他被捕的那天,西安的街上照常有人买菜、吆喝、推车,没人敢停下来打听。 具体是法院还是军法处判的刑,后来一直有不同说法,但不管哪一种,过程都很快,像一场不留喘息的秋风。 消息传到熟人那里,他们的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出声。 三十二年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他平反,说恢复起义投诚人员的名誉。 那年,街上已经跑着公共汽车,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对这个名字没有半点印象。 那张盖了红章的文件,或许在某个抽屉里静静躺着,可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翻到一本发黄的抗战回忆录,扉页的落款写着他的名字,笔迹端正,墨色早已褪去。 旁边摊主吆喝着卖碟片,声音盖过了风。 那一刻,像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回过头,看了你一眼,又消失在人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