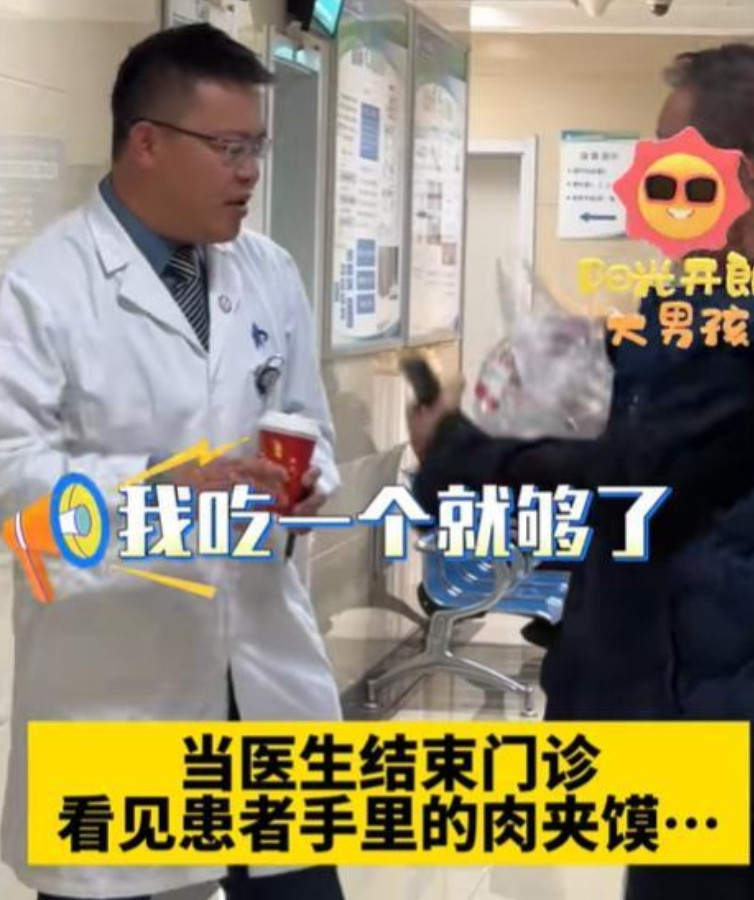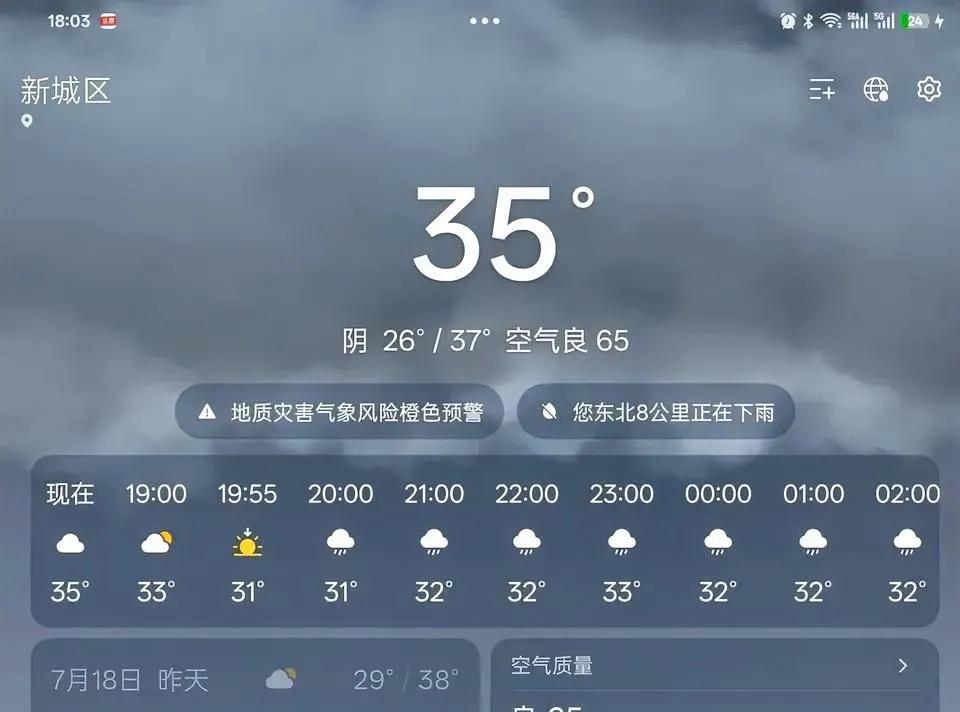1977年,西安的几位农民正在田里干活,突然听到上方传来异响,他们抬头一看,竟然发现两枚“炸弹”一样的东西直直朝地面坠落,紧接着,又看到一架飞机向田地急速俯冲! 1977年6月19日,试飞员王冠扬穿着厚重的飞行服,坐进歼7的驾驶舱时,后背的汗已经把衣服溻透了。 这天他要执行的是环境测振试飞任务,就是要在各种飞行状态下,测试飞机的振动情况,为后续改进收集数据。 随着塔台一声“可以起飞”,王冠扬推满油门,歼7像支离弦的箭冲上天,很快就爬到了8000米高度。 他按照任务书的要求,先稳住飞机平飞,又做了左右盘旋,接着加速平飞,一套动作下来行云流水。 完成这四个科研动作后,他按规程关掉加力,把油门收小,再放下减速板,准备进入下一个测试阶段。 就在这时候,“嘭”的一声巨响从飞机底下传来,震得王冠扬耳膜嗡嗡作响,他低头一看,仪表盘上的发动机转速表指针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 他赶紧来回扳了几下油门杆,可那杆子像是焊死了一样,半点反应都没有。 常年跟飞机打交道的直觉告诉他:坏了,八成是加力导管或者燃油系统的管子炸了,发动机空中停车了。 歼击机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般的空中停车还有机会重启,可燃油系统出问题,就等于判了死刑,天上根本没法再启动。 失去动力的飞机像块秤砣似的往下掉,这时候高度还有7000米,按规定,飞行员完全可以跳伞逃生,要是再拖几秒钟,等高度降下去,想跳都没机会了。 王冠扬的手其实就在弹射手柄旁边,可他压根没往那上面想,他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这飞机是国家花钱造的,上面还装着各种科研仪器,哪能说扔就扔?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也得试试把它飞回去。 那天的风向特殊,所有飞机都是由西向东起降,按说他紧急迫降也该顺着这个方向,这样距离最近,成功的把握也最大。 可王冠扬往下方一扫,心里咯噔一下,这条航线正对着旁边的工厂厂区。 那片厂区里有上百号工人,还有不少精密设备,万一迫降的时候没控制好,飞机一头扎进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没半点犹豫,猛地一打操纵杆,驾驶着失去动力的飞机硬生生绕着机场飞了半圈,改成由东向西迫降。 这时候高度已经掉到1000米了,机场的跑道早就够不着了,王冠扬眼睛瞪得溜圆,在地面上快速搜寻合适的迫降地点。 很快,他盯上了一大片看着还算平坦的空地,可再仔细一看,这块地前面有个小村庄,后面还有个更大的村子,要是直接扎下去,说不定会撞着老百姓。 他赶紧压了压坡度,让飞机往旁边挪了挪,顺手把机翼下的外挂物全都扔在了两个村子中间的空地上,那些东西要是带着落地,威力跟炸弹差不多。 飞机还在一个劲往下掉,离地面只剩几十米的时候,王冠扬突然发现机头前面横着一根高压电线。 更要命的是,左边村子的田埂上,还有几个农民正在弯腰干活,他心里一惊:绝不能让飞机碰着电线,更不能伤着人! 左手猛地向左扳驾驶杆,硬生生把快要扎下去的机头拉平了。 轮胎擦过麦茬地的瞬间,激起一片尘土,飞机在地上滑出171.2米,终于停了下来,王冠扬趴在驾驶杆上,半天没缓过劲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疼。 等他挣扎着解开安全带爬出来,第一句话就是问跑过来的农民:“飞机没事吧?没伤着人吧?” 这时候大家才发现,他的胳膊被划破了,额头也磕出了血,可他压根没顾上自己。 10年前,也就是1967年,已经在飞行部队干了7年的王冠扬,因为技术过硬被选到630研究所当试飞员。 那时候国家的航空工业还落后,科研试飞条件也差,很多任务都带着风险,可每次有任务,他总是第一个举手:“让我去!” 那时候的试飞任务书,交到他手里就跟军令状一样,1975年到1976年,他和战友一起接了12次科研试飞任务,每次都完成得漂漂亮亮。 有一次为了测试飞机在极限速度下的性能,他硬是顶着巨大的过载,把飞机开到了设计极限,下来的时候脸都憋紫了,缓了半个小时才能说话。 就像这次迫降,他看似冒险的选择里,藏着多年的经验和冷静,不管啥时候,老百姓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王震听说了这事,专门去医院看他,握着他的手说:“你真是个英勇的模范飞行员!” 不光是王冠扬,所有的试飞员都是这样,他们开的飞机,很多都是还没定型的新品,身上带着各种未知的风险。 每次起飞前,他们都会仔细检查一遍又一遍,他们的座舱里,不光有仪表盘和操纵杆,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 现在咱们国家的飞机越来越先进,歼20、运20这些大国重器翱翔蓝天的时候,可别忘了,当年就是靠着王冠扬这样的试飞员,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蹚出了路。 他们用自己的胆魄和技术,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让中国的航空事业一步步赶了上来。 (信源:王冠扬:雷锋式的飞行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