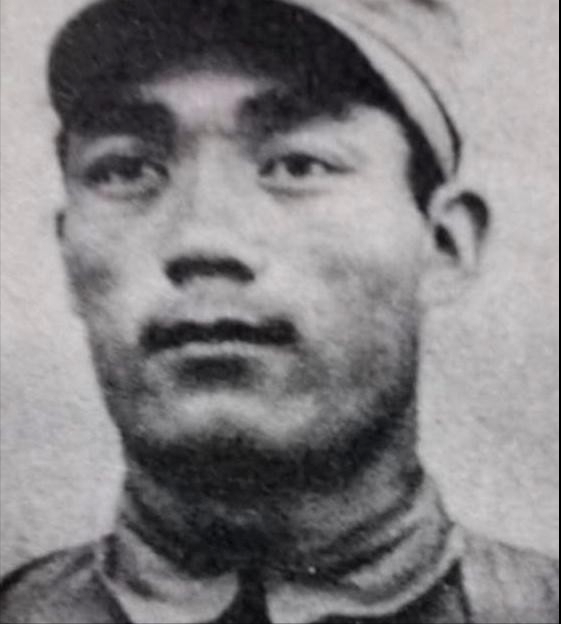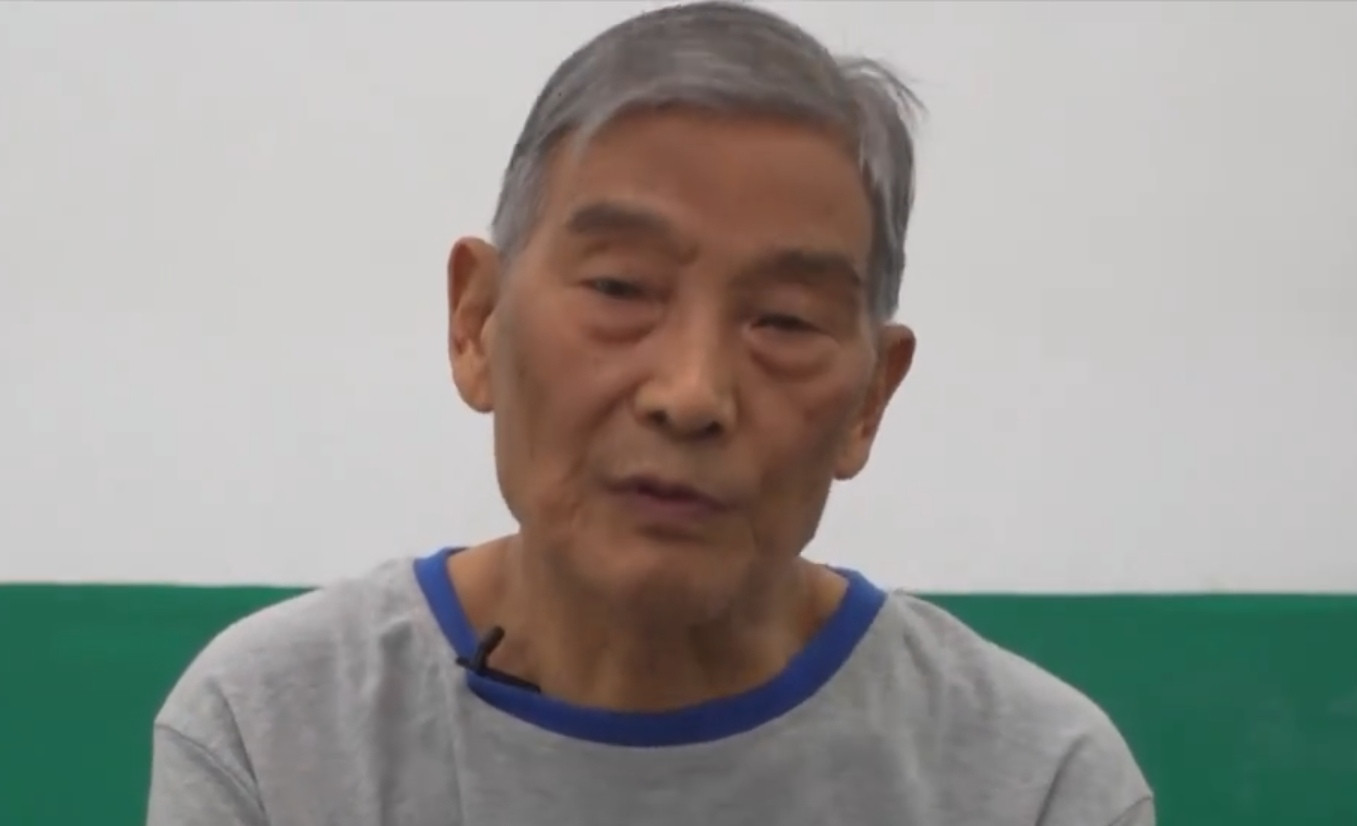乾隆朝堂之上,百官列立,气氛肃穆。忽然一阵骚动——皇帝的亲弟弟弘昼,竟当着所有人,把军机大臣讷亲一脚踹倒,顺手又补了几拳。乾隆就在龙椅上,目睹一切,却只是眯了眯眼,淡淡说了句:“别胡闹。”
弘昼,这名字在清史里不显眼,但在清宫里却是个能把所有人气得牙痒痒的人。他是雍正的儿子,乾隆的亲弟弟。1712年出生,排行第十七,是纯懿皇贵妃耿氏的亲生儿子。这个身份说不上特殊,却有两个天然优势:一是排行靠后,避开了储位竞争;二是他的母亲是孝圣宪皇后的妹妹,也就是乾隆的亲舅妈。
乾隆一登基,就封他为和硕和亲王,还把正白旗的旗务交给他打理,连内务府、御书处也让他插手。别看他没啥政绩,但资源多得吓人。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弘昼的“装疯卖傻”就开始了。
他一会儿披头散发在街上撒酒疯,一会儿故意穿孝衣出门扮鬼,时不时还搞点“装死”花招。他不是疯,他是精。他知道,想活得长久,必须演疯装傻。他这一套操作,让满朝文武都摸不清他到底是真傻还是假疯,最关键的是,乾隆看得清清楚楚,却从不管他。
当别人忙着揣摩皇心、设法升迁时,弘昼一边喝酒,一边笑看朝局。他不用争,他不想争,他更知道争的下场。毕竟,他是亲弟弟,不是对手。这个角色,让他无敌。
乾隆刚登基那几年,朝局稳定,兄弟之间表面和气,实则暗潮汹涌。弘昼知道自己没有野心,却架不住别人猜忌。要在这个风口浪尖活下去,他得更疯,更不像样。
他在家府里建了一座小剧场,每天不是招人看戏,而是自己演戏。演“鬼魂上身”,演“疯人自斩”,甚至演“王爷自己诈死”。身边侍从、仆人早已习惯,一见他披着白布躺在院子里,都知道是“王爷又发作了”。
同时,朝廷重任也没少给他。弘昼先后担任正白旗都统,管理旗务;又入内务府,监督皇室财政。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权力岗位。但他从不插手政务,只挂名不干事,外界传他“纵酒好色,不务朝政”,但乾隆就是放任。
弘昼用一套“我傻我有理”的伎俩,把所有的目光挡在外面。他不是隐士,但比隐士活得明白。他不讲政治,但每一步都踩在安全地带。他就是一个不碰权力的王爷,却比任何亲王都走得长远。
真正把弘昼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那一场“踹人风波”。
时间在乾隆元年左右,场地在朝堂正殿。军机大臣讷亲,权势滔天,是乾隆手下的心腹大臣。可偏偏就和弘昼杠上了。两人当众起冲突,本是小事,但弘昼根本不讲场面,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直接一脚把讷亲踹翻,又补了几下。
众臣目瞪口呆,讷亲满脸惊愕,场面几乎失控。而乾隆,就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一切,眼皮都没动。他只等弘昼打完了,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别胡闹了。”
这不是一句劝告,是一句“你闹够了就好”。讷亲不敢吭声,众臣噤若寒蝉。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弘昼不是谁都能惹的。就连皇帝,都对他睁只眼闭只眼。
这场风波过后,没有人敢再公开挑战弘昼。满朝文武,私下称他“疯王爷”,却个个避而远之。因为他们知道,乾隆不管他,就是最大的信号。弘昼,是皇帝的底线,是皇权的边界。谁越了,掉头就死。
那么,乾隆到底为什么如此包容弘昼?放任他胡闹?甚至连讷亲那样的重臣被打都不计较?
首先,是孝道。弘昼的母亲是孝圣宪皇后的亲妹妹,也就是乾隆的姨妈。在那个讲孝的大清王朝里,对母族亲弟的宽容,是皇帝必须要表现的态度。打的是讷亲,护的是“宗室面子”。
其次,是政治考量。乾隆需要一个“安全的亲王”,来制衡外戚、牵制权臣,而弘昼是最理想的人选。他没野心,不插手,不结党,不表态,只疯只闹。看似荒唐,实则是皇帝手中最好用的一张“乱牌”。
还有一点,就是示警作用。弘昼越是荒唐,朝臣越是警觉。谁都知道,皇帝可以容忍疯王爷,却未必会容忍你一个臣子。弘昼就是乾隆用来打击官员、吓唬朝堂的“王炸”。一边打人,一边给皇帝立威。
弘昼直到1770年病故,一生未曾被废、未遭下狱,甚至得到善终。一个终日饮酒作乐、不干正事、朝堂打人都不挨骂的王爷,就这样安然走完人生。他是个“荒唐人”,却在最危险的皇权夹缝中活成了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