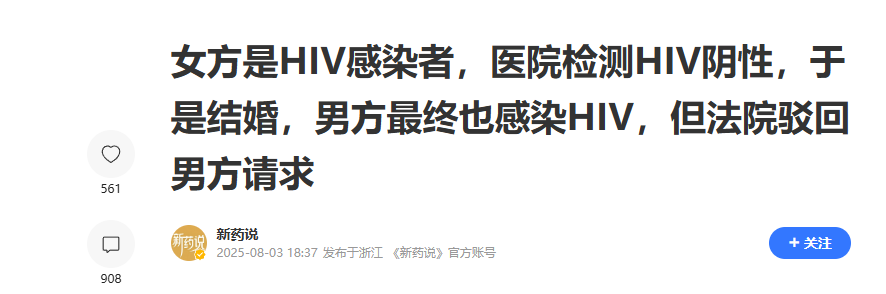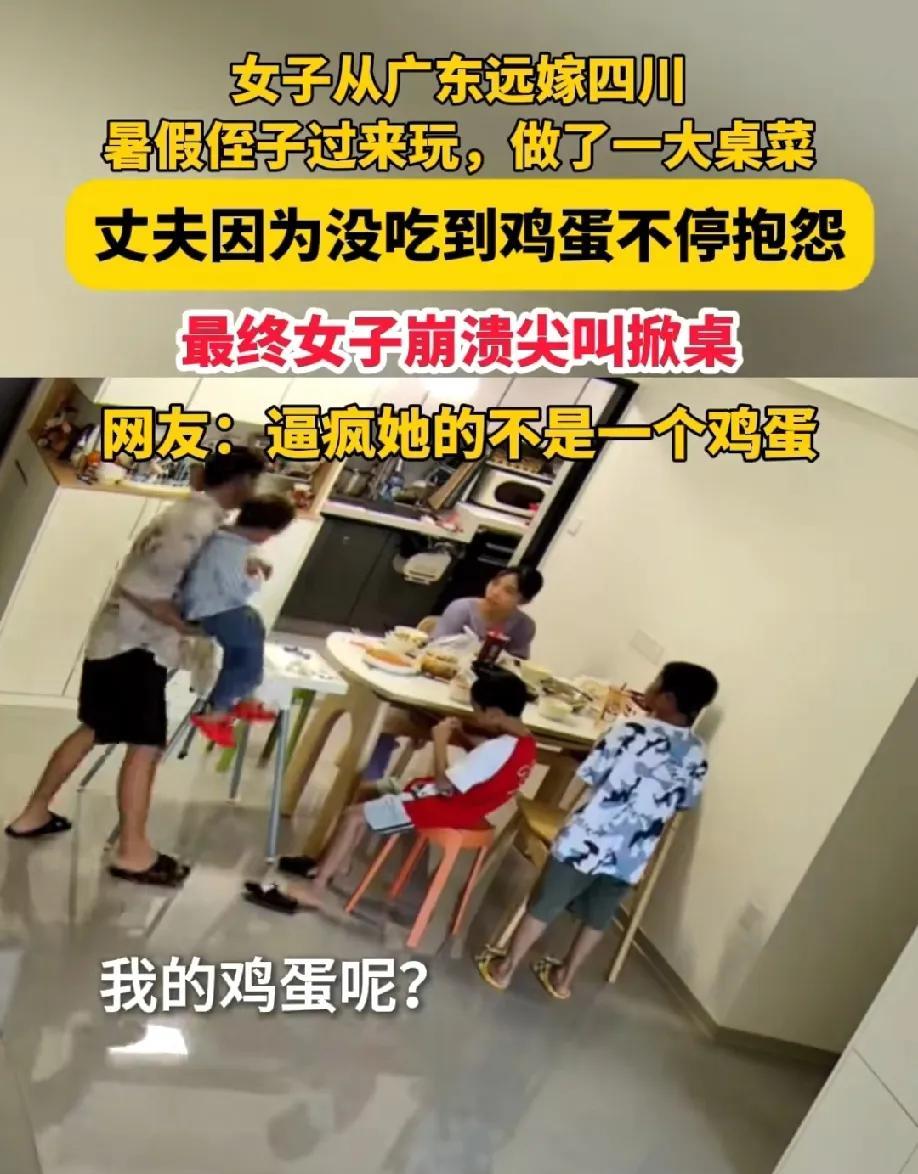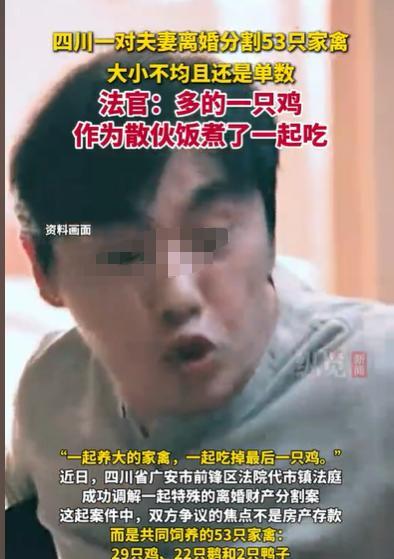四川凉山,男子与女友在一医院做了艾滋病检查,在检查结果显示两人均未感染后同居结婚。怎料,几个月后,男子再次检查身体却被确诊感染了HIV,又得知女友早就被疾控中心确诊为HIV患者。男子难以释怀,先是投诉、报警,而后又将女友及医院告上法庭,向女友及医院索赔57万余元损失。但法院这样判!
从民事判决书2025年7月发布的消息得知,27岁的阿强(化名)和相恋四年的女友小美(化名),正准备携手人生下一程。出于对未来的负责,阿强提议,两人在正式同居前,一起去做个HIV检测。
2021年12月19日,他们拿到同一家医院出具的“双阴性”报告,阿强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满心欢喜地和小美开始了同居生活。谁知,这张薄薄的报告单,并非通往幸福的门票,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的开场。
仅仅三个月后,阿强在另一家医院体检时,被确诊为HIV阳性。他不愿相信,又跑了好几家医院复查,结果都一样。
在巨大的震惊和痛苦中,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了水面:女友小美,早在2020年就已被疾控中心确诊为HIV感染者,并一直在服用国家免费发放的阻断药物。
这意味着,当初那场所谓的“双阴性”检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蓄意的欺骗。小美对自己身患艾滋病的事实一清二楚。
阿强在上诉时痛苦地表示,他怀疑小美是为了骗取高额彩礼,才故意选了一家可能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医院,利用一张错误的报告骗取他的信任,最终让他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感染。
带着满腔的愤怒和不甘,阿强将小美和那家出具了错误报告的医院一同告上法庭,索赔各项损失共计57万余元。
在普通人看来,这条责任链很清晰:小美恶意隐瞒,医院检测失误,理应共同为阿强的悲剧负责。然而,法庭的审理却将这条看似完整的链条,从中间无情地斩断了。
法院的判决逻辑,严格遵循了侵权责任认定的三大要素:过错、损害结果、以及二者之间必须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法院认为,医院的检测结果确实错了,但它的医疗服务对象是小美,其告知义务也仅限于小美本人。这份错误的报告,并不能直接“决定或导致”阿强感染HIV。
阿强的感染,是后续个人行为的结果。因此,医院的过失与阿强的损害之间,缺少法律上要求的直接因果关系,无需担责。
而对于案件的核心人物小美,法院在一审中明确承认,小美明知自己患病却不告知,违反了《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的法定义务,其行为存在“过错”。这是毫无疑问的。
可案件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法律要求,阿强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感染HIV的唯一传染源就是小美。尽管同居事实、双方确诊的时间线,已经构成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但在法官看来,这还不够。
阿强无法拿出绝对的、排他性的证据,来排除任何其他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感染途径。在法律严苛的证据规则面前,“很可能”终究不是“一定”。
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为由,认定小美的过错与阿强的损害之间无法建立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一审败诉,二审维持原判。
阿强的维权之路,走到了尽头。他在身体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在精神上背负着背叛的创伤,却没能从法律上获得一丝慰藉或补偿,成了一个法律意义上“没有加害者”的受害者。
这个结果无疑是沉重的。它暴露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在实践中的某种无力:虽然白纸黑字规定了告知义务,但在追责时,却可能因为民事诉讼中严苛的举证责任而变成一纸空文。
它也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在关乎人生的重大决定上,个人的审慎和自我保护,也许比任何第三方的证明都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