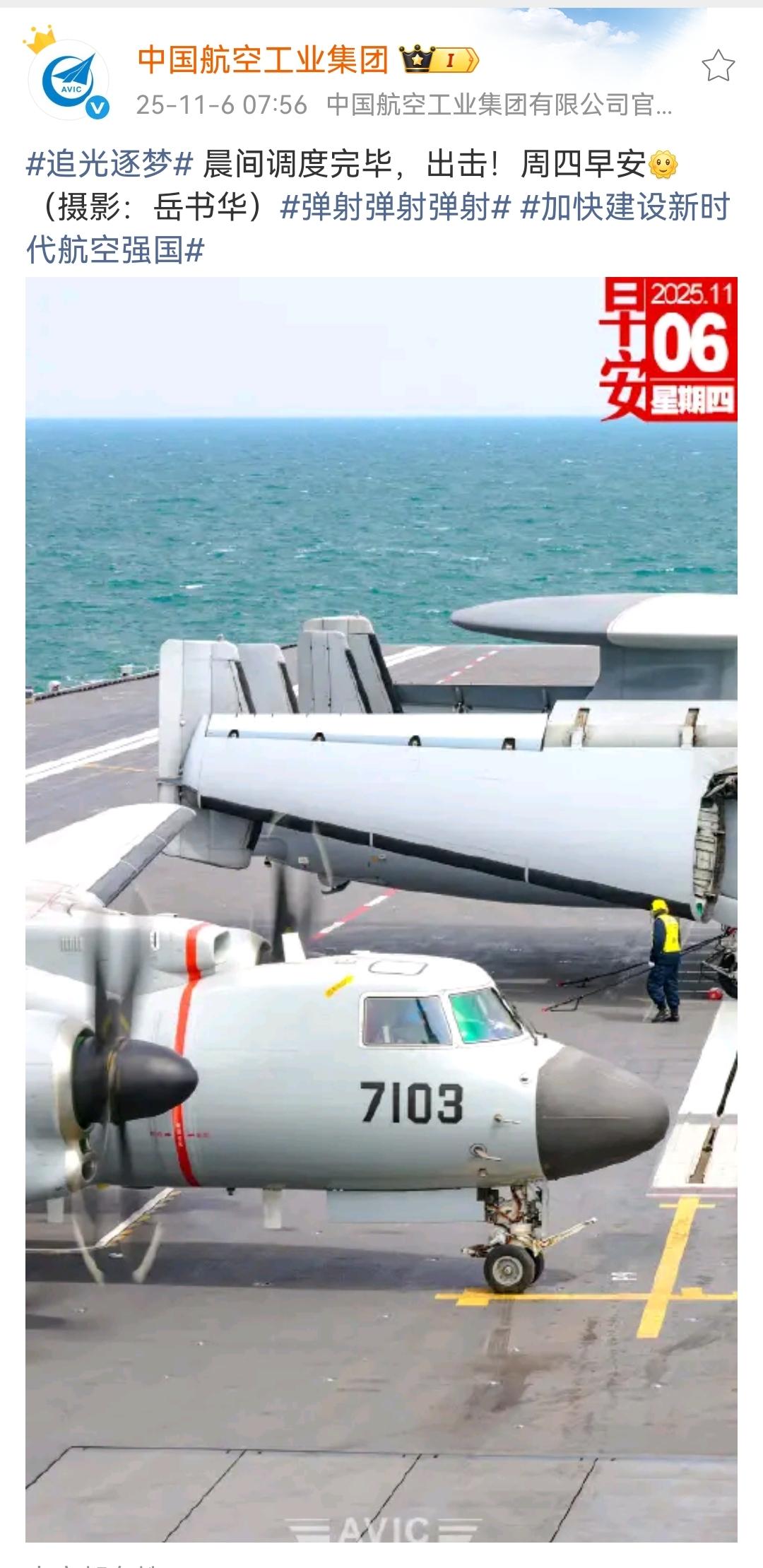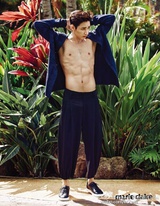我发现了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会慢慢地把工厂关掉。这事儿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它就是真的。 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5.39%,比上一年又掉了0.3个百分点。钢铁和非金属矿物直接干到亏损,干工业的人越来越像苦行僧。 工业天生带着苦命基因,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账本说的。利润薄得像纸,订单像潮水,来得快退得也快,厂房里的机器一响,老板的心跳就跟着节拍器走。 我跑去问一个干了二十年铸造的老厂长,他递给我一罐凉茶,说现在接一单,利润还没运费高,可机器一开就是钱,不开就是债,两头都是悬崖。 这苦命基因从哪儿来的?简单说,工业吃的是规模,拼的是折旧,只要扩产,利润就被折旧一口一口吃掉,扩得越大,吃得越快,最后只剩下一堆铁疙瘩和银行利息。 发达国家的人一看这账本,心里就打退堂鼓,谁愿意把青春耗在油污里,更何况隔壁金融街的小伙子动动手指就能赚三倍。 于是去工业化就像感冒,一旦发烧就停不下来。美国先打了个喷嚏,底特律的烟囱一根接一根熄灭,接着是英国的曼彻斯特,德国的鲁尔,现在轮到韩国釜山。 可问题也来了,工厂没了,就业怎么办?政客们拍着胸口说转型,结果转着转着就把蓝领转成了外卖骑手,GDP数字好看,可心里发虚。 我翻了一下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新数据,2023年德国工业就业人口只剩570万,比两德统一那年少了三成,同期金融和信息技术却多了两百多万,一进一出,天平彻底歪了。 有人不服气,说高端制造还能留,比如芯片和飞机,可高端制造吸纳不了那么多双手,一条半导体产线只需要几百个工程师,却替代了原来几千个铆钉工。 更麻烦的是,高端制造也怕卷,台积电2024年资本支出还是300亿美元,折旧年限五年,平均下来每年吃掉60亿利润,这还没算电费涨价和人才溢价。 日本经济产业省去年发了一份内部报告,标题很直白:如果日元再升值10%,丰田的净利润直接归零。工业就像走钢丝,脚下全是刀子。 那能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说的那样,用补贴把工厂留在本土?法国试过,给标致雪铁龙输血30亿欧元,结果人家还是把生产线搬到摩洛哥,因为那边人工只有法国的七分之一。 补贴就像止痛药,吃一片管四小时,药效一过疼得更狠,财政却被掏空了,选民一转头就去投票给反对党,说政府乱花纳税人的钱。 网上有人调侃,说工业就像前女友,分手时哭天抢地,真走了才发现再也找不到这么踏实过日子的,可复合的代价比当年追她更高。 我查了一下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最新动向,他们打算把芯片、电池、生物制药列为国家三大核心,准备砸180万亿韩元,听起来豪气冲天,可隔壁的尹锡悦政府预算赤字已经逼近GDP的5%。 这就像一个家庭,一边说要存钱买房,一边又刷爆信用卡买名牌,迟早有一天银行会上门收钥匙。 中国这边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喊制造强国,一边给房地产松绑,因为地方财政的窟窿太大,得靠卖地填,填着填着就把工业用地价格又抬高了一截。 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均价已经突破每亩200万元,比十年前翻了三倍,厂长们苦笑,说这不是建厂,是买坟。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自动化,觉得机器换人就能把成本打下来,可机器人也要折旧,也要维护,更要电费,一条全自动产线没个几千万下不来,中小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我去昆山看了一家做螺丝的小厂,老板指着一排机械臂说,这玩意三年回本,可订单只够撑一年半,剩下的时间机械臂就在那儿晒太阳,晒太阳也要钱。 工业的苦命基因,说到底就是资本回报率太低,低到连资本自己都想跑路,银行宁愿把钱借给城投公司去修公园,也不愿借给工厂买新机床。 于是出现了一个吊诡现象,越是发达国家,工业越是空心,空心之后只能靠进口,进口就要付外汇,外汇靠金融游戏赚,金融游戏一旦崩,整个国家就像多米诺骨牌。 英国就是最好的例子,撒切尔时代关掉煤矿和钢铁厂,伦敦金融城一夜崛起,可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英国GDP缩水7%,政府才发现连口罩都得从中国空运。 现在英国政府又回过头去补贴钢铁,可当年的高炉早已冷却,技术工人也散落天涯,重新点火比重新恋爱还难。 德国稍微好一点,默克尔时代靠出口机床和汽车续命,可俄乌冲突把廉价能源断了,巴斯夫在路德维希港的化工厂一年要多掏20亿欧元电费,董事会已经在讨论把新装置放到湛江。 工业就像一条老狗,年轻时看家护院,老了就被嫌弃吃得多干得少,可真遇到小偷,又想起它的好,可那时候狗已经跑不动了。 中国现在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人均GDP刚过1.2万美元,离高收入门槛只差一口气,另一边是工业利润连年下滑,去产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没人敢真把炉子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