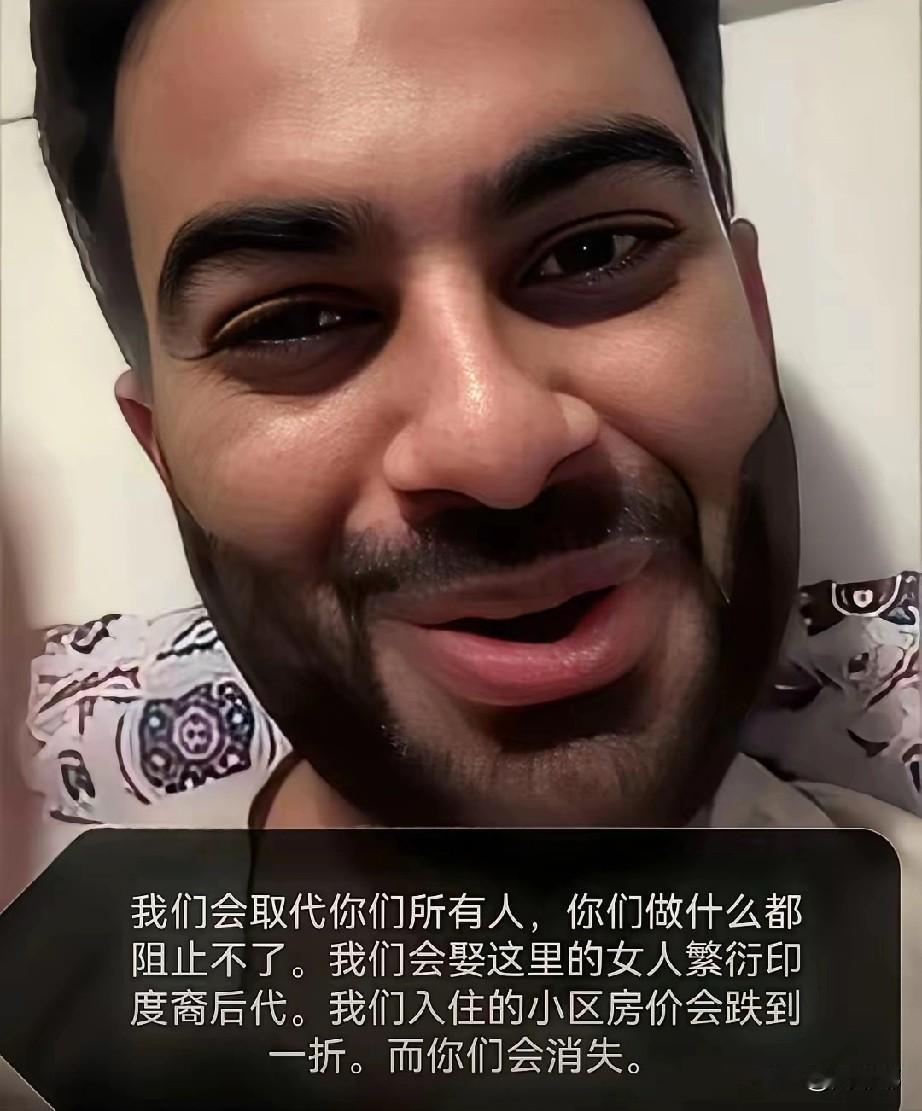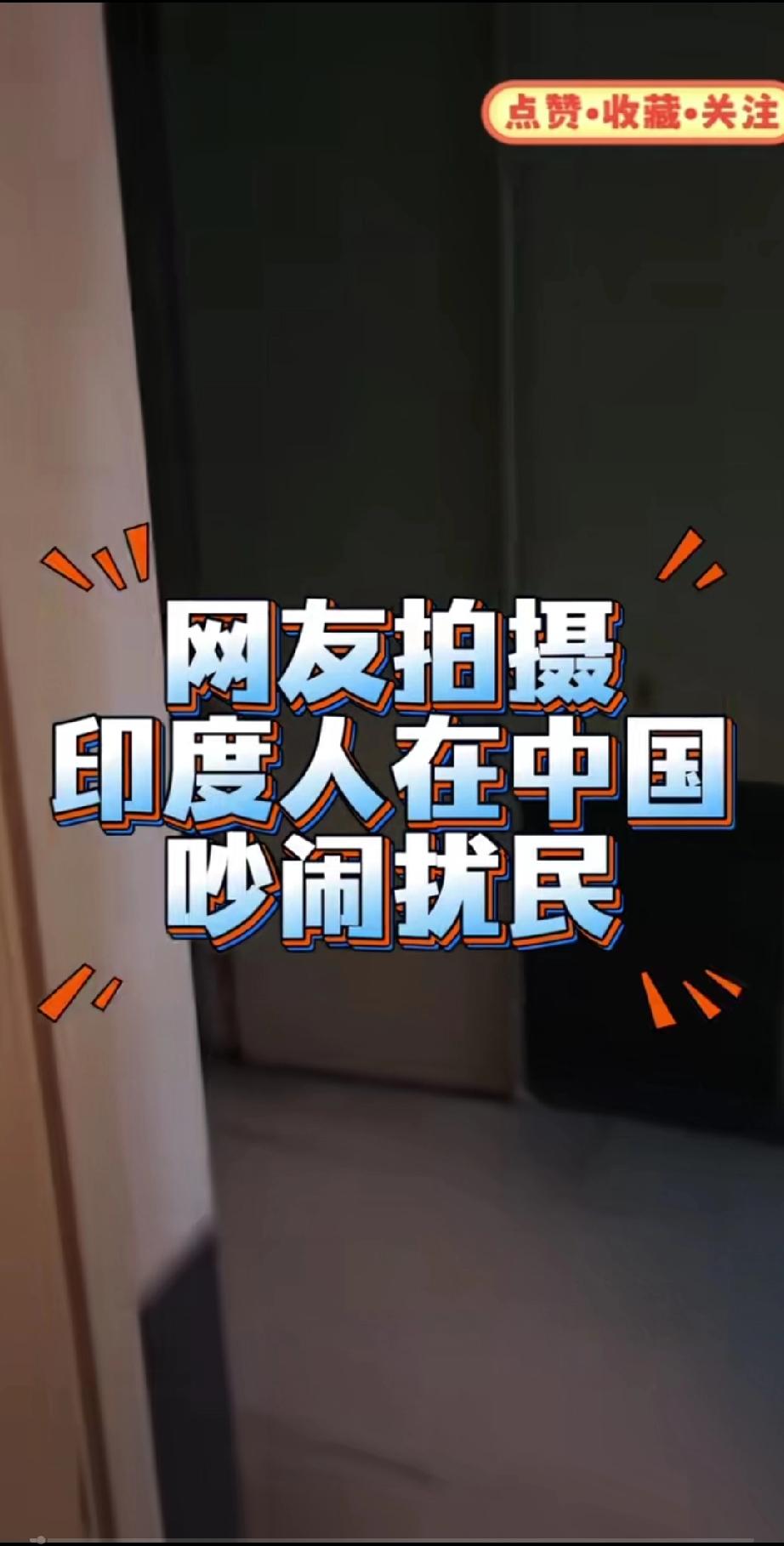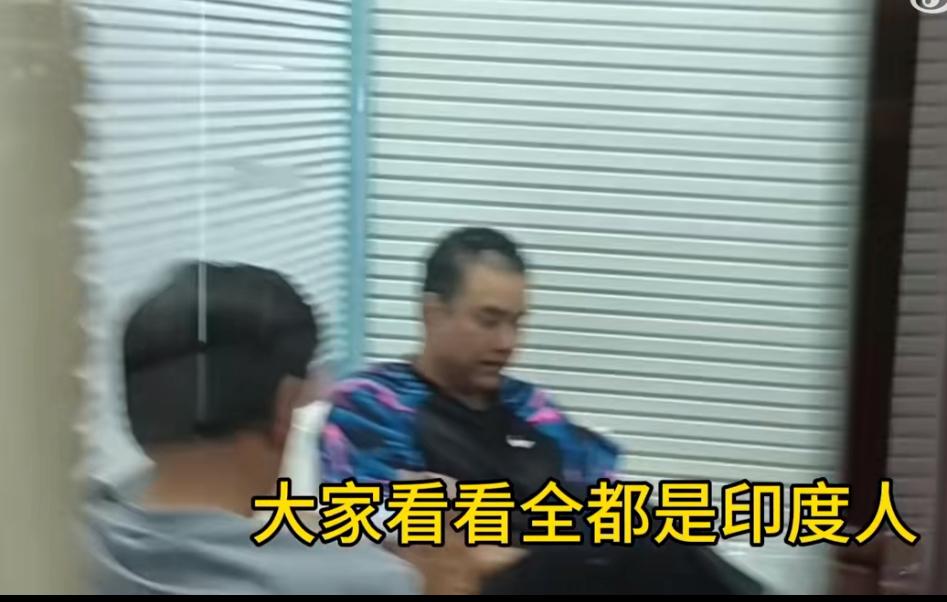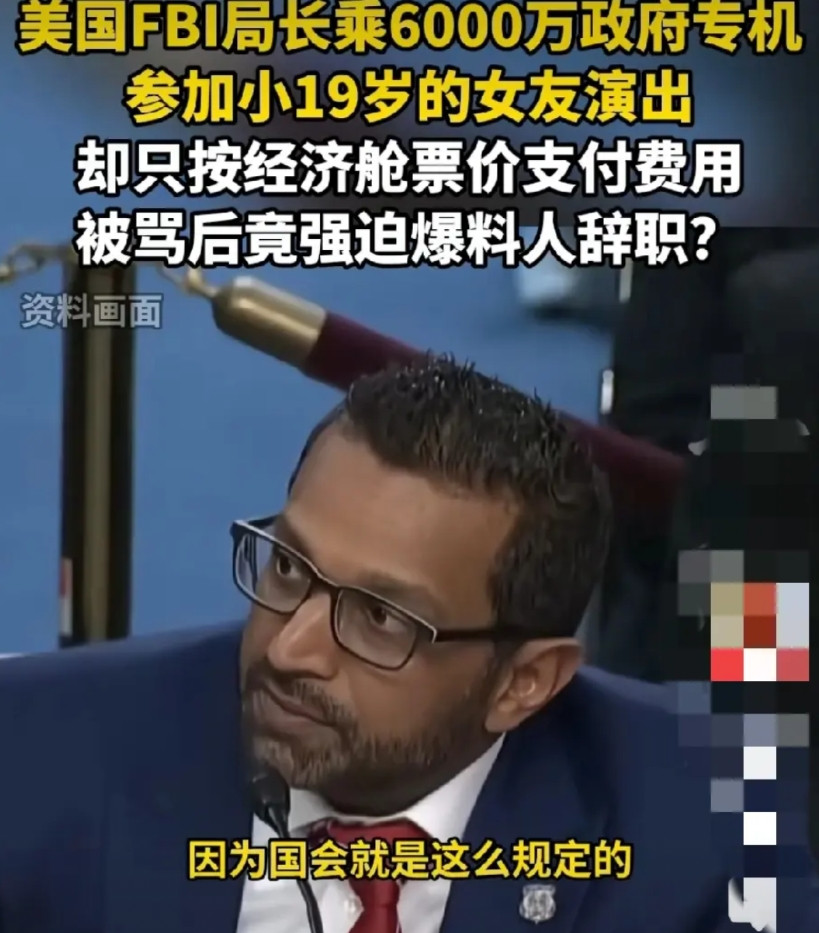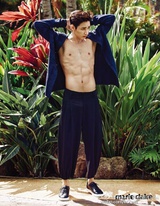来华的印度人,大多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西装笔挺、英语流利、一开口就是硅谷故事的精英。他们皮肤黑、穿得也简单,不是因为穷,是因为他们的路本来就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印度人来中国,是因为中国比印度发达,其实不是。真正的原因是中国给了他们一个“能赚钱但不用卷学历”的机会。高种姓的印度人,还是更愿意去美国、加拿大、澳洲,那些地方英语通行,文化也熟,去了就能当“自己人”。而中国,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连社交都困难。 但中国吸引的是另一批人:那些在班加罗尔做IT外包的、在金奈做外贸的、在浦那工厂里拧螺丝的。他们不是最底层的,也不是最顶层的,是那种在印度一个月赚三万卢比(大概两千五人民币)就觉得还不错的人。 来了中国,干一样的活,工资翻三倍。一个做软件测试的印度人,在班加罗尔一个月拿两万八,来深圳外包公司,直接给到九千人民币。吃住公司包了,剩下的钱还能往家里打。对印度普通家庭来说,这已经是“家里出了个能人”。 种姓制度没消失,只是换了地图。高种姓不是不来中国,是他们不来“打工”。他们宁愿去美国刷盘子,也不愿意来中国写代码。因为在美国,哪怕你刷盘子,别人也觉得你是“追求梦想”;在中国,哪怕你月入两万,别人也觉得你是“来打工的”。 但问题是,现实不跟你讲面子。2024年,印度IT外包行业平均月薪是3.2万卢比,折人民币2700块。而中国外包公司给印度员工的起薪,基本是8000到12000人民币,差距三倍起步。 有个在苏州做汽车配件的印度哥们,叫Raj,三十出头,原来是浦那一家德资工厂的质检员。来中国三年了,工资从一万二涨到一万八。他说得很实在:在印度,我是中产,在中国,我是打工人,但我能寄钱回家盖房子,能让我弟弟上大学,这就够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特别平静,没有那种“我要改变世界”的激情,也没有“我混得不好”的自卑。就是一句:我能养家。 评论区里有句话说得挺狠:在中国,没人问你姓什么,只问你干多少活。在印度,你姓什么,决定你能不能进这个门。 这不是夸张。印度社会学家Surinder Jodhka在2023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高种姓人群在海外的分布,美国占42%,加拿大21%,澳洲13%,中国不到0.7%。不是中国不欢迎,是他们根本不想来。 但低种姓和中产种姓不一样。他们不怕吃苦,就怕没机会。中国给了这个机会。哪怕语言不通,哪怕吃得辣,哪怕微信支付宝不会用,他们也愿意学。 有个在深圳华强北卖手机配件的印度人,叫Arjun,原来是德里一个小商贩。他说:在印度,我一天卖十个充电器,赚200卢比;在中国,我一天卖一百个,赚800块。我不需要会说中文,我只需要会按计算器。 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一个中国老板在笑,说你这中文说得比我还溜。他也笑,说:赚钱的语言,不用学就会。 其实中国政府也没怎么宣传这些事。印度人来华工作签证,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工作类居留许可,一种是外国专家证。2024年,印度籍在华持工作签证的人数大概是2.1万人,听起来不多,但比2019年翻了一倍。 这些人里,做IT外包的最多,其次是外贸、制造业、教育培训。很多人是“先来打工,再自己干”,比如先在外包公司干两年,摸清流程,就自己接私活,甚至开个小公司。 有个在杭州做软件外包的印度团队,五个人,全是原来在Infosys、TCS干过的。他们说:在中国,客户不问你是婆罗门还是刹帝利,只问你代码写得快不快。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尊重。 印度国内也不是没人反对。有些人说:你们去中国,就是给中国人打工,丢印度人的脸。但这种声音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面子不能当饭吃。 有个在东莞做模具的印度大叔,五十多岁了,原来是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个技工学校老师。他说:我儿子在印度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我在中国打工,一个月寄回去的钱,够他报三个培训班。你说我该选哪个?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有点红。不是委屈,是那种“我终于能做点事”的激动。 其实中印之间的这种“技术换收入”的流动,早就不是新闻了。2021年,中国驻孟买领事馆就发过一个数据:印度籍在华技术人员中,78%来自南印城市,比如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金奈。这些地方不是印度最穷的,但也不是最富的,是那种“有点技术,但缺机会”的中间层。 他们不是印度最亮的星,但他们是印度最真实的大多数。 而在中国,他们也不是最被看见的那群人。没有抖音博主拍他们的日常,没有媒体写他们的故事。他们只是每天坐地铁、吃盖饭、加班、寄钱、视频通话。 但这就是现实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谁更优秀,是谁在哪个城市能活出什么样子。 一个印度小伙在广州干了五年,攒了八十万人民币,回喀拉拉邦买了地,盖了房,开了个手机维修店。他说:我没变成精英,但我变成了家里最稳的那个人。 这句话,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