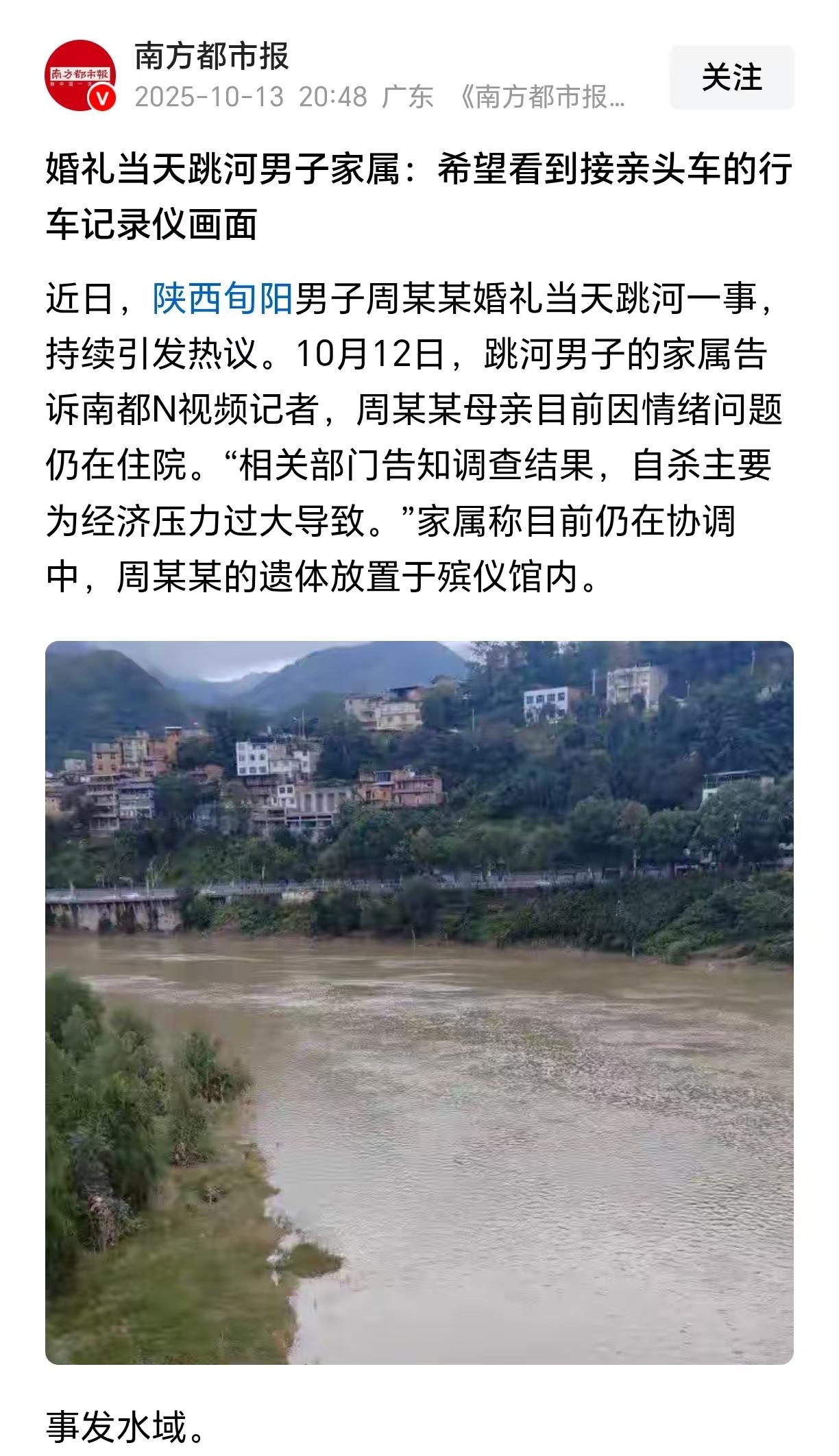1948年9月30日,上海提篮桥监狱,一个年轻男子在面对枪口时,突然仰头大笑。 ——— 那笑声带着铁锈味,在潮湿走廊里来回撞墙。执行队愣住,枪口不自觉往下垂。年轻人叫周鼎,二十五岁,公开身份是《申江新报》外勤记者,暗里给地下党送情报。笑声未落,他抬手,把散乱头发往后一撸,像上台领奖,不是赴刑场。 “兄弟,别愣着,快完事,我还赶着投胎。”他冲兵士眨眨眼,声音不高,却震得人心里发毛。士兵回神,咔啦推弹上膛,却没人敢先扣扳机。周鼎又笑,肩膀直颤,仿佛听到极好笑的段子。他转头,对墙上那盏昏黄灯泡喊:“老徐,你交代的任务我完成啦!下一步,看你的!” 兵士们面面相觑,不知“老徐”是谁。只有角落里的典狱官心里一紧——老徐,是上周被秘密处决的交通站站长,也是周鼎的单线上线。典狱官暗骂:死到临头还玩暗号?他挥手示意立即执行,可手指刚抬起,周鼎已先开口:“别让血脏了新换的衬衫,我兜里还有枚硬币,替我投黄浦江,就当送行。”说着,他舌尖一顶,把一枚磨得发亮的银元吐到掌心,随手抛向空中。银元旋转,在灯下闪出刺眼白光,啪嗒落地,滚到典狱官脚边。那清脆一声,像给黑夜点了根爆竹。 枪声同时响起。三发子弹穿透胸膛,血点溅在灰墙上,像谁甩了一把红漆。周鼎晃了晃,却没倒。他低头看胸口,又抬头,嘴角仍挂着笑:“手艺不行啊,再补一枪?”声音已弱,却字字清晰。士兵们脸色惨白,第四声枪响,他膝盖一软,扑通跪地,头缓缓垂下,额前碎发遮住了眼。那枚银元,静静躺在血泊里,像一轮冷月,照着他渐渐暗去的脸。 次日清晨,报童沿街叫号:“申江新报特刊!记者殉难,狱中留谜!”报纸卖到脱销。周鼎事先写好的文章被同事冒险刊出——揭露当局滥杀、呼吁释放政治犯,还附上一句:“我愿做一枚石子,投入黑暗井口,激起回声。”读者这才知道,他进监狱前,把全部采访资料、照片底片藏进报社暗房,连审判记录都提前复印。那枚银元,是地下党联络暗号:正面龙纹,反面“同舟”二字,谁捡到并投入江中,即表示“任务已了,继续航行”。当天傍晚,黄浦江边,一个拉黄包车的少年偷偷把硬币抛进江心,扑通一声,水花溅起,像给逝者点了头。 周鼎死了,可故事没完。后来,上海解放,人们在提篮桥档案室发现一页纸,是他临刑前夜写的:“我并非英雄,只是记者,记者记录世界,也被世界记录。若我之死能让污水里冒个泡,那就算没白活。”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口号,只有这几行字,却看得人眼眶发热。有人说他傻,明知暴露还回去取底片;有人说他痴,为一张纸送命。可正是这股痴劲,让今天的我们,能在档案馆摸到那份带着弹孔痕迹的报纸,读到七十年前那个年轻人的倔强。 我曾在上海外滩散步,望着黄浦江水,想象那枚银元沉底的样子。水面船只来往,汽笛声混着汽轮轰鸣,谁还记得一枚硬币的落水声?可历史记得。它像暗流,悄悄推着船舵,让大船拐了个小弯。周鼎用命换来的,不是惊天动地的胜利,只是一圈涟漪。但涟漪扩散,就能变成浪潮。我们享受的光亮,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微光汇聚——有人点燃自己,有人守护火种,有人传递灯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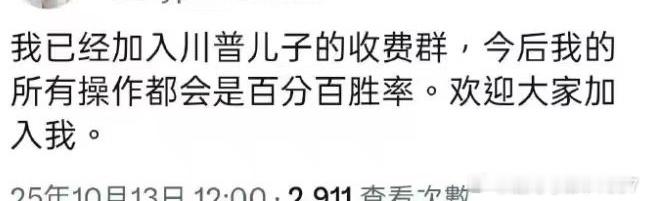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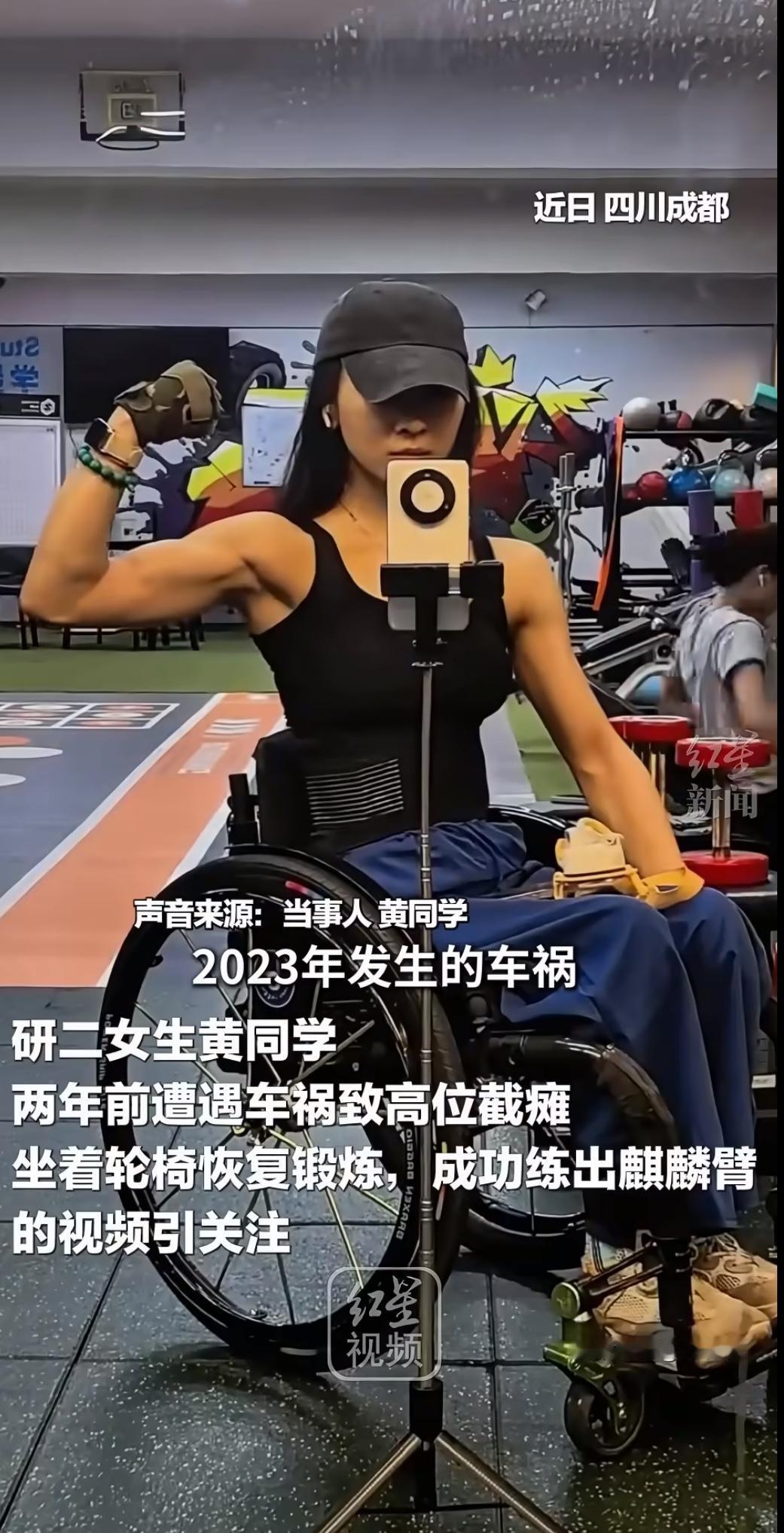

![又剩下司机一个人开车回来了[笑着哭],我们都坐飞机走了…看到机场广告,XC70](http://image.uczzd.cn/1810553852022074564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