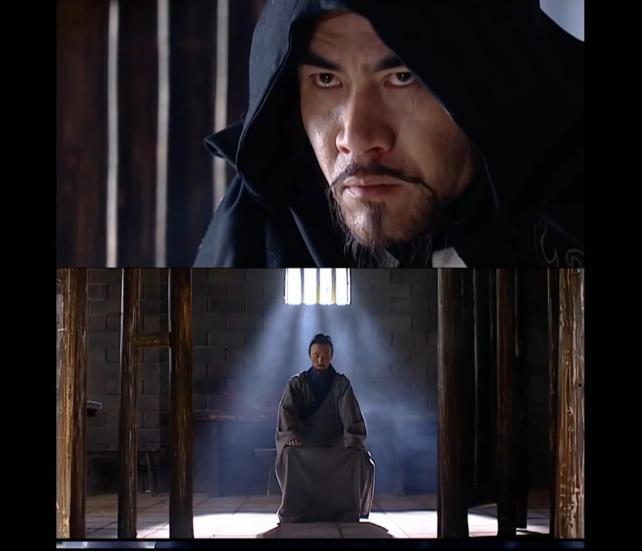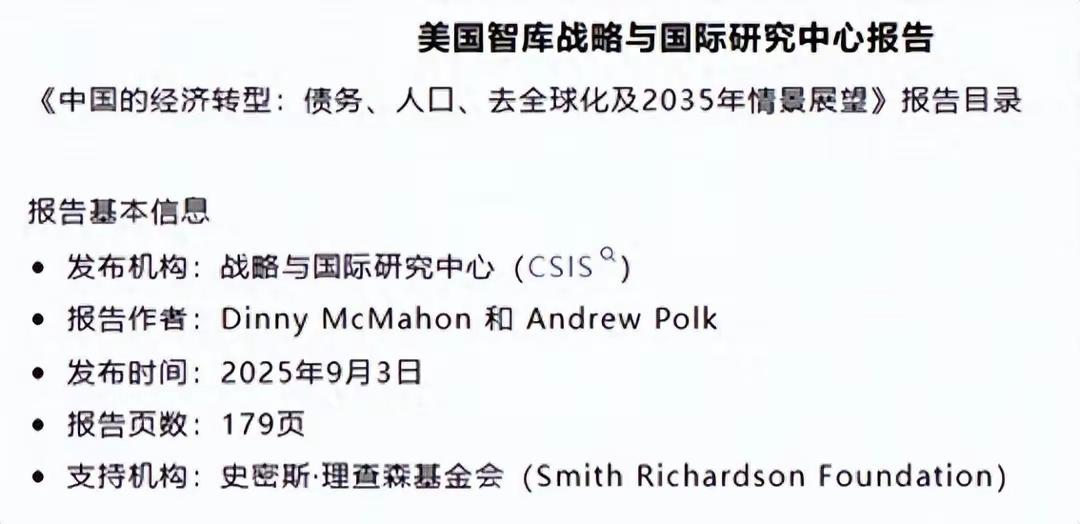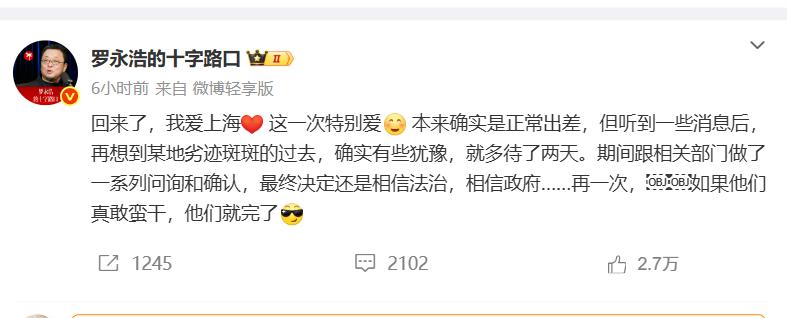“三武一宗”灭佛是针对金融特权集团的战争吗?其实,这场持续几个世纪的斗争,就是一场世俗政权与金融特权集团的生死博弈,一场针对享有免税特权、垄断金融资源、吞噬国家税基的寺院经济复合体的全面战争。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警示:“特权的存在,必然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王朝崩溃很少源于单一事件,其深层原因在于特权阶层通过金融工具进行财富的无限扩张。就像癌细胞吸收整个机体的养分,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佛教自东汉初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演变为庞大的、享受免税特权的“金融-地产”复合体,逐渐成为“国中之国”。 北魏时期,全国有三万座寺庙,供养着200万僧尼,占总人口近10%。这些僧尼不事生产、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却占有大量社会资源。 其实,当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就会不可避免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院”,《魏书·释老志》生动描述了当时寺院经济的繁荣景象。 唐代规定“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一如之”。这些土地不仅免税,还能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扩张。此外,寺院还经营水力磨坊、店铺、车坊等营利性产业,而且所有这些产业都享受免税特权。 富人官僚们发现这一避税天堂之后,就纷纷将财产寄存于寺院,用以逃避国家赋税。在长安寺院中,北魏太武帝就曾发现大量“官吏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看到没?宗教组织一旦与经济利益结合,就会异化为榨取民众的工具。 在积累巨额财富之后,寺院就会从事跑马圈地和高利贷业务。唐代寺院的“柜坊”就是早期金融机构,开展典当和借贷业务。这玩意就相当于不受朝廷控制的、特权化的巨型银行集团。 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就会造成了双重危机:一方面纳税户口急剧减少,财政收入大幅萎缩;一方面可用兵源也日益枯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正如辛替否对唐中宗的警告:“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将何以役力乎?” 面对佛教金融特权集团的挑战,“三武一宗”便开启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灭佛、废佛和限佛运动。 446年,北魏太武帝开启灭佛先例。他在长安佛寺发现兵器、酿酒器具和大量官僚富人寄存的财物之后,便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皆坑之!” 574年,北周武帝废佛则更加系统化,他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将4万所寺庙充为第宅,命300万僧尼“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845年,唐武宗会昌灭佛,废止寺庙4600多所,还俗僧尼26万余人,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此举极大地缓解了唐朝的财政危机。 955年,后周世宗限佛相对温和,他废减寺院3万多所,仅保留2694所,勒令数万僧尼还俗,并作出规定:今后出家者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官方度牒方可剃度。 其实,佛教“出家弃世”的教义本为超脱,却在实践中异化为逃避赋役的“制度性漏洞”。这种异化不仅削弱了儒家忠孝伦理,更让佛教从精神救赎沦为了“金融特权集团”的遮羞布。 韩愈曾在《论佛骨表》中直言批评:“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就像《大明王朝1566》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无父无君,弃国弃家!” 等到宋元明清,主角虽然从寺院换成了世俗王公贵族、官僚豪强,但剧本却惊人地相似。明万历时期,高利贷极度猖獗,不仅民间富豪放贷,连朝廷都开办了“皇店”进行高利贷经营。这种官营高利贷与土地兼并紧密结合,就把农民逼上了绝路。 李自成原本是驿卒快递从业者,但因明朝裁撤驿站而失业。失去稳定收入之后,他被迫借贷度日。最终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被官府拘押并遭受严刑拷打。出狱之后,他愤而杀死债主,走上反抗道路。 表面看,“三武一宗”灭佛是对宗教势力的打击,深层原因却是国家权力与金融特权集团的博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多个维度。 但灭佛运动只是暂时清除佛教金融集团,缓解危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特权+高利贷”这一财富掠夺模式,也没有改变滋生“癌细胞”的体质。 其实,只要特权与贪婪结合就能进行财富无限扩张的机制还在,王朝的衰亡宿命就难以避免。所以,这场战争远未终结,只是变换了形式。从寺院的金身到世俗的钱庄,从僧侣的袈裟到官僚的朝服,特权与资本结合的本质从未改变,要么被清除,要么与宿主同归于尽。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响,更是未来的预言。在这场永无止境的斗争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无论是清醒,还是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