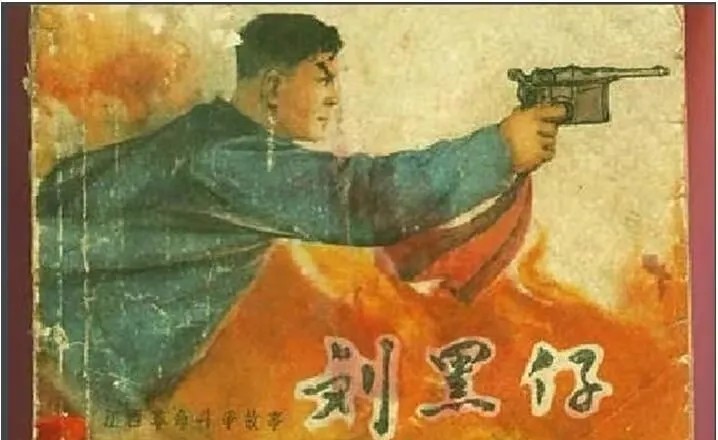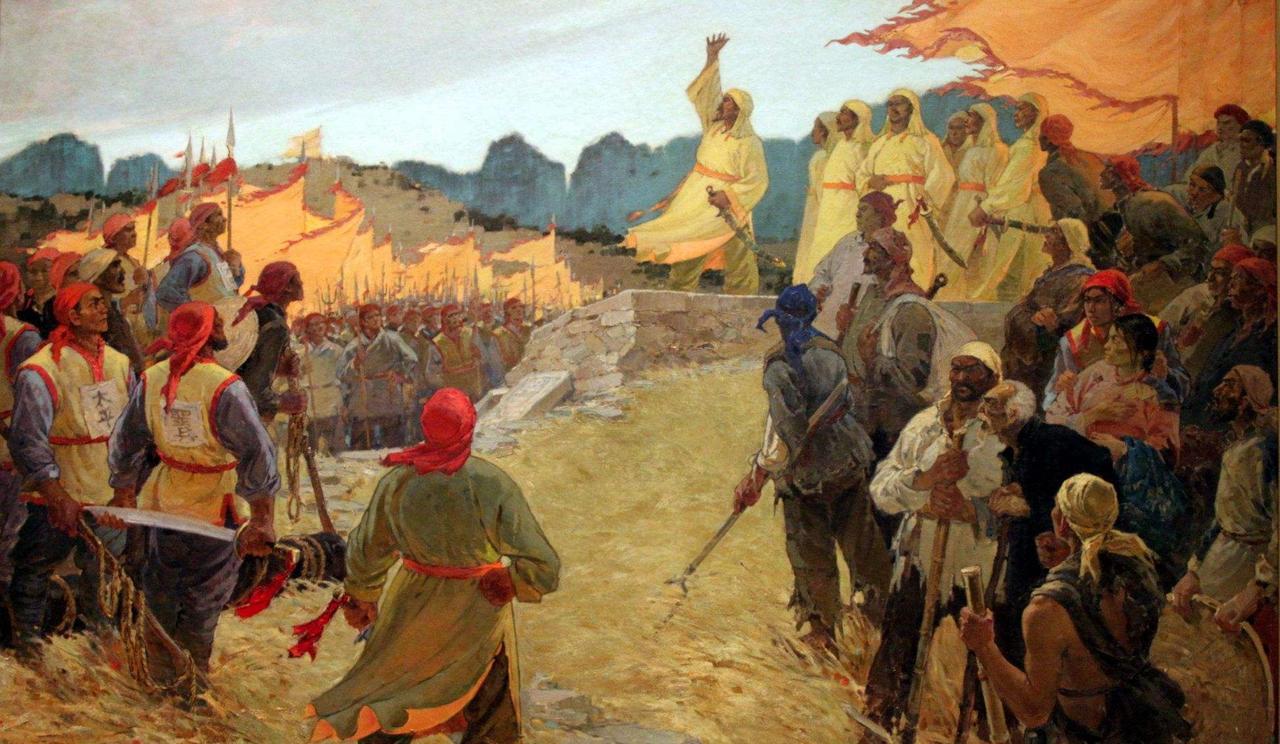1904年4月,孙中山因为革命行动惹恼了清政府,清政府于是对孙中山下达了追杀令。孙中山被迫逃到美国避难。然而杀手们还是找上门来,然而当他们发现孙中山的贴身保镖竟然是司徒美堂的时候却一个个都放弃了对孙中山的追杀!司徒美堂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自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的足迹便烙在流亡路上。
不管是逃到日本、檀香山、伦敦,那些清廷的鹰犬如影随形,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
1900年秋,惠州起义的硝烟散尽,此时革命陷入更深的困局,日本盟友态度暧昧,南洋据点屡遭驱逐,起义经费几近枯竭。
就在此时,一个大胆计划浮出水面。
曾参与戊戌变法的文廷式献计,他说此时山东义和团余火未熄,清廷在列强压迫下焦头烂额,正是北上举义的良机。
而日本志士末永节更提议直插义和团发源地青州,夺取清军旗营武装,剑指济南。
这个构想点燃了孙中山眼中久违的光,当南方道路被封锁,山东或成破局之钥。
选择青州绝非是一时兴起。
而是此时胶州湾被德国强占为“租界”,清军难以渗透,况且青岛港外轮往来,便于隐蔽出入。
更关键的是,青州府城驻防的八旗兵素以战力薄弱著称,而这里还蛰伏着一位关键人物,兴中会元老魏嵋。
要知道当时魏嵋的名字在山东士林中颇具传奇。
在1875年中举后,他因组织灾民抗粮被革去功名,铁牢磨砺出反骨。
1893年,他在广州偶遇开设药局的孙中山。
那个时候刚27岁的孙中山正从“医人”转向“医国”,两人一见如故,甚是投缘。
而这位年长他14岁的举人,成了孙中山在江北最早的同志。
1901年4月9日,日本密探记录孙中山乘船赴檀香山“探亲”,宣称将转道新加坡。
这实为精心设计的迷阵,新加坡英当局早将他列为“五年禁入者”,此行根本无法登陆。
当日本外务省档案还在计算他“6月5日从檀香山赴新加坡”的虚假行程时,孙中山已登上德国亨宝公司的“亚美利加号”。
在汽笛长鸣中,轮船悄然转向青岛港。
德国人修筑的胶济铁路刚通至胶州,铁轨在初夏阳光下延伸向西。
他换乘骡车穿越高密、潍县,沿途德国工程师正测绘线路,清廷官吏却不见踪影,而他们殖民者的特权意外成了革命者的护身符。
到了青州的地界魏嵋在此布下严密警戒,这位坐拥百亩良田的乡绅,早已变卖祖产资助革命。
他交给孙中山三样东西,山东旗营布防图、德国在胶澳的动向,以及三万银元的汇票,相当于今天千万元巨资。
这是同志们的血汗钱,”他沉声道,“拿去点燃火种。
随后数日,孙中山化装成商人勘察青州城防。
他注意到城墙西北角的裂缝,记下旗兵换岗的疏漏,更在基督教堂暗会同情变革的外籍牧师。
这些细节后来化作他给日本盟友的信中疾呼,夺青州可断清廷脊骨!”
到了6月初,魏嵋之子魏复庄护送孙中山至青岛。
就在临行前夜,两人站在胶济铁路旁。
远处德国机车喷吐白烟呼啸而过,孙中山忽然开口,你看这铁轨,洋人用它吸中国膏血,我们却要让它载革命奔流。
十二年后,当他以铁路督办身份重访青岛,在德华大学演讲时那句“德国人12年成就远超中国千年”,实为对这次密行的隐晦确认。
那三万银元很快化作东京革命机关的经费,催生了1905年同盟会的诞生。
而青州成为山东革命火种最烈的地区,武昌起义爆发时,这里走出290名志士,占全省近半。
到了1929年,当青岛将最繁华的斐迭里大街更名为中山路,世人只知纪念1912年那次公开访问。
唯有魏嵋家族记得,这条路正是1901年孙中山登陆青岛的第一站。
他踏过石板路直奔《胶州报》社,那里有接应他的兴中会老友朱淇,报馆窗口正对德国总督府尖顶。
当孙中山离青那日,魏嵋在桑园埋下一坛酒,待山河光复时痛饮,”他说。
1929年秋,当老人跪拜济南车站南运的中山灵柩,酒坛仍在土中静默。
革命者的密行终被岁月解密,青岛德华大学的演讲辞、中山路的路牌、青州桑园的断碑,拼凑出那个初夏。
当铁轨刺穿齐鲁大地,一个书生与一个举人,正在帝国的裂缝中埋下惊雷。
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虽多次遭遇失败仍坚持斗争,展现了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他常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至今仍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