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直接走出会议厅,元老于右任赶紧追上去:“中正,能否方便谈一谈,在离开重庆前,将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放出来”。 都说人走茶凉,但有些人的茶,就算人走了,也压根没人敢去碰。1949年1月21日的蒋介石,就是那个“走了,但茶没凉”的人。 那天,南京国民政府的大会堂里,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老蒋在台上宣布自己第三次下野,让副总统李宗仁出来代理总统,去跟对岸和谈。这话说完,他没半点留恋,转身就走。 就在这时,国民党里德高望重的元老,也是个大书法家——于右任,急匆匆地追了出去。他追上蒋介石,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了标题里那句话。注意一个细节,于右任说的地点是“离开重庆前”,但实际上蒋介石当时在南京。这或许是口误,或许是历史流传中的一点小偏差,但核心诉求很明确:为了和谈能有个好姿态,先把张学良和杨虎城放了吧。 这俩人为啥被关着?大家心里都有数,1936年的西安事变,在老蒋心里,那是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 面对老前辈的请求,蒋介石怎么反应的?他几乎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此事你找德邻(李宗仁的字)去办!” 嘿,这话说的,滴水不漏。表面上,我下野了,不问政事,你找现在的代总统。实际上呢?这就像一个公司的创始人“退休”了,但财务、人事、核心业务的头头,全是他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兄弟。 他确实想干出点名堂。他上台后,立马就拿释放张、杨二人作为自己推动和平的“投名状”。这不光是响应于右任等人的呼声,更是向对岸展示诚意,希望能保住“划江而治”的最后一点念想。 李宗仁动作很快,马上发电报、写亲笔信,分头派任务。 负责释放张学良的,是时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因为“汉卿”(张学良的字)当时已经被秘密转移到了台湾。 负责释放杨虎城的,是重庆市长杨森和西南军政长官张群。 陈诚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号称“小委员长”。但他跟一般只会溜须拍马的人不一样,他有自己的判断,也敢跟老蒋说几句真话。接到李宗仁的电报,陈诚心里也犯嘀咕。他觉得,都到这个份上了,再关着张学良,确实没啥意义,反而显得国民党小家子气。 于是,他给已经退居浙江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示“老板”的意见。电报里说的大意是:“老板,我觉得现在放了张学良也没啥大不了的,老关着反而累赘,不如就放了吧?您看呢?” 这封电报,现在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的关键史料。它证明了,即便是陈诚这样的心腹,当时也觉得释放张学良是顺水推舟的事。 结果老蒋直接回绝了。他告诉陈诚,这事儿不能听李宗仁的。而且还给他出了个“高招”:如果李宗仁那边催得紧,你就说你根本不知道张学良具体关在哪儿,省政府向来不管这事。 程思远一听,明白了,这趟白来了,只能悻悻地飞回南京复命。 另一头,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同样石沉大海。张群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杨森更是依附老蒋才能在四川立足。这两人对李宗仁的命令,直接来了个“软顶”,就是拖着不办。 蒋介石不仅在“遥控”指挥,还留了后手。他一边让手下人敷衍李宗仁,一边秘密下令,赶紧把张、杨二人都转移,藏到更隐蔽的地方去。 负责看管张学良的特务头子刘乙光,连夜把张学良从新竹转移到了高雄的寿山要塞,藏得严严实实。而杨虎城一家,则被秘密押送到了贵阳的麒麟洞。据说杨虎城当时预感不妙,曾对看守特务说:“李代总统要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转移我?我不走,要死就死在这!” 可惜,他的命运,根本由不得他。 李宗仁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他的“总统令”,出不了总统府的门。这场“放人”风波,把国民党内部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暴露得淋漓尽致。 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夜,蒋介石败退台湾前夕,在重庆下达了那道绝情的命令。他把在大陆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归咎于西安事变。他心中的那股恨意,在最后时刻化为了屠刀。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女儿,连同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年幼的儿子“小萝卜头”,在重庆松林坡被特务残忍杀害。 历史没有如果。但回望1949年的那个冬天,于右任老先生追出去的那几步,和他那句焦急的恳求,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他想为一个即将倾覆的时代,抓住最后一丝善意和体面,可惜,他追得上去蒋介石的脚步,却拉不回一颗早已被仇恨与权力固化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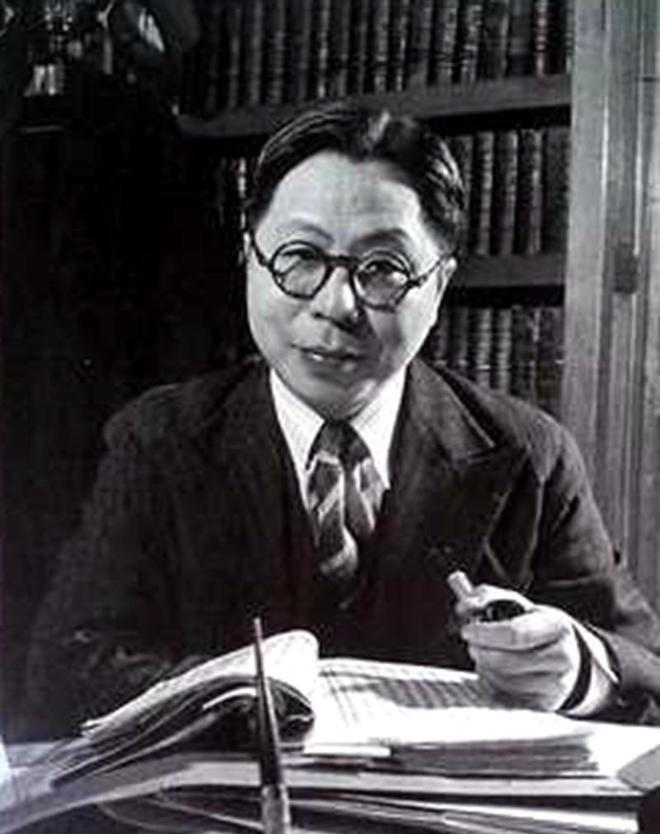

用户10xxx56
光头就一心胸狭窄之人
煌煌赤道不可冬日之无残大炎
丁辛三合,亥丑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