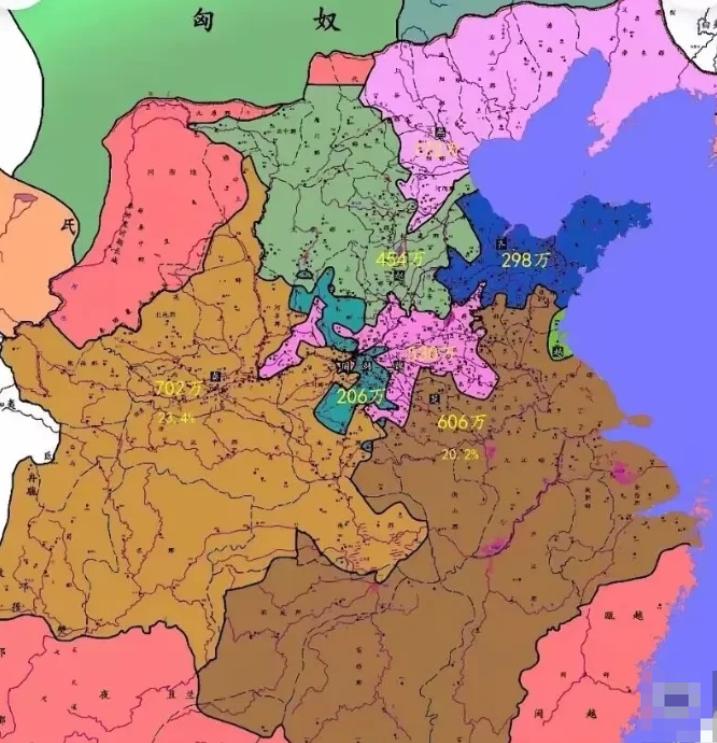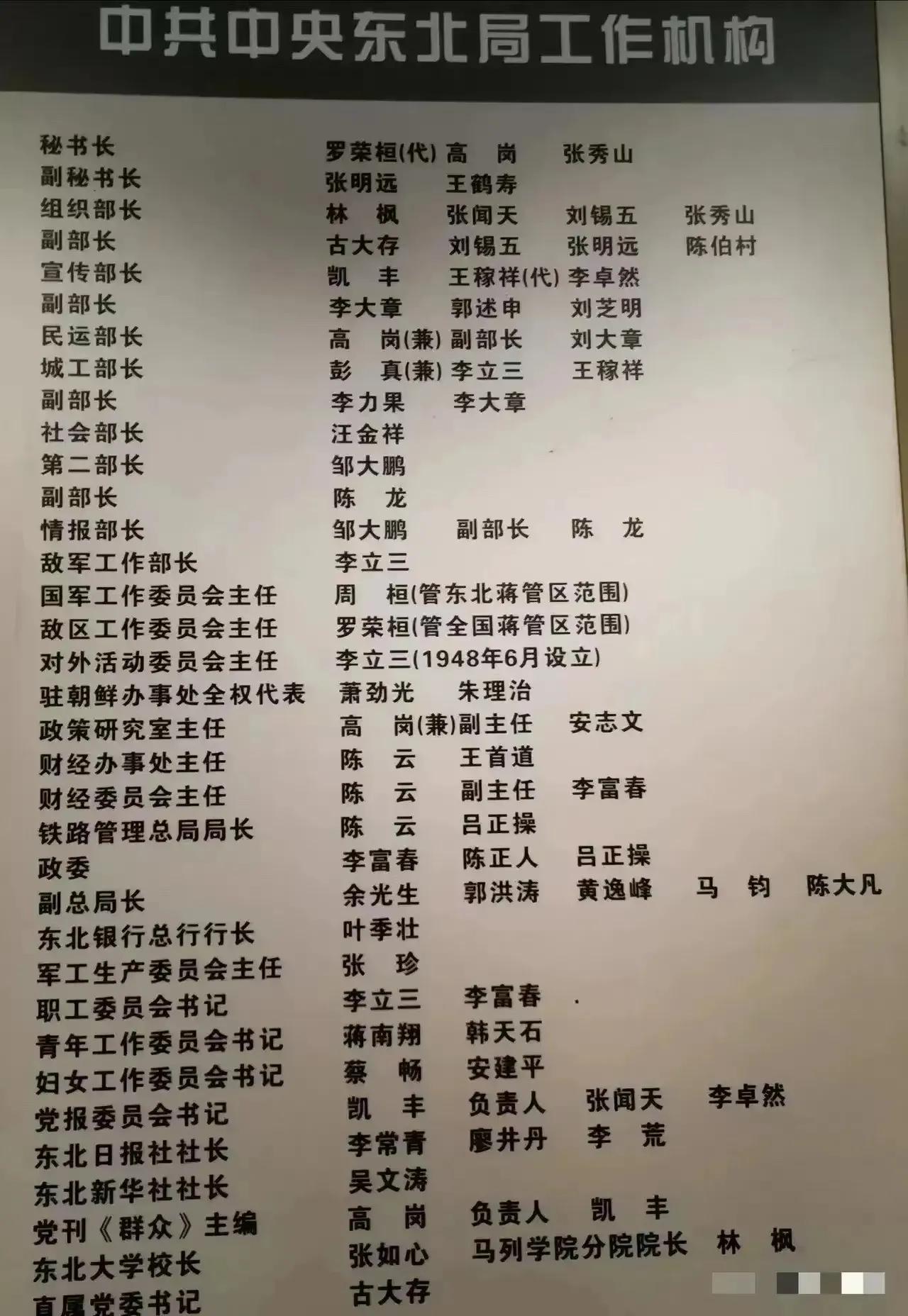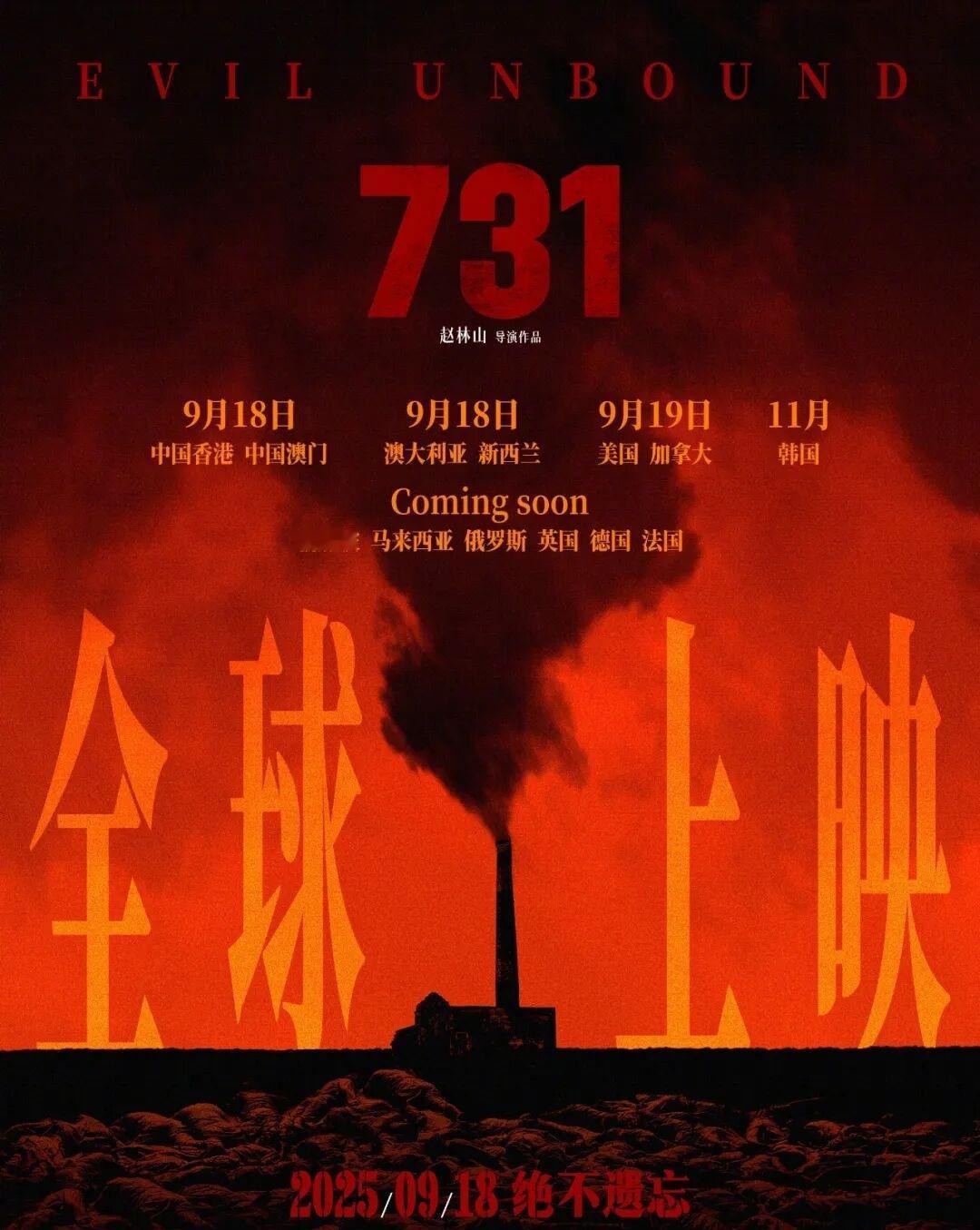岳飞被下狱之后,他手下的岳家军将领纷纷签字画押,指认岳飞谋反,无一人替他说话。 大理寺的牢门“哐当”一声关上时,岳飞身上的镣铐拖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望着窗外那方被高墙切割的天空,忽然想起郾城大捷那天,岳云抱着头盔冲进帐来,脸上还沾着金兵的血:“爹,弟兄们都说,跟着您能直捣黄龙!”那时帐外的欢呼声震得帐篷都在抖,如今想来,那些声音像隔了层厚厚的冰,冻得人心里发疼。 第一个在供词上画押的是王贵。他是岳飞的同乡,从少年时就跟着他打仗,胳膊上那道深可见骨的伤疤,是当年为了护岳飞被辽兵砍的。可当秦桧的人把他儿子绑到面前,刀刃架在孩子脖子上时,他手里的笔抖得像秋风中的叶子。供词上“岳飞谋反”四个字,每个笔画都歪歪扭扭,像是用血写的。画押那天,他没敢去见岳飞,只是在牢门外的墙根下蹲了一夜,天亮时鬓角的头发全白了。 张宪被打得最狠。狱卒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胸膛,他咬着牙骂:“奸臣误国!”可当他们把岳飞的养子岳雷拖进牢里,说“你不画押,这孩子就替你死”时,他忽然泄了气。岳雷才十六岁,脸上还带着稚气,是他看着长大的,每次打了胜仗,总爱缠着他要教枪法。张宪闭上眼睛,在供词上按了手印,指印红得像烙铁,烫得他心口直冒白烟。 岳家军里最年轻的将领傅选,当年是岳飞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的。那时他才十三岁,腿上中了箭,岳飞背着他走了三里地,还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了他。可如今他站在秦桧面前,看着满桌的金银财宝,听着“只要画押就封你做节度使”的许诺,终究没抵挡住诱惑。签字那天,他特意换了身新衣服,可走到牢门口,却怎么也迈不动腿,最后是被两个侍卫架着走的,像个提线木偶。 没人替岳飞说话,连那些曾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兵都沉默了。有个叫李宝的火头军,当年在朱仙镇,岳飞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骑,说“你年纪大,经不起折腾”。他提着菜刀想去劫狱,刚走到大理寺门口,就被巡逻的士兵抓住,鞭子抽得他浑身是血,他却对着牢里喊:“将军,俺对不住你!”喊声被鞭子抽打的声音淹没,像颗石子投进了深潭。 岳飞在牢里听说了这些事,没骂也没怨。他只是让狱卒拿来纸笔,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字。字里行间没有恨,只有一种沉甸甸的无奈——他太清楚这些弟兄的难处了。他们不是贪生怕死,只是家里有老娘要养,有孩子要护,那些所谓的“气节”,在家人的性命面前,轻得像张纸。 有回狱卒偷偷告诉他,王贵画押后,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刀在胳膊上划了个“忠”字,血流了满床。岳飞听了,只是叹了口气,让狱卒把自己那件旧战袍送给他。战袍的袖口磨破了,是王贵当年一针一线缝的,如今送回去,像把没开刃的刀,割得人心里淌血。 临刑前,岳飞最后见的人是岳云。父子俩隔着铁栏,岳云哭着说:“爹,他们都背叛您了。”岳飞摸了摸儿子的头,手镣的铁链擦着儿子的脸,冰凉冰凉的:“他们不是背叛,是身不由己。记住,当兵的,护得住家,才算护得住国。”这话里没有怨,只有一种看透世事的平静,像深秋的湖水,再大的风也吹不起波澜。 风波亭的雪下得很大,把地上的血都盖住了。岳飞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战袍,望着天空,忽然想起年轻时母亲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情景,那时针落在皮肤上,疼得他直哆嗦,母亲却说:“疼才记得住。”如今他真的记住了,只是这代价太大,大到要整个岳家军来还。 后来有人骂那些将领不忠不义,可没人知道,王贵晚年把自己关在祠堂里,对着岳飞的牌位,每天磕一百个头,直到磕得额头出血;张宪被流放岭南,临死前还攥着块碎布,上面是他偷偷绣的“还我河山”;傅选当了节度使,却夜夜被噩梦缠住,梦见岳飞拿着枪问他“为什么”,最后疯疯癫癫地跳进了河里。 岳家军的旗帜后来被收进了国库,上面的血迹早已发黑。可每当有人说起那段历史,总会想起风波亭的雪,想起那些在供词上画押的手,想起岳飞临刑前那句“天日昭昭”。或许这就是乱世的无奈——不是所有的忠诚都能挺直腰杆,不是所有的背叛都出于本心,只是在那片浑浊的水里,连英雄的骨头,都得带着几分妥协的疼。 参考书籍:《宋史·岳飞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