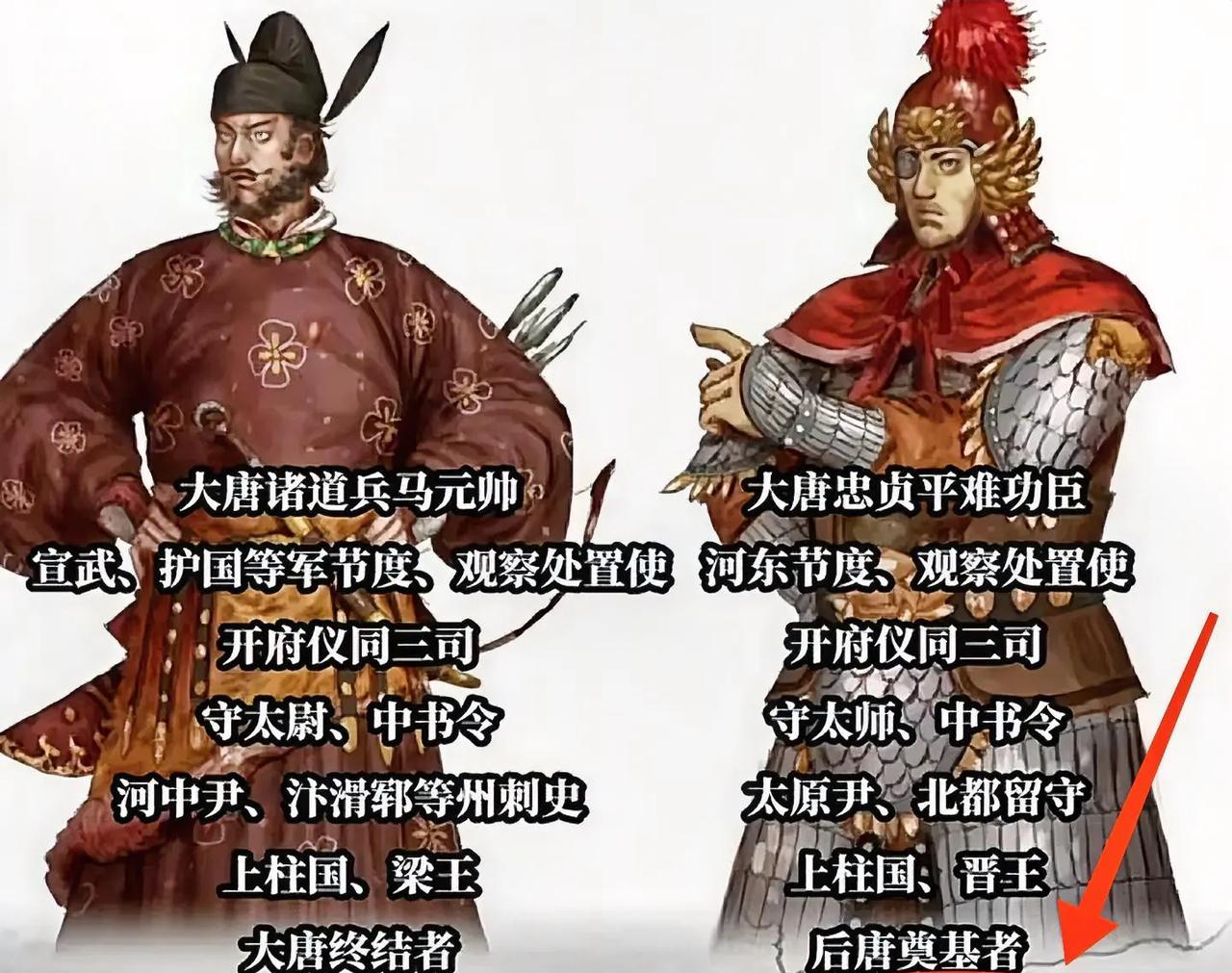1221年,金国名将毕资伦被俘虏,他宁死不降,堪称金国版文天祥。被南宋关押14年,毕资伦从未忘记金国,宋人被他感动,佩服他是条汉子。 1234年,曾经的金国,在蒙古铁骑与南宋联军的夹击下,轰然倒塌。 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殉国,然而,在南宋牢狱的深处,两位金国旧臣的命运,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轨迹。 1221年,这位金国名将毕资伦在战场上被俘。 面对南宋的威逼利诱,他拒绝归顺。 自此,他被囚禁在南宋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一待便是十四年。 而毕资伦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深入骨髓的潮湿与阴冷。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他便起身,面朝北墙,一站便是半个时辰。 因为那是金国的方向,是故乡蔡州的所在。 看守换了一茬又一茬。 最初是个愣头青,隔着栅栏唾骂“金狗”。 毕资伦从不还口,只在对方骂累了,才纠正:“我叫毕资伦,是金国的将军,不是狗。” 后来那年轻看守调离时,竟偷偷塞给他一块晒干的艾草。 因为知道他每逢阴雨,旧伤便如蚁噬骨,彻夜难眠。 送饭的老卒姓王,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 起初递饭时,总把粗陶碗摔得哐当作响。 时日久了,见这位金国将军每次都把碗中食物吃得干干净净,连掉落的米粒也仔细拾起,态度便渐渐软和。 冬日天寒,老卒会多舀一勺滚烫的菜汤,嘟囔着:“趁热喝,冻坏了没人跟我这糟老头子搭话。” 毕资伦明白,老卒是寂寞了。 牢中犯人,不是终日哭嚎,便是癫狂痴傻,唯有他,偶尔还能与老卒聊几句庄稼收成、节气农时。 某年的深秋,南宋一位礼部侍郎踏入牢房,许以高官厚禄、华宅美眷,劝他归降。 而毕资伦抬起头:“侍郎大人府上,可有祖坟?” 侍郎愕然,毕资伦接着说:“我爹娘的坟,在蔡州。我若降了,背弃故国,他日九泉之下,有何面目祭拜双亲?” 侍郎哑口无言,最终留下一件大袄,默然离去。 1234年的冬天,一日送饭的老王眼眶通红。 毕资伦感觉不对劲,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老卒终于说出:“蔡州破了,金国亡了。” 那一夜,牢房里没有点灯。 看守透过栅栏缝隙窥见,毕资伦坐在稻草上,一夜没睡。 后半夜,传来了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 次日清晨,看守发现他额头一片青紫,渗着血丝。 而他依旧面朝北墙站立,只是那曾经挺直的腰杆,似乎被无形的重担压弯了些许。 国都没了,坚守还有什么意义? 送饭的老王常对旁人说:“你们没瞧见吗?他给墙角石缝里钻出的一株野草浇水。明知它活不长,还日日悉心照料。这人的心啊,比石头还硬,比那野草还韧。” 两年后,毕资伦病倒了,最终连起身的力气都耗尽。 南宋一位将军带着珍贵药材探视,劝道:“毕将军,只要你肯说一句‘归顺’,我立刻接你出去医治。” 可毕资伦抬手指向牢窗:“你看那日头总是往西边落,它不会因谁喊几声就改了道,我也一样。” 他走的那日,老卒为他擦拭身体时,发现他贴身藏着一块磨得锃亮的铜牌,上面刻着一个深深的“毕”字。 那是他年少从军时,父亲亲手为他打制的。 看守的士兵们自发凑钱,置办了一口薄棺,将他安葬在城外一处面朝北方的小山坡上。 下葬时,来了许多人。 后来,常有百姓自发为这座孤坟添土。 说书人将他的故事编成话本,传唱道:“南北虽隔,忠义不分。” 与此同时,在临安府戒备森严的囚室中,另一位金国重臣正经历着另一种考验。 张天纲,金国最后的宰相之一。 他在蔡州城破时被俘,与毕资伦的坚守不同,他面对的,是南宋朝廷的公开审判与威逼利诱。 他被押解至南宋都城临安,被送上“献俘”大典承受着胜利者的羞辱与围观。 临安知府薛琼厉声质问:“你本是河北汉人,有何面目以金国宰相之身,至此为虏?” 张天纲毫无惧色:“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大金已亡,我主哀宗皇帝以身殉社稷,较之当年贵朝徽、钦二帝北狩,受牵羊之礼,囚五国之城,含恨而终,孰高孰下?” 这番犀利的言辞,直指南宋君臣心中靖康之耻。 薛琼被噎得面红耳赤,恼羞成怒,只得命人将他押下。 次日,宋理宗赵昀,亲自提审张天纲。 他试图以帝王之威压服这位亡国宰相:“张天纲,你当真不惧死?” 而张天纲挺直脊梁:“大丈夫何惧一死!唯惧死不得其所,不能全其节义!今求一死!” 言罢,竟主动请死。 宋理宗既恼怒其不屈,又暗生几分敬佩,终究不忍心把他杀了,又关回大牢。 南宋官吏不死心,逼迫张天纲书写认罪供状。 张天纲却说:“要杀便杀,何须此等文书!” 最终,张天纲的下落湮没于历史尘埃,或病逝狱中,或从容就义,无人知晓。 毕资伦与张天纲,一位在漫长孤寂中坚守故国之思,一位在雷霆威压下捍卫故主尊严。 他们身处不同的牢笼,面对不同的压迫,却以同样的赤诚,书写了金国末世最悲壮的绝唱。 国可破,家可亡,唯精神之脊梁,永不弯折。 主要信源:(《金史·毕资伦传》相关记载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