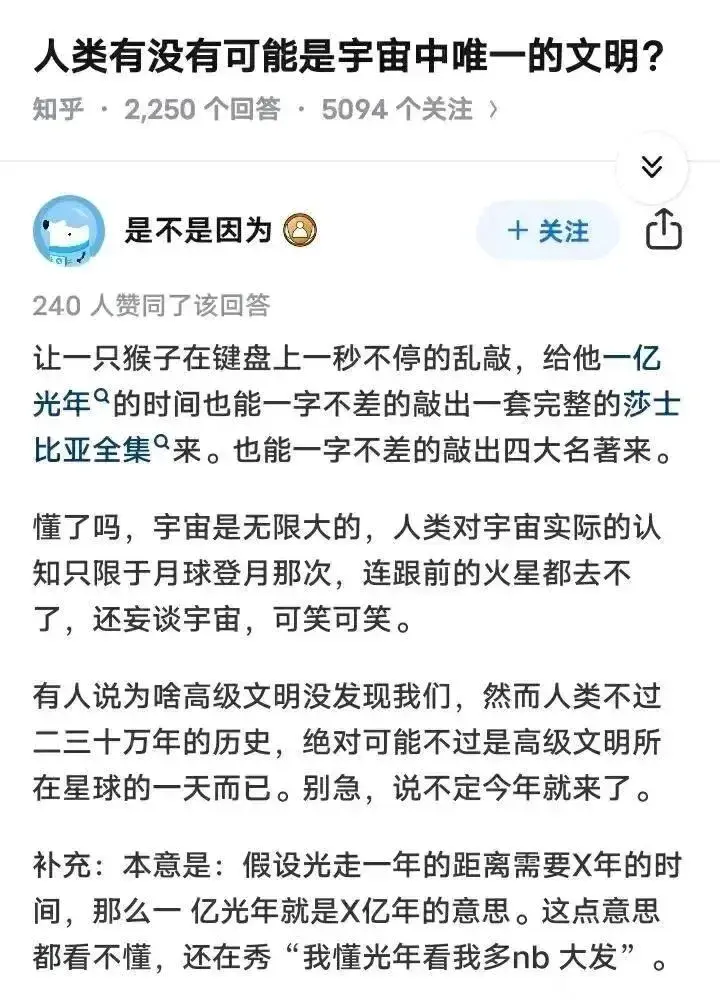如何定义“人”?在哲学层面,对这个抽象问题的回答无疑可以列举众多理论和学说。当我们转向日常生活会发现,虽然人们很少直接定义“人”,但其实也时刻在表述着关于什么是“人”的看法。比如,人们谈起人生感想会以“人嘛,最重要的是开心”开头,这是一种有关“人”的描述,只不过它定义的是生存目标和意义。与什么是“人”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还是当人们在表达对某件事某种现象不满时说的“不是人”(如“这是人能做出来的吗”),这里的“不是人”也即“非人”。通过重申人与动物的不同,是定义“人”常见的一种方法。
当然,人也是动物。当早期的人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状态,“人”产生,与动物的差异也就产生了。
作为人,人不能向同类施加暴力,但是被允许宰杀动物。在“非人化”心理研究领域,研究者认为,人性中有一套心理机制在约束人的暴力行为,所以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施暴的过程也就是把对方“非人化”的过程,唯有把对方视为“非人”的对象(“不把人当人”),才可能冲破心理机制的强大约束,当然其最终犯下的行为,本身也是“非人”性质。哲学家史密斯(DavidLivingstoneSmith)以“非人化”研究著称,他将这一过程形容为“制造怪物”。黑人、犹太人都曾作为群像被视为“怪物”。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制造怪物》一书,内容为作者从自然界开始谈论暴力的机制。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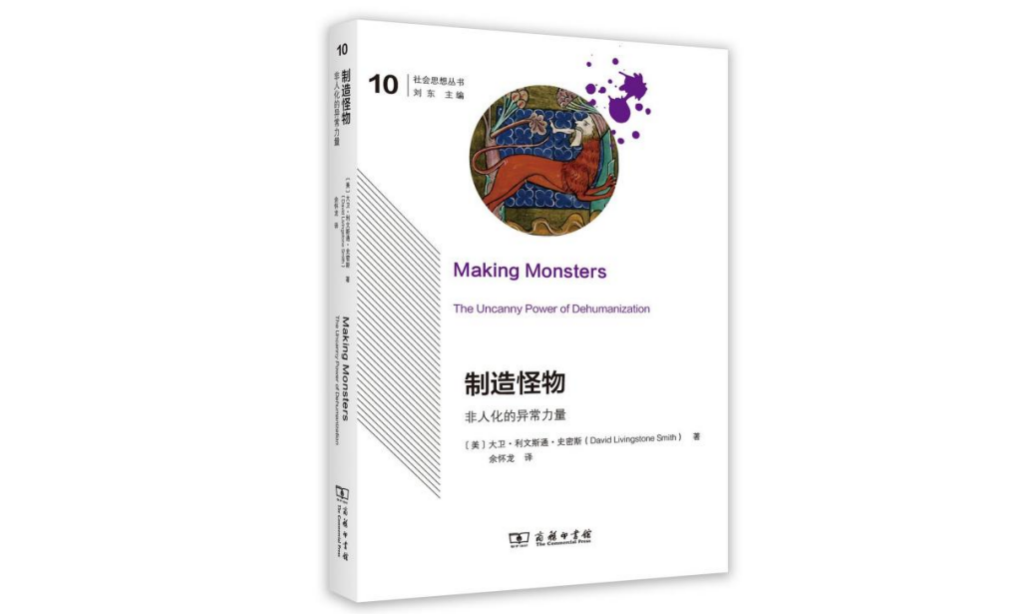
译者:余怀龙译
版本: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
自然界的和谐与矛盾
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地板上,俯瞰着我在新英格兰的家后面的大片林地。
两只漂亮的红尾鹰栖息在一棵高大的树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看到一只俯冲下来,用爪子抓住一些倒霉的哺乳动物——松鼠、花栗鼠或田鼠——带到栖木上,把还活着的动物撕成碎片,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近处,我看到蜻蜓在院子里飞舞。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象,但我知道这些在空中表演的杂技演员是凶猛的捕食者,是四处寻觅蚊子和其他昆虫来吃的微型杀戮机器。蜻蜓吃的许多蚊子都很圆润,因为它们肚子中的血来自在树林里游荡的鹿。再靠近一点,一群小蚂蚁拖着一只扭动的毛毛虫穿过我脚边的地板,带到巢穴里生吞活剥。

《动物王国》(Lerègneanimal,2023)剧照。
自然界一点也不和谐。这是一个奇妙而又可怕的地方,在那里,生命不断地以彼此为食。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的肉为生,即使是温和的食草动物也会肢解和吞食植物。如果植物能尖叫,它们一定会持续地发出叫声。有些生物与它们的猎物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播撒种子,吃水果的生物能够得到相应卡路里的热量。但对其余大多数生物来说,天敌的存在意味着剥削或毁灭。这就是为什么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将自然描述为“一个充满折磨和痛苦的游乐场,生物只能通过互相蚕食来维持生命。因此,每一种邪恶的动物都是成千上万其他动物的活坟墓,而它们只能通过以彼此为食来继续生存……并经历痛苦的死亡”。或者,正如菲利普·基切尔(PhilipKitcher)简要地指出的,“苦难不是生活中偶然发生的,而是命中注定的”。暴力是生命的存在条件。
智人也不例外。早在史前时期,我们夺走其他生物的生命,以获取食物、防护品、材料,如把动物皮毛和植物纤维用于制作衣服、木材,把角和骨头用于制作最终供娱乐的工具和装饰品,并且我们屠杀它们用于祭祀,以取悦我们神灵的嗜血欲望。几千年来,除了杀戮,人类一直在利用非人类动物的生理机能和肌肉力量,把牲畜当作行走的食物储藏室、蛋源和奶源、犁地工具和交通工具。
如果不伤害其他生物,我们就无法生存。但同样正确的是,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类,如果对同类的暴力行为没有受到强有力的约束,我们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对大多数群居动物来说,在攻击和克制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不是问题,因为进化赋予了它们一系列处理这种平衡的本能。黑猩猩生来就不会杀死同伴,而是喜欢吃被它们猎杀的疣猴。它们不必怀疑——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怀疑——剥夺生命是不是被允许的。它们只是在遵循本能。但我们智人不同,我们不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受到本能的束缚,我们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多的行为能动性。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并被迫寻找理由来证明我们的选择是合理的。
关于动物处境的解释
在我们人类历史进程的某个时刻,我们的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为什么可以杀死某些生物,而不可以杀死另一些生物?无论多么深奥,他们都需要一个合理化的说法,一个关于杀生行为规则的解释。在当今的一些采食文化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种合理化说法(这种说法在史前的狩猎-采集文化中可能很常见):作为猎人的人类和猎物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动物出现在猎人面前是因为它们想要被猎杀。因此,人类杀死动物是在满足动物的愿望,这是动物自己在奉献出它的生命,而不是人类夺走了它的生命。宗教研究学者格雷厄姆·哈维(GrahamHarvey)写道:
在一些地方,萨满的一个工作任务就是说服动物,让动物自己被猎人发现,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萨满在说服动物和人类,猎杀和被猎杀都是一种牺牲。死亡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往往是毫无意义的。但牺牲是神圣的、超然的、高于生命的。因此,萨满可能要学会找到对他人来说隐藏的东西:在远处的动物。一旦他们知道作为目标的动物在哪里,萨满通常会试图说服隐藏的猎物与猎人见面,并说服猎物放弃自己的生命。在文化上,萨满向猎物表达了适当的尊重,并承诺在猎物死时和死后采取进一步的尊重行为。
在一些版本中,动物在被杀死后,它们的灵魂会在来世继续存在,并一定会得到安抚。在另一些版本中,它们转世为其他动物,在死亡和重生的无尽循环中轮回。

反思掠杀动物的纪录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2005)。
当然,猎人都知道,动物试图不被杀害,并且害怕那些想要杀害它们的人。而每个猎人都知道,被刺穿身体的动物在死前会遭受痛苦。动物把自己作为猎物的想法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目的是使人类对它们的捕杀合法化。这是一种信念体系,其功能是使一个群体(即人类社会)受益,并使另一个群体(被人类剥削和杀死的非人类动物群体)做出牺牲。虽然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这样的信念具有“压迫”动物的功能。你可能觉得用“压迫”这个词来描述我们与非人类生物的关系并不合适。当然,你可能认为这个词只适用于我们与其他人类的关系。但你的这种想法与我在第九章中所阐述的等级框架观念是不一致的。“只有人类才会受到压迫”,这种直觉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偏见,即我们人类在宇宙秩序中占据着比其他生物更高的位置。
在某个时期,也许是随着畜牧业、农业和阶级社会的出现,一种新的杀戮观诞生了。事实上,这种观念是非常强有力的,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自然等级观念为物种间的暴力问题提供了更为高明的解决方案。对其他生物施暴的合法性被认为是由它们在“存在巨链”中的等级所决定的。羚羊可以被杀死和吃掉,因为它们是非人存在者,但杀死和吃掉人类社会中的成员是不被允许的。就像动物把自己当作猎物的观念一样,“存在巨链”观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过去和现在都在重申的信念体系,因为它使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暴力合法化了,进而为对人类有利的行为提供系统的支撑。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存在巨链”观念能如此广泛地传播,以及为什么它能如此强大地控制着人类思想。生命以生命为食,自然的等级观念是一种工具,其作用就是使我们赖以繁衍和生存的暴力行为合法化。
超级社会性
我们是超级社会性动物。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没有任何一种哺乳动物,能像智人那样拥有如此高的社会化程度。为了在高度社会化的群体中生存,我们必须拥有能够适应社会交往的思想。有研究确切表明,在单独监禁的情况下,囚犯表现出来的状态包括“焦虑、退缩、极度敏感、思虑过重、认知功能障碍、幻觉、失控、易怒、攻击性强、愤怒、偏执、绝望、情绪崩溃、自残、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事实上,我们是如此强烈地渴望社会交往,以至于我们倾向于看到根本不存在的人。“我们把月亮看成人脸,把云朵看成军队,”大卫·休谟注意到,“如果不通过经验和反思加以纠正,我们就会根据一种自然倾向,将恶意与善意归因于一切伤害或愉悦我们的事物。”

《暴力史》(AHistoryofViolence,2005)剧照。
群居动物必须避免对其社群成员进行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攻击,否则社群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人类的超级社会性约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天生喜欢顺利的合作行为。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在他对人类暴力行为的大量研究中写道:“人类的基本倾向是彼此在相互关注中成为焦点,并被彼此的身体节奏和情感语调所吸引。”柯林斯认为:
这些过程是无意识的和自发性的,也非常具有吸引力。最令人愉快的人类活动是人们被一种明显的微互动节奏所吸引:共同的语调,流畅的对话,笑语中的默契,人群的热情,相互的性唤起。通常,这些过程构成了一种互动仪式,至少在当下产生了主体间性和道德团结的感觉。面对面的冲突之所以难以发生,首先是因为它违背了这种共同意识和身心愉悦感。……有一个明显的障碍阻止我们陷入暴力对抗。它违背了人类的生理规律,即违背了人类在本能上就具有的……团结合作的倾向。

反法西斯电影《美丽人生》(Lavitaèbella,1997)。
暴力对抗的极端形式是身体暴力,最严重的是杀戮行为。因此,如果柯林斯是对的,那么人类对社会团结的偏好必然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如何激发人们的军事战斗能力。事实的确如此。美国陆军历史学家马歇尔(S.L.A.Marshall)在1947年出版了一部对人类影响深远的著作,即《人与战争的对抗:战斗指挥问题》(MenagainstFire:TheProblemofBattleCommand)。这本著作引发了美国军事训练的彻底改革。他在该著作中阐述了上述问题。马歇尔在战斗结束后立即采访了士兵,他发现许多步兵在射击时遇到了困难,不是器械方面的困难,而是心理方面的困难。他声称,这些采访使他相信,士兵们往往无法让自己使用致命性武器,因为“一般而言,那些正常健康的人,即能够承受战斗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和身体压力的人,仍然对杀害同胞存在一种内在的、通常未被意识到的抗拒,即如果有可能逃避战争责任的话,他们就不会主动去杀人。……在关键时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拒服兵役者”。在马歇尔看来,士兵对杀戮的心理抗拒是社会化的结果:
他就是由他的家庭、他的宗教、他所受的教育、他所处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理想塑造的。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来自一个文明社会,在这个文明社会中,夺取生命的侵害行为是被禁止和不可接受的。他对侵害行为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如此之深入、如此之长远——几乎就像他母亲的乳汁对他的影响一样——这是正常人情感构成的一部分。这是他参加战斗时的一大困难。他扣动扳机的手指停了下来,尽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对他的一种束缚。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障碍,而不是认知上的障碍,所以这种障碍不能通过“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样的认知推理来消除。
马歇尔对士兵在心理上抗拒杀戮行为的解释,与他那个时代正统的行为主义观点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除了少数先天条件反射外,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通过适应环境习得的。
抑制暴力的心理机制
一些来自发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婴儿天生就具有合作精神和利他精神。心理学教授、参战老兵大卫·格罗斯曼(DavidGrossman)让马歇尔的思想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他不同意马歇尔关于士兵为何常常难以痛下杀手的解释。他认为人类天生就抗拒杀害他人的行为。格罗斯曼认为,这种抗拒是很强烈的。

《少年的你》(2019)剧照。
尽管马歇尔和格罗斯曼的著作都很有真知灼见,但它们毕竟不是学术著作,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充其量只是轶事。而且,马歇尔关于士兵抗拒杀戮行为的说法还受到了强烈批评。然而,他们与其他学者有着非常相似的思想。颇具影响力的奥地利伦理学家伊雷纳乌斯·艾布尔-艾贝斯费尔特(IrenäusEibl-Eibesfeldt)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他认为,我们智人天生就具有抑制杀戮(Tötungshemmungen)的本能——在生物学意义上对杀害同类的抑制,“人类的攻击性行为被许多系统发育适应性有效地控制住了……我们天生就具有抑制攻击性行为的能力”。

《启示》(Apocalypto,2006)剧照。
心理学家菲瑞·库什曼(FieryCushman)及其同事在一篇题为《模拟谋杀》(SimulatingMurder)的论文中很好地描述了人类是如何抑制攻击性行为的。这篇论文记录了他们进行的一项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确定对暴力行为的厌恶是完全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还是偶尔基于对暴力行为本身的厌恶。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模拟暴力行为,并观看其他人所模拟的暴力行为。一种是拿起锤子,用力敲打实验物的假小腿(“小腿”实际上是实验物空裤腿中的一根塑料管);另一种是拿起一块大石头,用力砸打从实验物衬衫袖子中伸出来的橡胶手;第三种是用一把逼真的玩具枪“射击”实验物的脸部;第四种是用橡胶刀“割”实验物的喉咙;第五种是把一个栩栩如生的假娃娃的头用力撞在桌子上。
在实验过程中,心理学家会监测受试者的血压和心脏活动。他们发现,即使受试者清楚地知道在实验过程中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他们也会在生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痛苦迹象,尤其是当他们自己实施这些行为而不是观看别人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实验表明,引起厌恶的是暴力行为本身,而不是其道德后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为不会受到有害后果的影响,但这确实意味着,只关注道德同情心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库什曼及其同事在结论中指出:“对直接性伤害行为自发产生的强烈厌恶反应,可能可以解释其他令人费解的人类行为。在战场和假言道德判断中,人们拒绝做出直接的伤害,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同样,在我们的研究中,人们对模拟的伤害行为有强烈的厌恶反应,尽管他们明确知道这些行为不会真正造成伤害。这些案例都强烈表明,我们对行为后果的明确认知和我们对行为的自发情感反应是分离的。”
这些观察结果意味着,正常人具有一种心理机制来自动调节攻击行为,这种心理机制是自发运行的,不受意识的直接控制。这种机制可能是与生俱来的、由基因决定的,也可能是后天习得的,又或者可能是我们可以快速学会的。这一心理机制的起源问题在本讨论中并不重要。关键是认识到这样一种心理机制是存在的,并且它具有抑制人际间暴力行为的作用。
原文作者/[美]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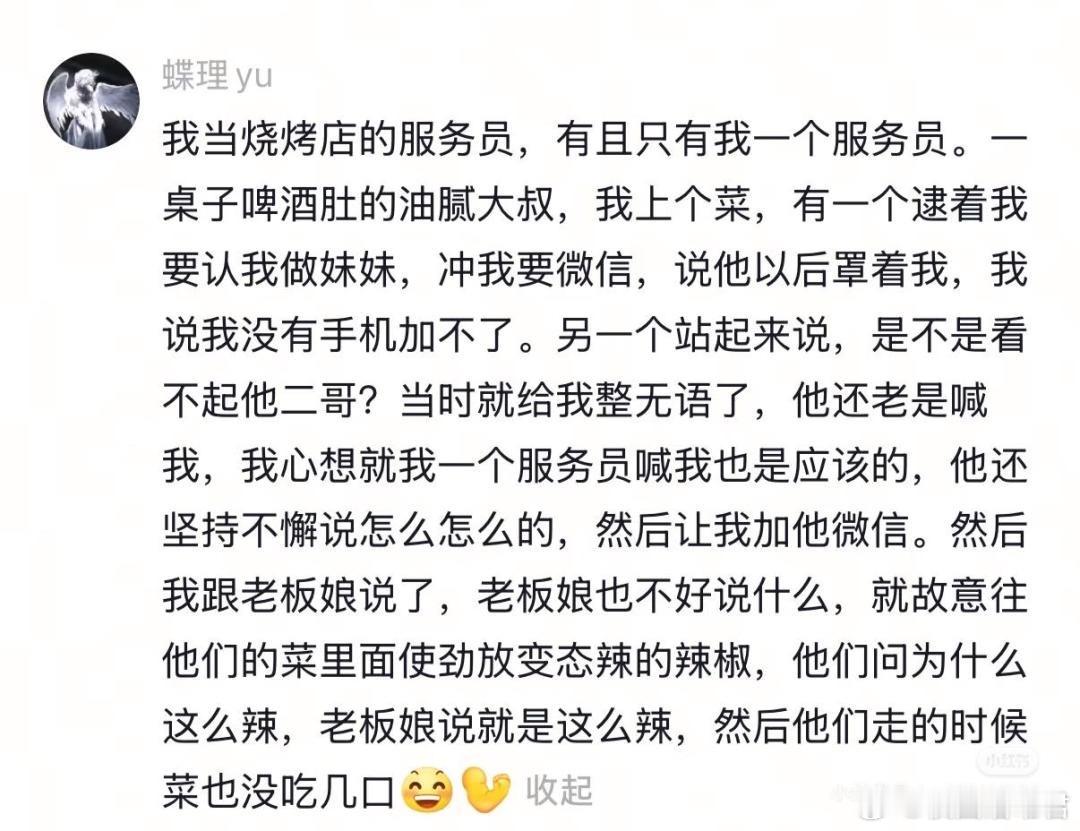
![看起来很像某种动物。[思考]](http://image.uczzd.cn/1489410184491465229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