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节有个说法,在军机处里流传很广:“满六必损。”一旦大臣人数凑够六人,就总有一个倒霉出局,或死,或贬,或病,或退。朝堂上下没人明说这话准不准,但一个个血淋淋的案例摆在那儿,没人敢不信。 朝中人事看似循规蹈矩,实则波涛汹涌。军机处,皇帝贴身智囊,本该是清廷运转最稳的地方。可奇怪的是,哪怕编制上限是六人,许多年间,皇帝宁可缺位,也不敢让它凑齐。一次两次还说是巧合,但每逢凑够六人,准有大事发生。渐渐地,这“六”成了禁忌,背后隐含的,是权力角力和血雨腥风。 第一桩事,起于光绪初年。文祥是慈禧信重之臣,入值军机,干练能干,人望极高。当时军机处已有五人,迟迟不补。直到景廉进来,第六人补位才刚坐稳,几个月后,文祥突发急病去世。说是病,但没有预兆,时人纷纷猜测是不是“触霉头”了。这事一出,“满六必损”开始在内务府口口相传。 紧接着沈桂芬的例子,更添一把火。他入值后,本还精神矍铄,但没几个月,突感胸闷气短,吐血身亡。他的位置正是第六席,跟前头文祥如出一辙。坊间早有风声,说谁补第六,就像端了命数。 但朝廷运转不能靠忌讳维持。左宗棠应诏进京,那时军机大员又凑到五人。老左虽性格火爆,但对这类宫廷怪象也心存警惕。他知道人们议论“六人之灾”,偏偏此时,潘祖荫来了。 他补第六,左宗棠大惊。果不其然,潘祖荫刚坐稳几个月,就被暴病带走,走得悄无声息。坊间彻底炸锅。连封疆大吏都说,宁做五军机,不碰第六个椅子。 背后原因其实不难猜。军机处虽说只是辅政之所,但每一位大员背后都有靠山,有的系满洲贵胄,有的联汉臣重臣。当人数凑齐,势力碰撞加剧,微妙平衡被打破,就容易出事。文祥如此,沈桂芬如此,潘祖荫也没逃脱。 满六,其实是多方势力的临界点。凑到六人,就有人必须退场,谁也不愿被下手,谁也都怕被替代。朝堂不缺人才,缺的是坐得稳的椅子。第六个不是职位,而是火药桶。捧上去就炸,压住了就出事。 慈禧深谙此道。她干脆规定,军机编制不强求满额,不凑整。光绪后期,李鸿章被召进军机,皇太后亲口嘱咐,只当顾问不算正式成员,以此规避“满六”的冲突。李鸿章也知分寸,凡军机大事,从不越权一步。他明白,这椅子坐得太多,人心就动得太乱。 到了晚清最后几年,军机处早已风光不再,但这“六”字禁忌,仍是心照不宣。连载福、那桐、张之洞等人都谨慎应对,从不主动要求补员。甚至到了宣统时期,军机处常年空位,皇帝宁可缺人,也不敢再冒“第六人”的风险。 其实,六不是灾,是表象。真灾的是权力过密,是皇帝怕军机合谋,是彼此掣肘之下,人人自危。六人一屋,若无强主镇场,注定乱作一锅粥。皇帝怕出奸臣,臣子怕遭妒忌,“满六”变成了众人都不愿提,却谁都知道的雷区。 清末官场心态,藏在这些细节里。有人胆大坐六,有人识趣退位,有人站到门前转身离开。朝局如此,国运也难长。等到辛亥爆发,军机处解体,这场长达数十年的“满六必损”魔咒才算画上句号。 可等到民国之后,旧朝遗老回忆此事时,仍对那几桩“凑六出事”的往事讳莫如深。有人写进笔记,有人当作笑谈,也有人至死没敢提起自己当年“差点坐第六”的那次经历。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玄学,是刀口舔血,是政治对人的冷静安排。 “满六必损”,不是迷信,是制度深处的必然反应。它不是天意,是人意,是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为稳住局面自设的“人肉保险丝”。一旦电流过载,第六人,就成了那个必然牺牲的开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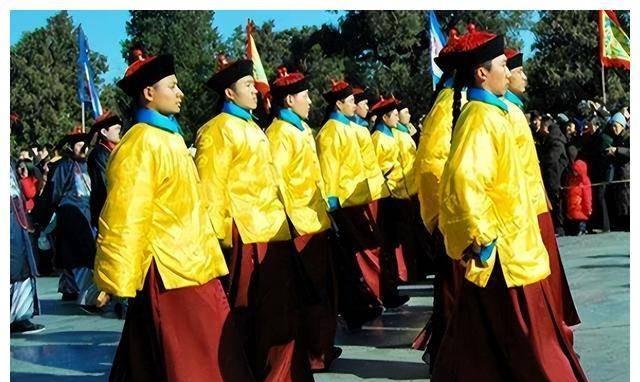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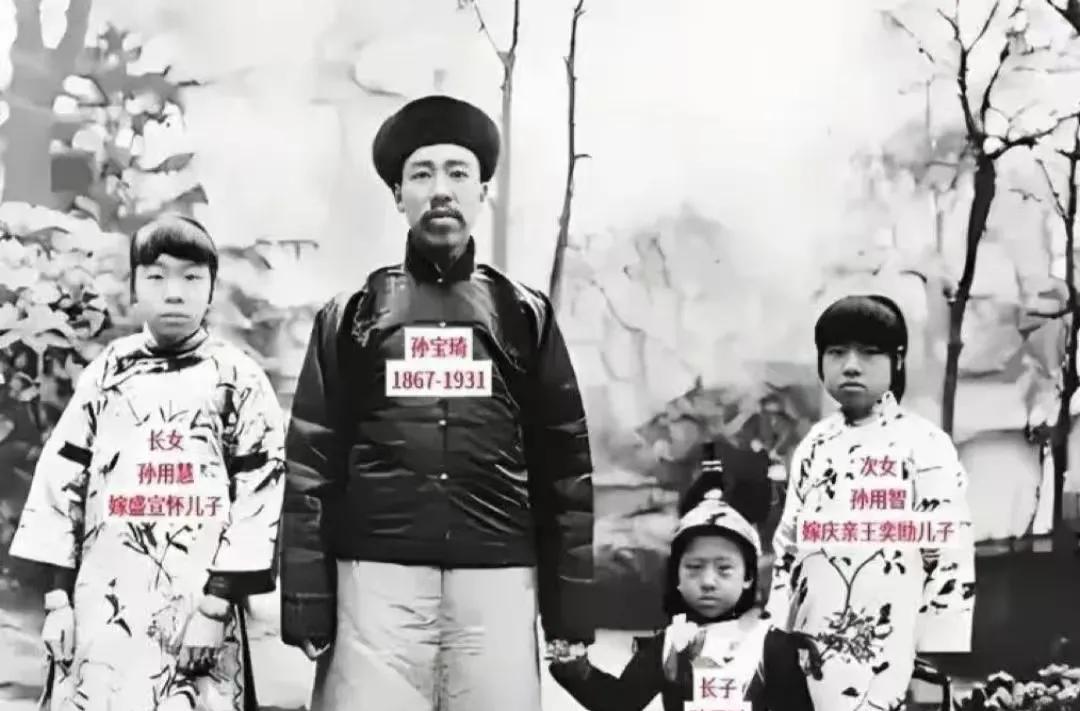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