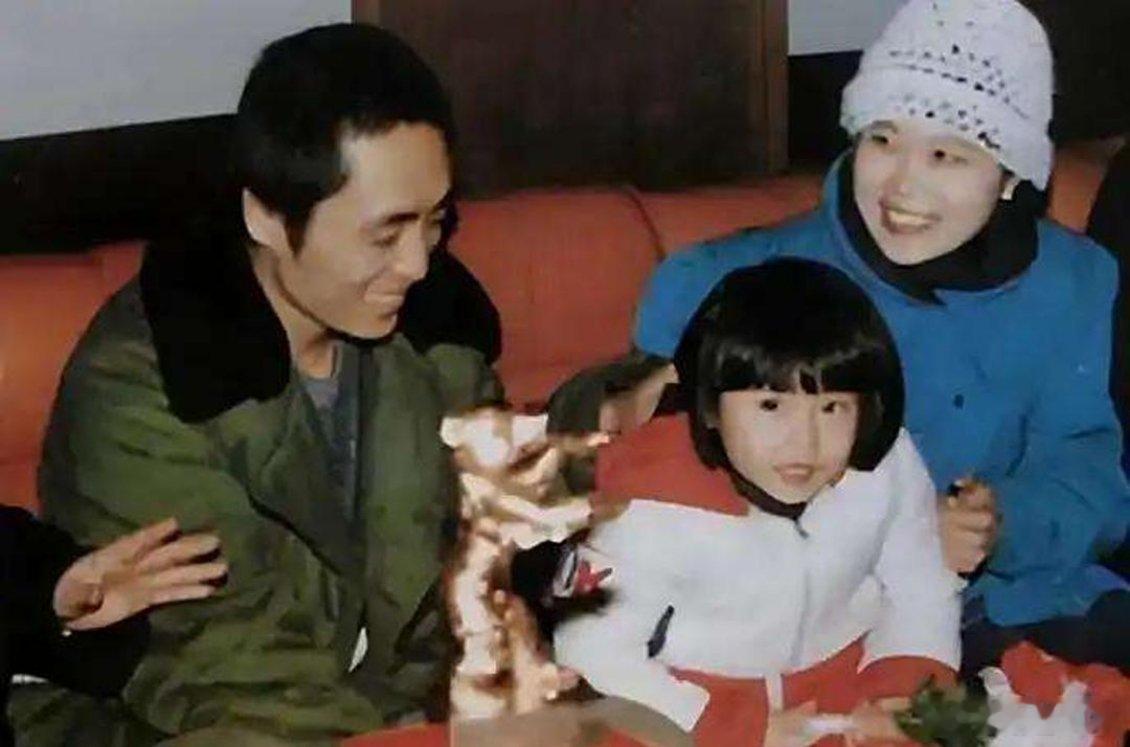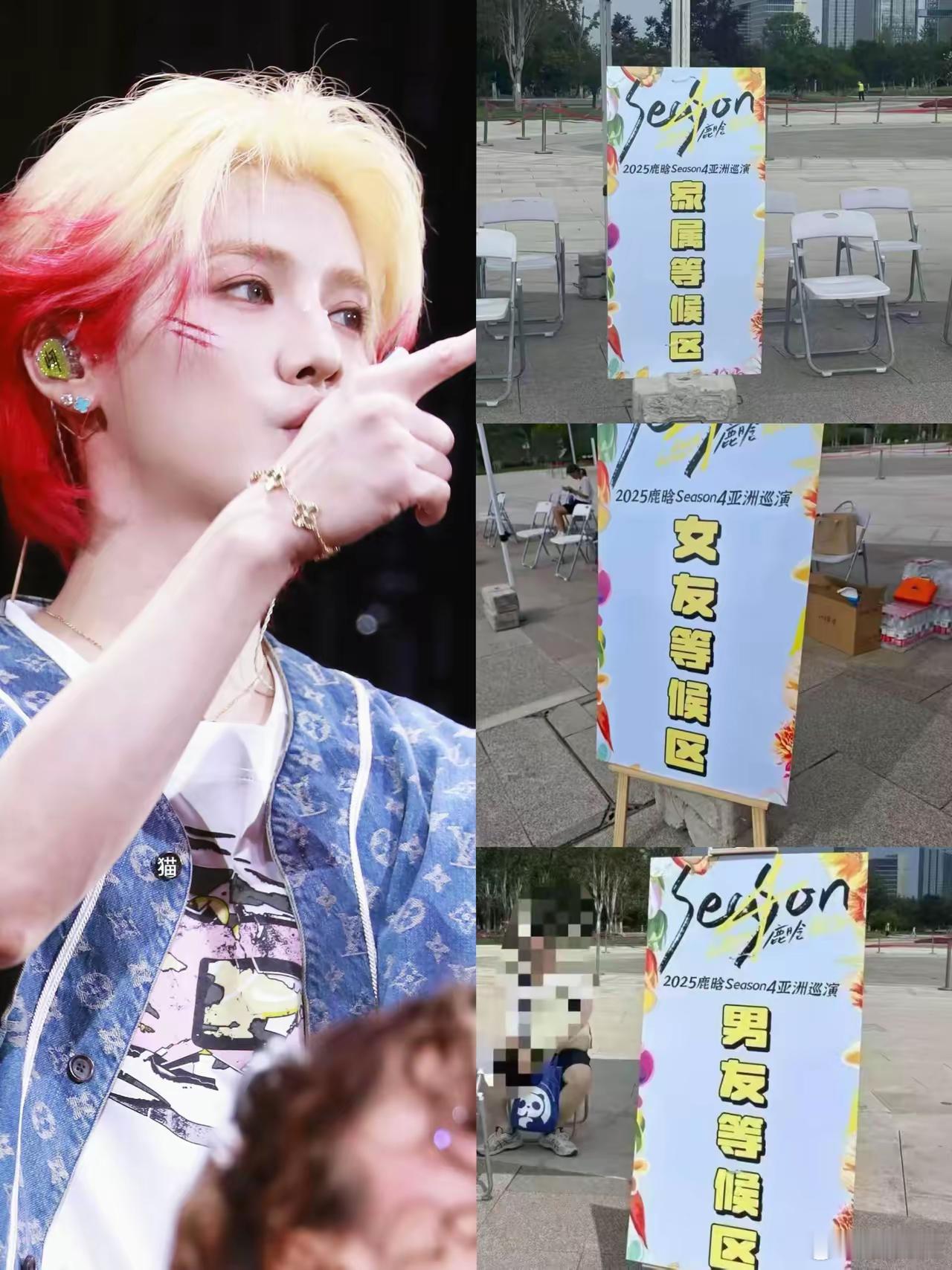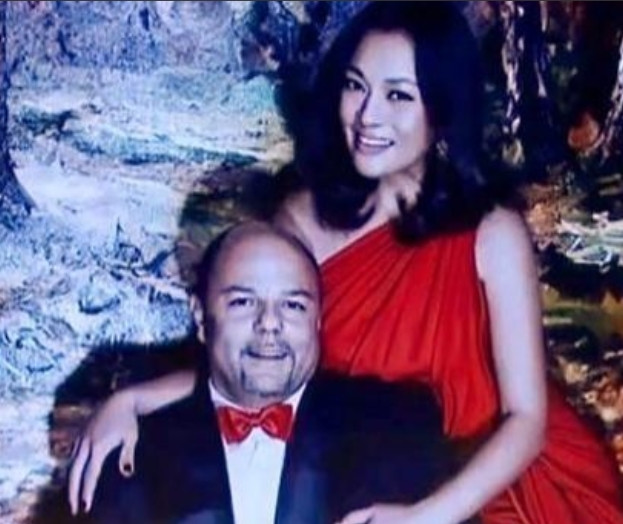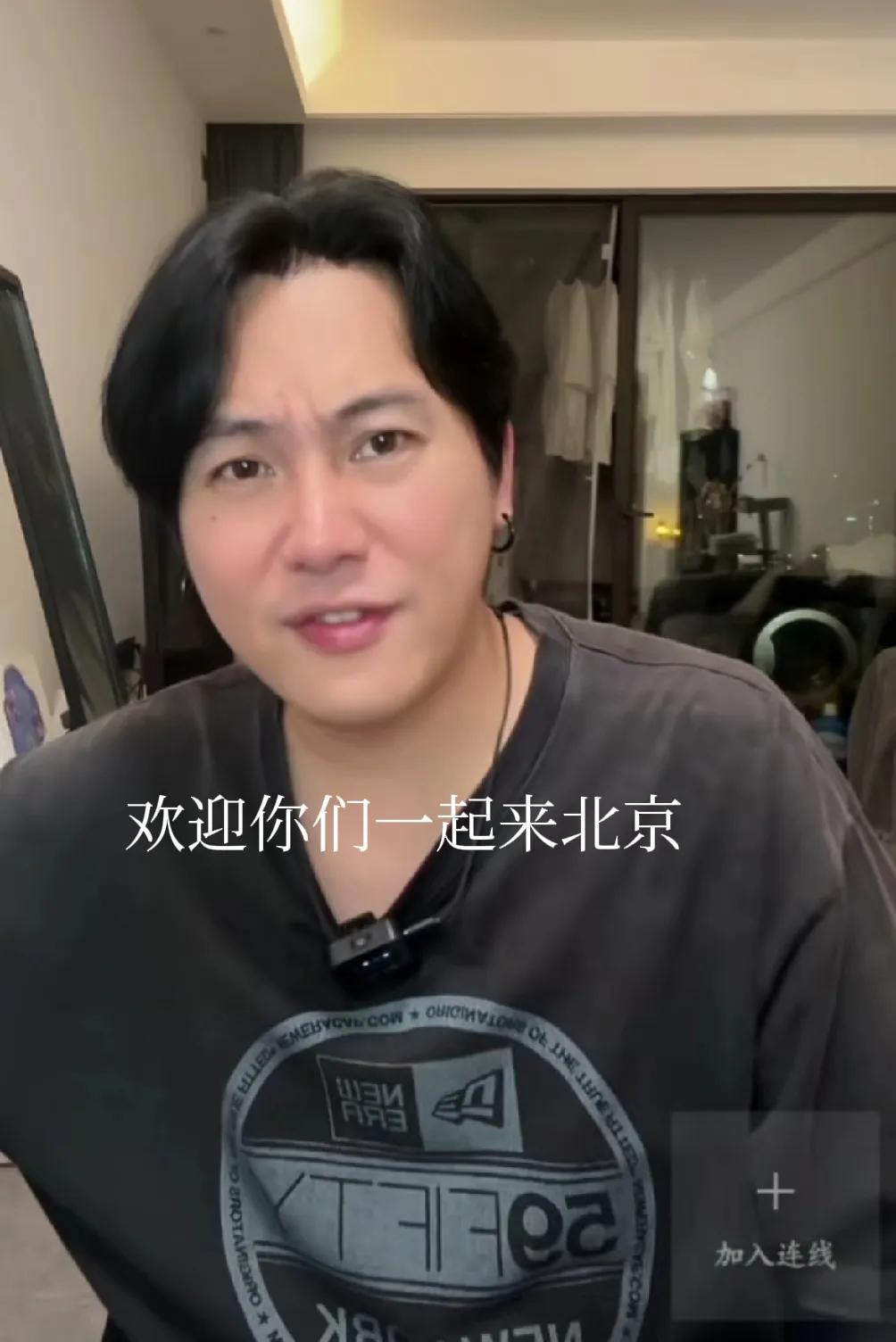张艺谋身家40亿,一回陕西老家,就去找那个修自行车的残疾弟弟,跟他说:“老弟,哥给你三个选择,要么去县城,要么去北京,要么去省城!”可弟弟头都没抬,回他:“你赶紧走吧,别赶不上二路汽车!”
1952年,在西安城墙根,张艺谋家的两间土坯房藏在胡同最里头。他父亲是参加过抗战的军人,母亲在卫生院当护士。张艺谋是老大,下面有二弟张伟谋、三弟张启谋,哥仨岁数差三岁,却常常穿着同一件打着补丁的衣服。
1966年秋天,一场变故突然降临这个普通家庭。父亲被下放到陕北农场,家里的日子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母亲白天在卫生院加班,晚上就着煤油灯缝补衣服。张艺谋放学回家,总能看见二弟张伟谋蹲在灶台前,用冻裂的手给弟弟们煮玉米糊糊。
有天夜里,母亲发现二儿子对自己的呼唤没反应,伸手一摸他耳朵,满手都是黏糊糊的脓水。当时家里连买青霉素的钱都凑不齐,张伟谋的中耳炎就这么拖成了慢性顽疾,后来彻底听不见了。
倒霉事还没完,三弟张启谋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好。有次张艺谋带他去看露天电影,银幕上的人在他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光斑。医生说是视神经萎缩,得住院治疗,可母亲翻遍抽屉,就找出三张皱巴巴的毛票,只能看着小儿子的世界一点点变黑。
1971年,19岁的张艺谋被分到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在国棉八厂的车间里,张艺谋成了最拼命的挡车工。白天扛着几十斤的棉纱在机器间穿梭,晚上就在宿舍啃借来的书。后来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他背着馒头坐火车去报到。
张伟谋听不见以后,在街道办的修配厂当学徒。有一天,他正给机床换零件,机器突然失控,飞溅的铁屑像刀子一样扎进他眼睛。等送到卫生院,右眼已经彻底看不见了。母亲抱着浑身是血的二儿子哭晕过去,张伟谋却在病床上比划着:“不碍事,左手还能干活。”
张艺谋在电影学院收到家信时,正在拍毕业作品。他连夜扒上回西安的火车,这个从不流泪的男人突然跪在地上:“二弟,是哥没本事,没照顾好你。”
张伟谋从枕头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几块皱巴巴的钱,他塞到大哥手里,用手比划:“你好好念书,家里有我。”
1984年《红高粱》在柏林拿奖,张艺谋站在领奖台上说“感谢家人”,却不知道三弟张启谋的世界已经完全陷入黑暗。
失明后的张启谋没哭,反倒笑着对母亲说:“娘,以后不用给我买灯油了。”张伟谋在胡同口支起个修车摊,兄弟俩搭伙过日子:听不见的二哥负责拧螺丝、补轮胎,看不见的三弟负责递工具、收钱。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故意把五角钱说成一元,张启谋虽然看不见,却摸出纸币大小不对。他没发火,只是笑着说:“后生,你车胎上有个小石子,我给你抠出来,下次骑车稳当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张艺谋成了家喻户晓的“国师”。他第一次开着豪车回了老家,车刚停在胡同口,差点蹭到张伟谋的修车摊。张伟谋看到车标愣了愣,很快认出从车上下来的大哥,他咧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伸手拍掉张艺谋西装上的尘土。
“二弟,跟我去北京。”张艺谋拉着弟弟粗糙的手,指关节都因为用力发白了,“我给你俩在北京买套带院子的房子,雇个保姆,看病也方便。”张伟谋却抽回手,指了指不远处的老院子,又指了指自己的修车摊,摇了摇头。
那天吃晚饭,母亲炖了羊肉,砂锅在煤炉上咕嘟咕嘟响。张艺谋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两个弟弟吃饭——张伟谋夹菜总碰翻碟子,张启谋的筷子要在碗里摸索半天。他喉咙发紧:“去县城也行,我给你们买套带门面的房,开个小超市,不用再干活。”
张启谋把一块炖烂的羊肉夹到母亲碗里,轻声说:“大哥,你忘了小时候娘总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他手指在桌上摸索着,摸到个苹果,慢慢削起皮来,果皮连成条线,没断。
“去省城?”张艺谋还不放弃,“我在西安给你们买套大平层,离医院近,二弟看病方便。”
张伟谋突然放下筷子,走到墙角翻出个铁盒,里面全是他修好的零件:磨得发亮的链条、补好的内胎、换下来的齿轮。他拿起个齿轮在大哥面前转了转,又指了指自己,一脸骄傲。这个听不见的汉子,在用自己的方式表明:我靠双手吃饭,不丢人。
母亲叹了口气,给张艺谋盛了碗汤:“你二弟三弟就喜欢守着这摊子,每天听着街坊们说话,心里踏实。”她抹了抹眼角,“去年冬天你二弟发烧,街坊们轮流来照顾,你三弟看不见,就坐在床边给他擦汗,擦了整整一夜。”
张艺谋望着窗外的老槐树,突然想起小时候爬树掏鸟窝摔下来,是二弟背着他跑三公里去卫生院;三弟把舍不得吃的水果糖塞给他,说“大哥要考大学,得补脑子”。这些回忆一下子涌上心头,他忽然明白了:有些东西,比钱更珍贵。
临走时,张启谋摸索着塞给张艺谋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花椒辣椒:“娘说你在外面总吃不好,炖肉时放一点,像家里的味道。”张伟谋则把修好的自行车铃铛挂在大哥车上,用手比划:“路上慢些。”
这世上总有一些东西,是40亿都换不来的。就像张启谋常说的:“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是过给自己心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