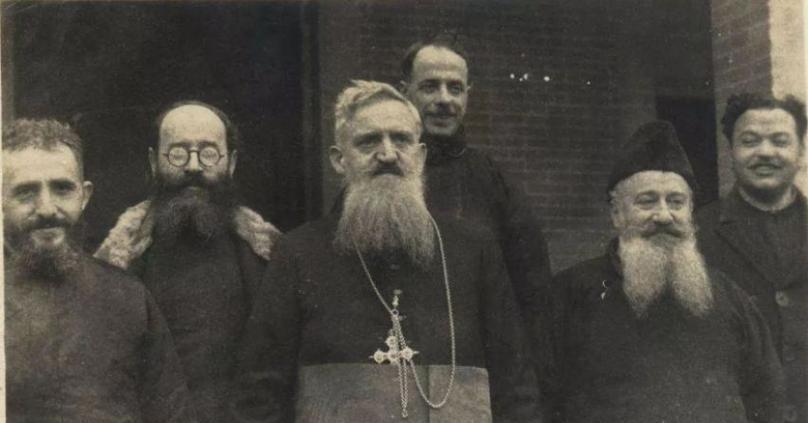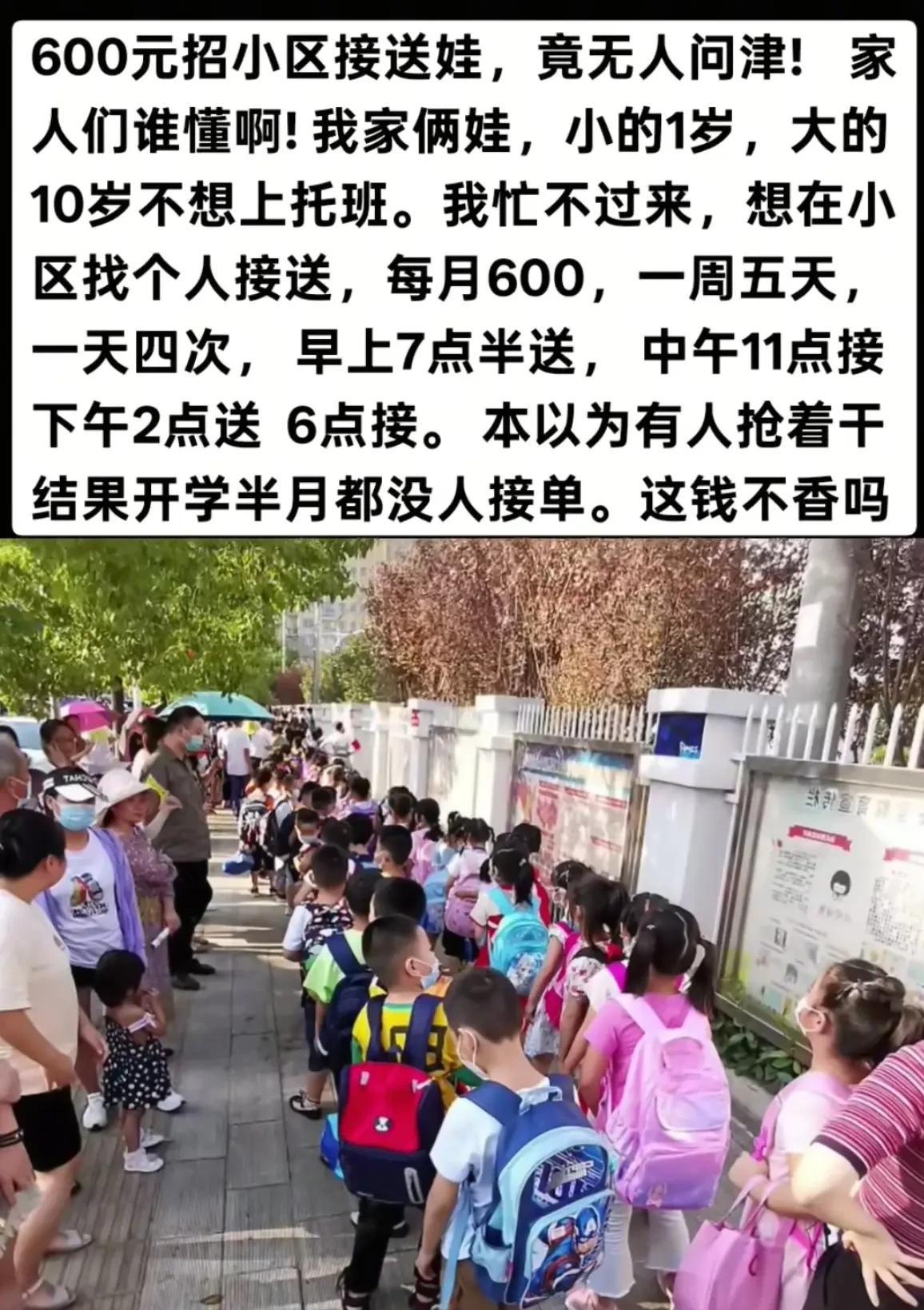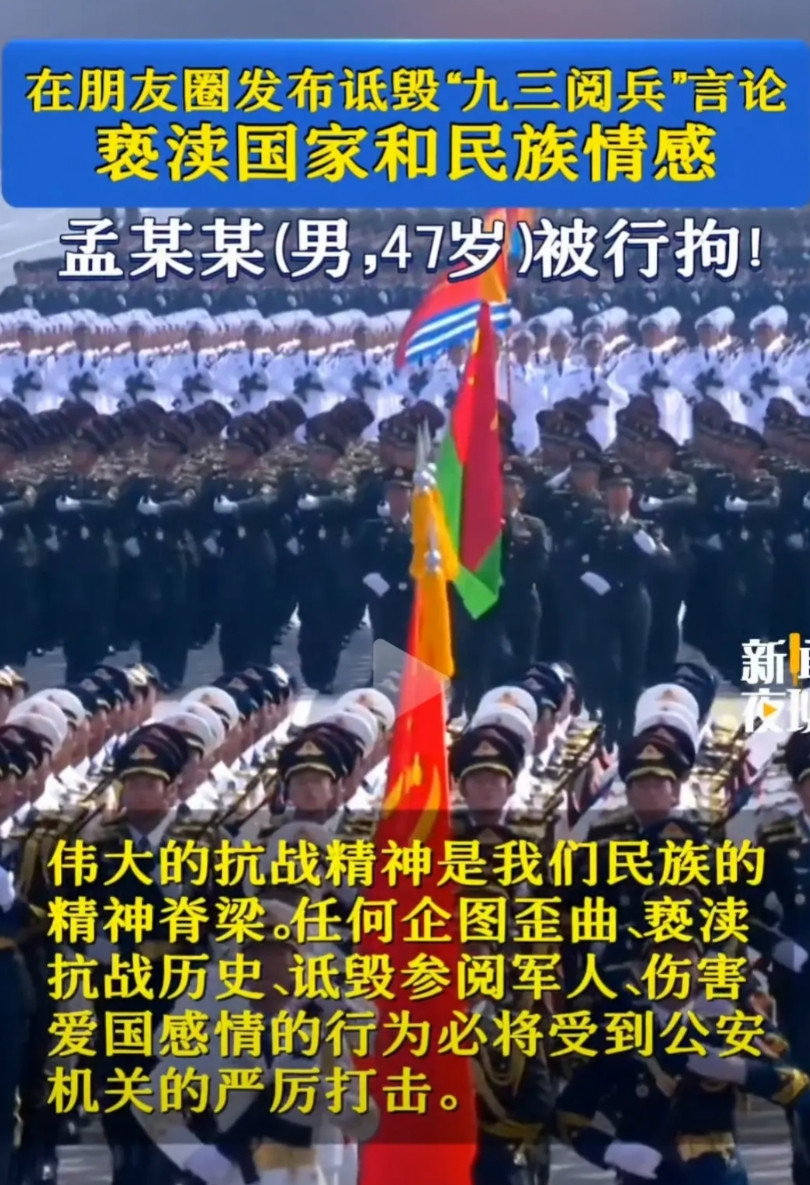北大教授刘半农,生下女儿后,对妻子说:对外就说是男孩 别人家添丁,恨不得敲锣打鼓昭告天下,他倒好,悄悄跟老婆朱惠商量:“对外就说是男孩。”朱惠听了,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丈夫的苦心,点了点头,竟真的就这么办了。要知道,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刘半农,那个在新文化运动浪潮里,亲手为汉字创造了“她”和“它”的先锋人物。一个思想如此前卫的学者,在自己家里却导演了这么一出“性别乌龙”,这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和辛酸? 聊刘半农,就不能不提他的家庭。他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刘宝珊是个老派的秀才,满脑子都是“忠孝传家,诗书继世”的规矩。在这样的家庭里,刘半农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华,六岁能诗,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可父亲的爱,是带着沉甸甸的期望和规矩的。 刘半农的婚事,就充满了这种旧式家庭的拉扯。他和妻子朱惠的缘分,可以说是阴差阳错。起初,刘半农的母亲相中了比他大三岁的朱惠,可他父亲刘宝珊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理由是“八字不合,女大三,不吉利”。朱家无奈,想把小女儿许配过来,谁知天意弄人,小女儿竟突然病逝。这下,朱家母亲铁了心,又回头提起了大女儿朱惠的亲事。刘宝珊本还犹豫,是刘半农的母亲心善,觉得不能在人家伤口上撒盐,这才拍板定了下来。 婚前,刘半农偶然见过朱惠一面,姑娘在院里洗衣服,看到他,脸一红就跑回了屋。他心里却惦记上了另一件事,回去就跟母亲念叨:“朱惠还缠着小脚呢,都什么年代了,能不能让她放了?”这话传到朱惠耳朵里,姑娘心里一热,觉得这个未来的丈夫,和别人不一样。 然而,生活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婚后几年,朱惠两次流产,都没能保住孩子。这下,刘宝善的老观念又上来了,整日里唉声叹气,话里话外都说朱惠“身子骨不中用”,甚至张罗着要给儿子纳妾。刘半农哪里肯依,为了躲避家里的压力,他干脆带着朱惠搬到了思想更开放的上海。 1916年,女儿刘小蕙终于在上海呱呱坠地。刘半农初为人父,抱着小小的女儿,心里乐开了花。可高兴劲儿还没过,他就对虚弱的妻子说出了那句开篇的话。朱惠明白,丈夫不是重男轻女,他是怕了。怕远在老家的父亲再拿没有子嗣说事,怕纳妾的阴影再次笼罩这个小家。 这一个“谎言”,是他在封建大家长的威严下,能想出的保护妻女的唯一办法。 于是,刘小蕙的童年,是在男孩子的衣服和称呼里度过的。衣服是蓝布对襟小褂,鞋子做得厚实,为的是显得“稳重”。亲友来访,朱惠从不敢抱孩子出门,只说“娃儿顽皮”。这个秘密,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却被这对夫妻小心翼翼地守护了整整九年。 这事儿想想就觉得拧巴。一个在外面大声疾呼个性解放、女性独立的知识分子,回到家却要用最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矛盾。但你细品,这恰恰是那个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他们的思想已经飞向了未来,一只脚却还深深地陷在传统的泥沼里。 最有意思的对比是,就在刘半农小心翼翼隐藏女儿性别的同时,他却在为全中国的女性做一个巨大的贡献。当时的白话文里,第三人称只有一个“他”字,男女不分。刘半农觉得这不行,“女性在书面语中,是消失的。”1920年,在前往伦敦留学的轮船上,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一经发表,“她”字第一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这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新字,更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赋予了女性独立的身份和地位。 很多守旧派骂他“胡闹”“破坏规矩”,他根本不理会,在自己的译作和文章里坚持使用“她”。他顶着全社会的压力去推动一个字的革命,却在家庭内部选择了一种妥协和退让。这种矛盾,让人唏嘘,也让人理解。 1925年,刘半农学成归国。在一次家宴上,他终于向家人和盘托出真相:“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女儿,小蕙。”据说,父亲刘宝珊当时只是放下了筷子,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老了,听不清”,便起身离席。这个持续了九年的“谎言”,就以这样一种平静到近乎冷漠的方式落幕了。那天之后,刘小蕙才第一次穿上了裙子。 刘半农的一生很短,1934年,年仅44岁的他因病去世。但他留下的,远不止几首诗和几本书。他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真实的缩影,一个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夹缝中的真实选择。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往往充满了妥协、矛盾,甚至是一些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迂回”。 这或许,才是历史最真实、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