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陆小曼在昏睡中,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她微微睁开双眼,对赵清阁笑着说:“我看见志摩了,”赵清阁俯下身子,询问她:“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陆小曼出生在一个风光的年代,也生在一个风光的家庭,父亲陆定是清朝进士,后来在北洋政府当上了财政部的高官,母亲吴曼华出自名门,家教严格,审美挑剔,这种家庭里长大的女孩,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七岁开始读书,念的是北京女子师范附小,九岁进了北京女中,十四岁就把基础课程学完了,接着进了法国圣心学堂,英语和法语都能说得流利,还学得一手好钢琴,画画也漂亮得不像话。 她的青春,是在琴声、法语和墨香里展开的,十八岁那年,已经能在外交场合当口译员,给北洋政府的高官传话,翻译文件,举止从容不失优雅,那时的陆小曼,是北平上流社会的风景线,走到哪儿都是焦点,连胡适都说她是“北平不得不看的风景”,社交场合里,她总是谈吐得体,衣着考究,才华与美貌并存,追求者自然排成长队。 十九岁那年,家里为她安排了婚姻,对方叫王赓,留学美国的高材生,西点军校毕业,是个前途无量的军人,他们在北京海军俱乐部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宾客云集,风光无限,起初的婚姻生活并不算糟糕,王赓工作繁忙,陆小曼则继续画画、写字、出入沙龙,生活看似体面,实则孤独,王赓的重心始终在公务上,家里冷清得像办事处,陆小曼日复一日地独自度日,浪漫被现实消磨得所剩无几。 命运的转向,是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开始,临行前,王赓托付好友徐志摩照顾她,这本是出于信任的安排,却无意中打开了另一扇门,徐志摩当时已经离婚,追求林徽因未果,心中空落,两人志趣相投,都爱诗画,都讲究品位,频繁接触后,感情迅速升温,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久压抑后的释放,徐志摩像是她生命中久违的共鸣,让她相信爱情还有可能。 为了这段感情,陆小曼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离婚在当时尚属禁忌,而她不仅毅然决然地与王赓分开,还承担了大笔经济赔偿,1926年,她和徐志摩在北海公园举办婚礼,场面虽简单,却轰动一时,婚礼上,证婚人梁启超公开表达反对,语气严厉,甚至预言这段婚姻不会有好结果,那一刻的警告,如今看来确实是一种命运的预告。 婚后的生活远不如想象中浪漫,陆小曼依旧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三层洋楼、司机佣人、名贵衣物,她一项都舍不得放弃,徐志摩为了维持家庭开支,在五所大学兼课,收入虽高,却难以支撑这样的开销,更糟的是,陆小曼因身体虚弱、神经衰弱,在医生翁瑞午的建议下开始吸鸦片止痛,一旦沾染上烟瘾,生活就更难自控,徐志摩几次劝阻无果,婚姻中的裂痕慢慢扩大。 1931年11月,徐志摩为节省旅费,搭乘邮政飞机前往北平参加林徽因的讲座,不料飞机在济南上空失事,年仅三十四岁的他瞬间离世,噩耗传来时,陆小曼几乎崩溃,悲痛、悔恨、自责,全数涌上心头,人们在徐志摩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张典当凭证,是陆小曼典当他怀表所留下的,这张纸成了她挥霍与依赖的象征,也成了众人责备她的证据。 徐家的态度冷酷至极,不仅拒绝她参加葬礼,还公开指责她是“间接害死志摩的人”,外界的舆论也异常残忍,所有的风言风语都指向她一个人,在这样的重压下,她选择了沉默,她停下社交,断绝外界联系,把所有精力投向画纸之上,她开始整理徐志摩的遗稿,编纂成集;她重新拿起画笔,一笔一墨地画山水、描花鸟,仿佛在用艺术为自己赎罪。 从名媛变成画师,是一个漫长又辛酸的过程,1950年代,她进入上海中国画院任职,每月工资不过八十元,为了维持生活,她将画作寄售于朵云轩,靠出售作品换取微薄收入,早年的华服珠宝早已不见踪影,她穿着补丁棉衣,住进无暖气的老公寓,日子虽清苦,却也朴实,她开始习惯早起磨墨,咳嗽加剧时便扶着桌角画画,从不抱怨。 在生活最困顿的日子里,她仍保留着底线,抗战期间,有日本商人高价邀她拍广告,她故意穿着破衣服前往,以此婉拒,她的画作越来越成熟,风格沉静内敛,晚年,她仍坚持创作,哪怕身体已不堪重负,她的生活一再压缩,但她从未放弃手中的画笔,画,是她的自尊,也是她最后的依靠。 1965年春天,她病情恶化,住进华东医院,肺气肿和哮喘让她呼吸维艰,牙齿脱落,身形枯槁,去世前不久,她将一些朋友寄存的字画托付给堂侄女保管,这一决定让不少文物得以保存,临终时,家属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只得由好友赵清阁出钱为她添置绸衣,她的遗愿是与徐志摩合葬,但被徐家的长子拒绝,她的骨灰因无人认领,被搁置在殡仪馆长达二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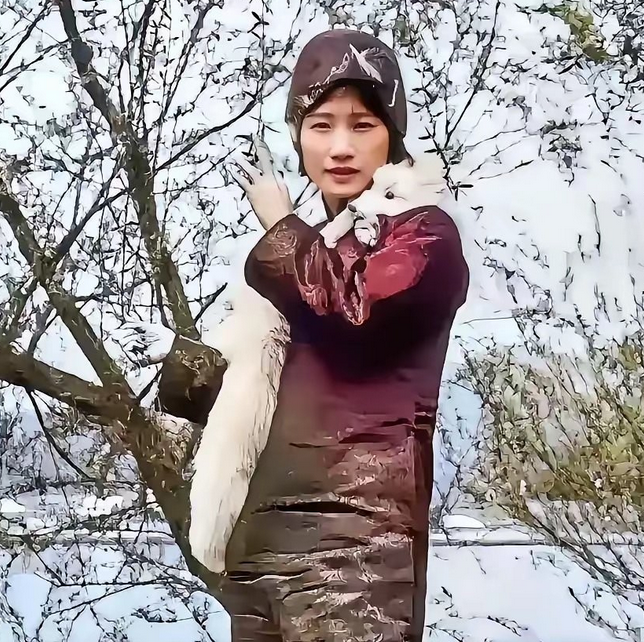








鱼翔潜底
少作一点,人生也不会这样凄凉。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