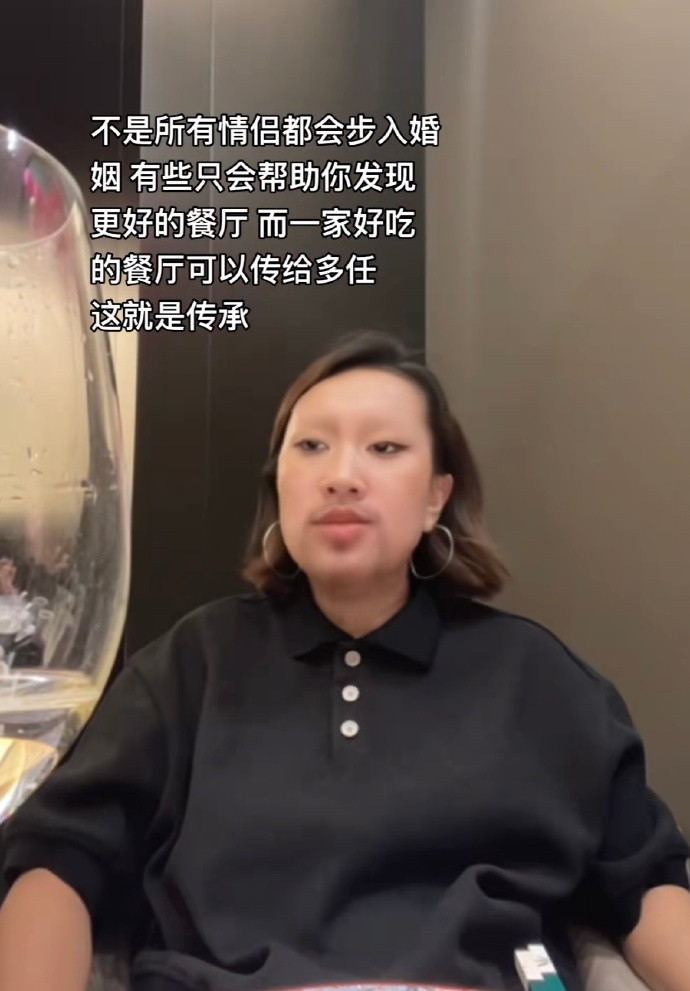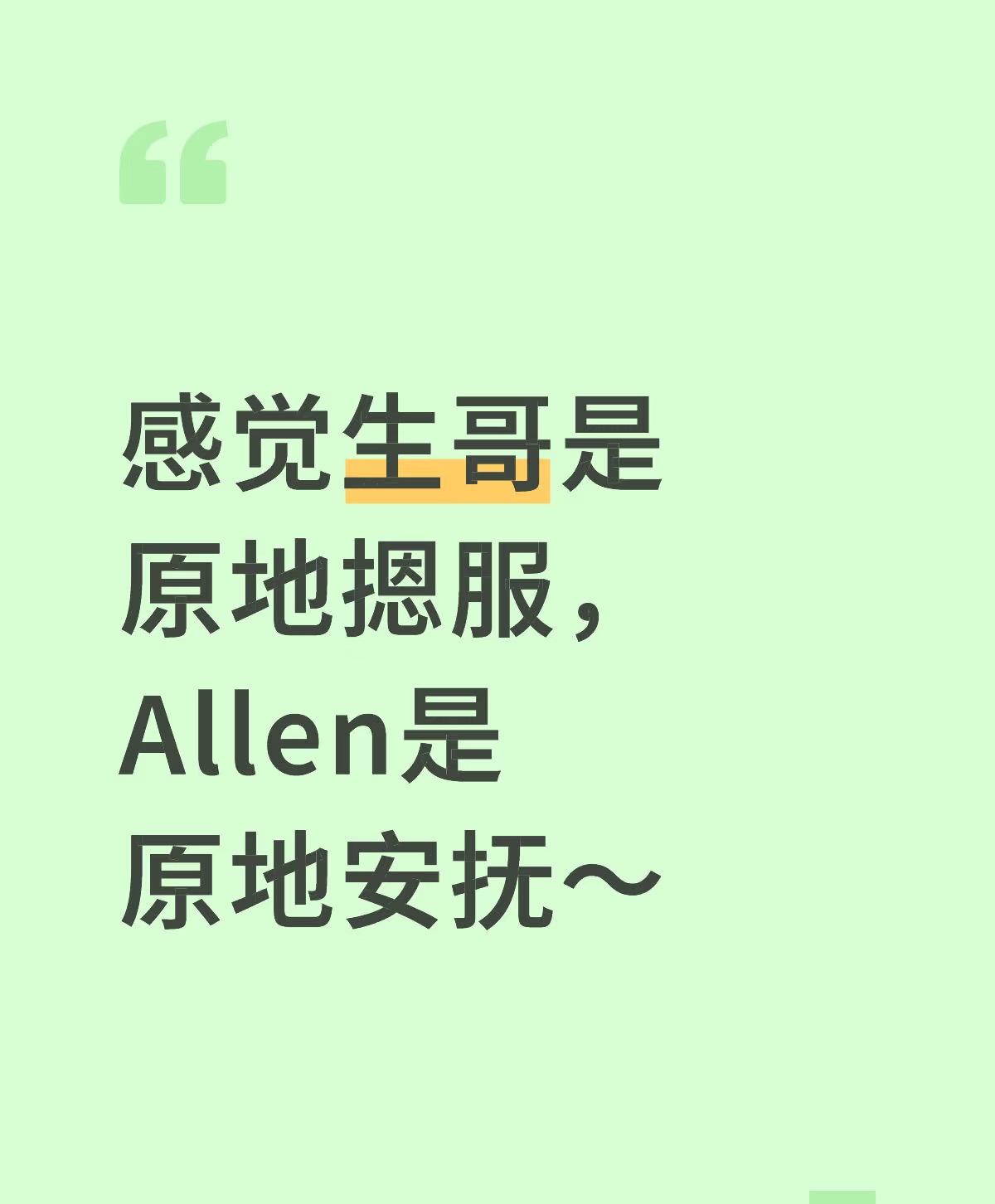1958年1月的,实验室的消毒水味里混着一丝紧张。61岁的汤飞凡卷起左袖,看着助手手里那管透明液体,平静地说:“滴吧。”当沙眼病毒顺着眼睑滑进眼球时,这位头发已泛白的科学家没眨眼。 他要亲自记录这场“人体实验”的每一个细节,从红肿到化脓,从视物模糊到几乎失明,整整40天没敢用一滴药。 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是这个近乎自虐的举动,让中国在全球沙眼研究领域抢回了话语权,而这,只是汤飞凡用命拼出来的众多突破之一。 时间倒回1943年的昆明,抗日战争正打得胶着。前线送来的伤兵一批接一批,多数不是死于枪伤,而是伤口感染后发的败血症。 那时青霉素被称作“神药”,但全靠从美国进口,一支的价钱能买两亩地,普通士兵根本用不起。 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汤飞凡看着伤员在痛苦中死去,把自己关在西郊山洞里三天三夜,出来时手里攥着张草图:“咱自己造!” 没有发酵罐,他带着学生用汽油桶改造;缺培养皿,就用土窑烧制玻璃器皿;连最关键的菌种,都是在菜市场发霉的豆腐上找到的。 有人笑话他异想天开,可他认准了一个理:“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凭啥不行?”1947年元旦那天,当第一支国产青霉素从简陋车间里产出,检测显示每支药效达到20万单位时,工人们抱着他哭了。 这意味着战场上的死亡率能降一半还多,而成本只有进口药的十分之一。 更绝的是汤飞凡的“土办法”里藏着的巧思。他发现进口青霉素总因纯度不够引发过敏,就琢磨着用活性炭吸附杂质,这个法子后来被写进国际药典。 知道前线缺冷藏设备,他又研究出干燥保存技术,让青霉素在热带气候里也能存半年。 到1948年,他的工厂每月能产10万支青霉素,不仅供国内战场,还支援了东南亚的抗日联军。有美国记者来参观,看到用汽油桶改的发酵装置时瞪了眼:“这居然能造出和辉瑞齐名的药?”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东北突然传出坏消息:鼠疫来了。 这种能通过飞沫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几天内就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哈尔滨街头开始出现戴口罩的行人。当时苏联答应支援疫苗,但运到东北至少要一个月,可疫情根本等不起。 汤飞凡接到急电时,正在整理青霉素厂的资料,他连夜带着团队坐闷罐火车赶去沈阳。临时实验室设在废弃的仓库里,窗户糊着报纸,冷风从门缝往里灌,他却在会上拍了桌子:“不用等苏联的,咱自己做,还得做得更快更好!” 别人都觉得他疯了,鼠疫疫苗常规生产要三个月,他却想在两个月内搞定。更冒险的是,他放弃了国际通用的死疫苗技术,改用减毒活疫苗。 死疫苗安全但产量低,活疫苗效价高却容易出危险。汤飞凡盯着显微镜里的菌株,跟助手说:“用乙醚处理,既能杀死病毒活性,又能保留免疫原性。” 那段时间,他几乎睡在实验室,每天只靠几口干粮充饥,眼镜片上的雾气总也擦不干净。 当第一批疫苗生产出来,检测显示免疫力比苏联的还强,剂量却少三成时,负责运输的战士们背着冷藏箱往疫区跑,汤飞凡在仓库门口看着远去的车队,腿一软坐倒在地,那时的他已经三天没合眼了。 这场仗打得漂亮,三个月后鼠疫就被扑灭,而他研发的疫苗技术,后来成了中国应对烈性传染病的范本。 很少有人知道,汤飞凡最看重的不是青霉素或鼠疫疫苗,而是沙眼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一半人受沙眼困扰,农村里“十眼九沙”是常事,严重的会瞎掉。 当时国际上都认为沙眼是细菌引起的,只有汤飞凡觉得不对劲。他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熬了五年,用了两千多只小鸡胚,终于在1955年分离出沙眼病毒。 为了证明这东西真能致病,就有了开头那次“自滴病毒”的实验。40天后,当他把自己眼睛里取出的病毒再接种到小鸡胚里,看到典型的病理变化时,激动得把显微镜都碰倒了。 这个发现让中国在微生物领域第一次领跑世界,后来国际医学界把这种病毒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的名字也永远和这个发现绑在了一起。 可这位能在实验室里创造奇迹的科学家,却没躲过时代的风浪。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有人把他的研究说成“资产阶级那套”,实验室被封,连他珍藏的菌种都被扔掉。 9月30日那天,汤飞凡在书房里写下最后几个字:“科学没有阶级,治病救人不分立场。”然后就再也没醒来。他去世后不久,国际沙眼防治组织给他寄来金质奖章,可收件人再也看不到了。 如今在湘雅医学院的校史馆里,还摆着汤飞凡当年用过的玻璃培养皿,边缘有磕碰的痕迹。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他常说的一句话:“搞科研就像打仗,得敢冲锋,还得懂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