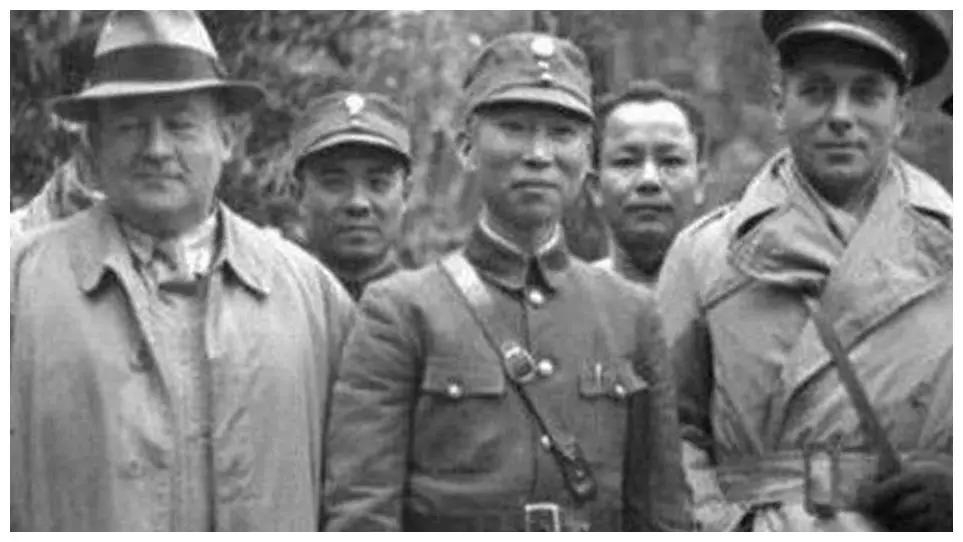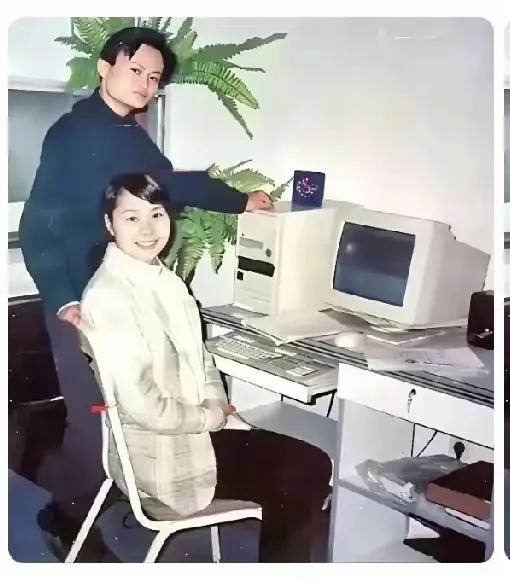1950年,陈伯达和刘淑宴领了结婚证,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这一年陈伯达46岁,而他的妻子刘淑宴才28岁,两人之间相差了18岁,属于老夫少妻组合了。
陈伯达出生在1904年的福建惠安县,原名叫陈建相。从小在农村长大,他早年就对学习感兴趣,1919年考进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那时候他每天早起背书,课余还帮家里干活。毕业后,他去了上海,当上了《厦声报》的记者,同时在上海大学文学系上课。那个年代,社会动荡,他接触到各种思想,1925年先加入国民党,干过秘书工作,但很快就转向了革命道路。1927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23岁,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不久,他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1930年回国后,在北平中国大学教书,还负责北方局的宣传事务。1931年,他被国民党抓捕,关了几年牢,坚持住了立场,1937年出狱后直奔延安。在延安,他教书育人,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工作,1939年起成了毛泽东的秘书,帮着起草文件,整理理论材料。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的马列学院当副院长,负责理论教育和宣传,生活逐渐稳定下来。
刘淑宴比陈伯达小18岁,1922年出生在四川灌县的一个穷苦家庭。她从小就懂事,帮父母干农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38年,她才16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重庆做地下情报联络。那时候,她伪装成普通职员,在国民党统治区收集消息,传递党的指示,风险很大,但她干得有条理。1949年,她跟着队伍进京,进了马列学院,从事行政和教学辅助。之前,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前夫叫刘光,早逝了,留下一个女儿刘海梅,她一个人拉扯孩子,日子也不容易。进京后,她继续工作,生活慢慢好转。 陈伯达和刘淑宴就是在马列学院认识的。那时候,陈伯达是副院长,刘淑宴在行政岗位,两人因为工作接触多起来。学院里开会讨论理论问题,他们经常碰面,交流观点。相处了两年多,他们的关系从同事变成了伴侣。1950年春天,他们决定结婚。领证那天,很简单,就去了民政部门,办了手续。陈伯达当时46岁,正处于事业高峰,刘淑宴28岁,带着女儿入住新家。
这段婚姻是陈伯达的第三次,前两次分别是和诸有仁、余文菲,都以离婚结束。第一任诸有仁是福建人,1932年结婚,生了儿子陈小达,但后来分开了。第二任余文菲是延安时期的同事,1944年结婚,生了儿子陈晓农,1948年离异。现在和刘淑宴结合,年龄差距大,但当时看起来还算融洽。他们住在北京的一个普通院子,生活朴素。 婚后,刘淑宴给陈伯达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陈岭梅,小儿子陈晓农。陈晓农其实是他们的小儿子,原名叫陈小弟,后来改的。家里多了孩子,日子热闹起来。刘淑宴负责家务和照顾小孩,陈伯达忙于工作,下班回家就看书写东西。起初几年,他们的感情还行,互相支持。陈伯达在理论界有影响力,写了不少文章,如1951年的《论毛泽东思想》,刘淑宴在学院帮忙,偶尔也当他的秘书,帮着整理资料。那个年代,大家都忙于建设新中国,他们的家庭也跟着时代节奏走。刘淑宴的性格直爽,是典型的川妹子,从小革命经历让她坚强,她不怕说实话。陈伯达呢,书生气重,工作上严谨,但家里有时脾气大。
时间推移到1967年左右,陈伯达的工作压力增大,回家后容易发火。刘淑宴察觉到变化,两人开始闹矛盾。她经常直言他的处境,让他觉得不舒服。为了避开争执,陈伯达用职权安排刘淑宴去山东的一个部队疗养所休养。她去了后,很不满,多次写报告要求回来,但没回应。有一次,她在街上发泄不满,当地负责人封锁街道,让她闹腾,但不让她走。最终,他们的离婚申请获批,从此分居两地。刘淑宴留在山东,陈伯达在北京,两人再没见面,就这么老死不相往来。 陈伯达的晚年过得孤单。1988年转到北京市文史馆,继续研究书籍,写了些文章,比如1982年的《求知难》,用笔名纪训发表。1989年9月20日,他因心肌梗死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85岁。丧事简单,由小儿子陈晓农操持,没什么仪式。刘淑宴没去现场,只送了个花圈。陈伯达留下的财产大约两万元,大部分给了陈晓农一家。陈晓农是他们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张兰华,一家子照顾陈伯达的晚年生活。陈晓农后来在出版社工作,帮父亲整理遗稿。刘淑宴呢,1996年6月去世,享年74岁。她一生革命,早年吃苦,晚年独自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