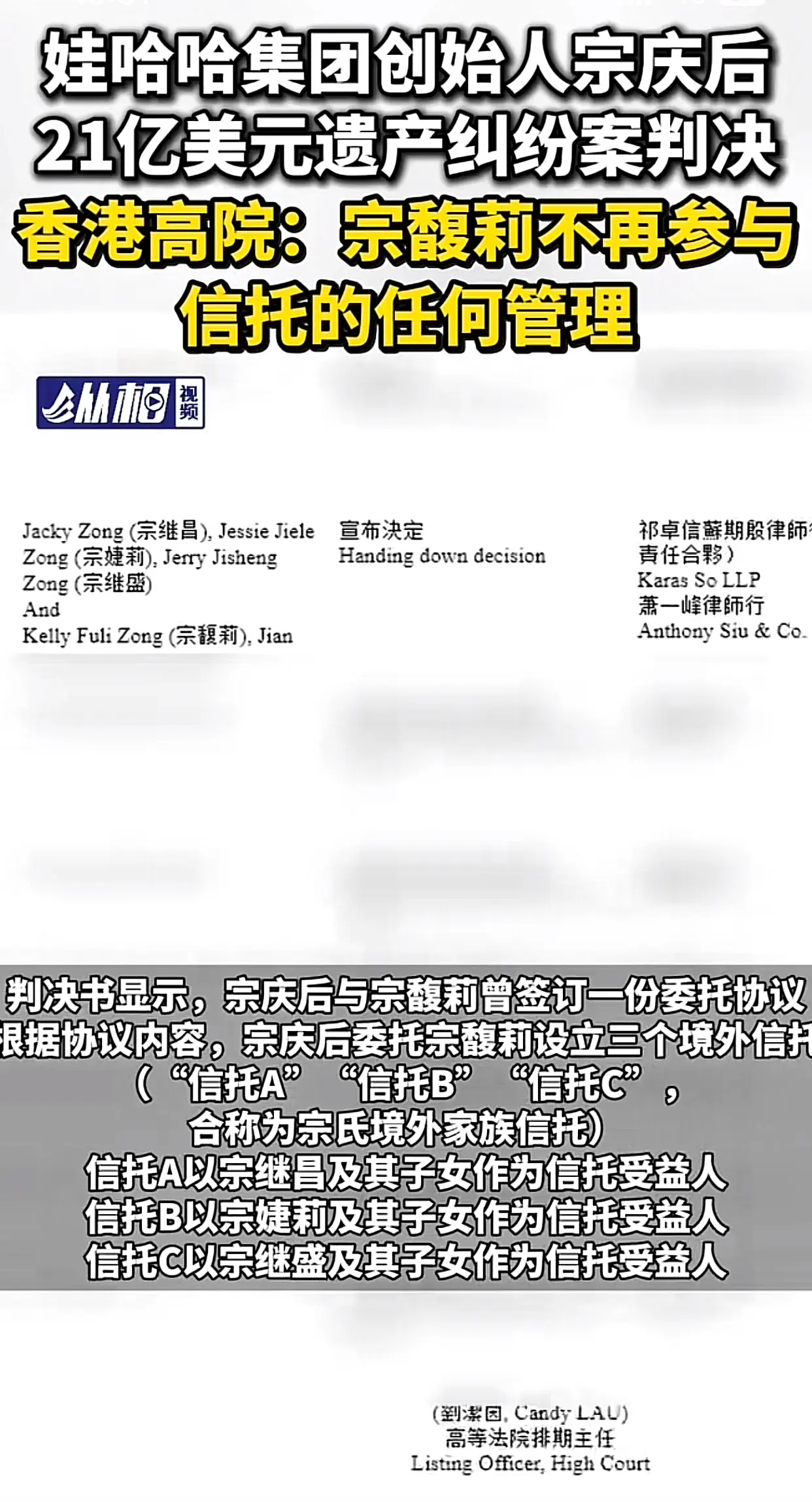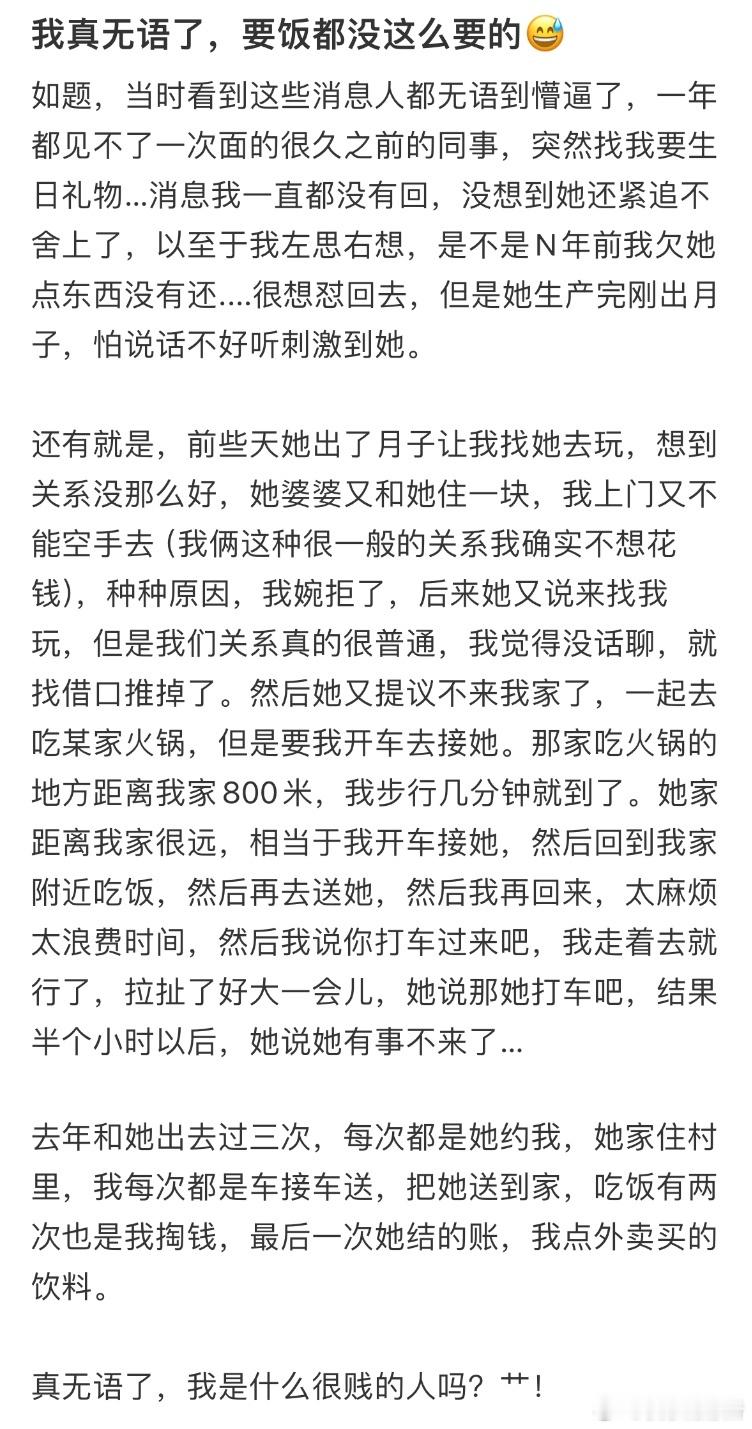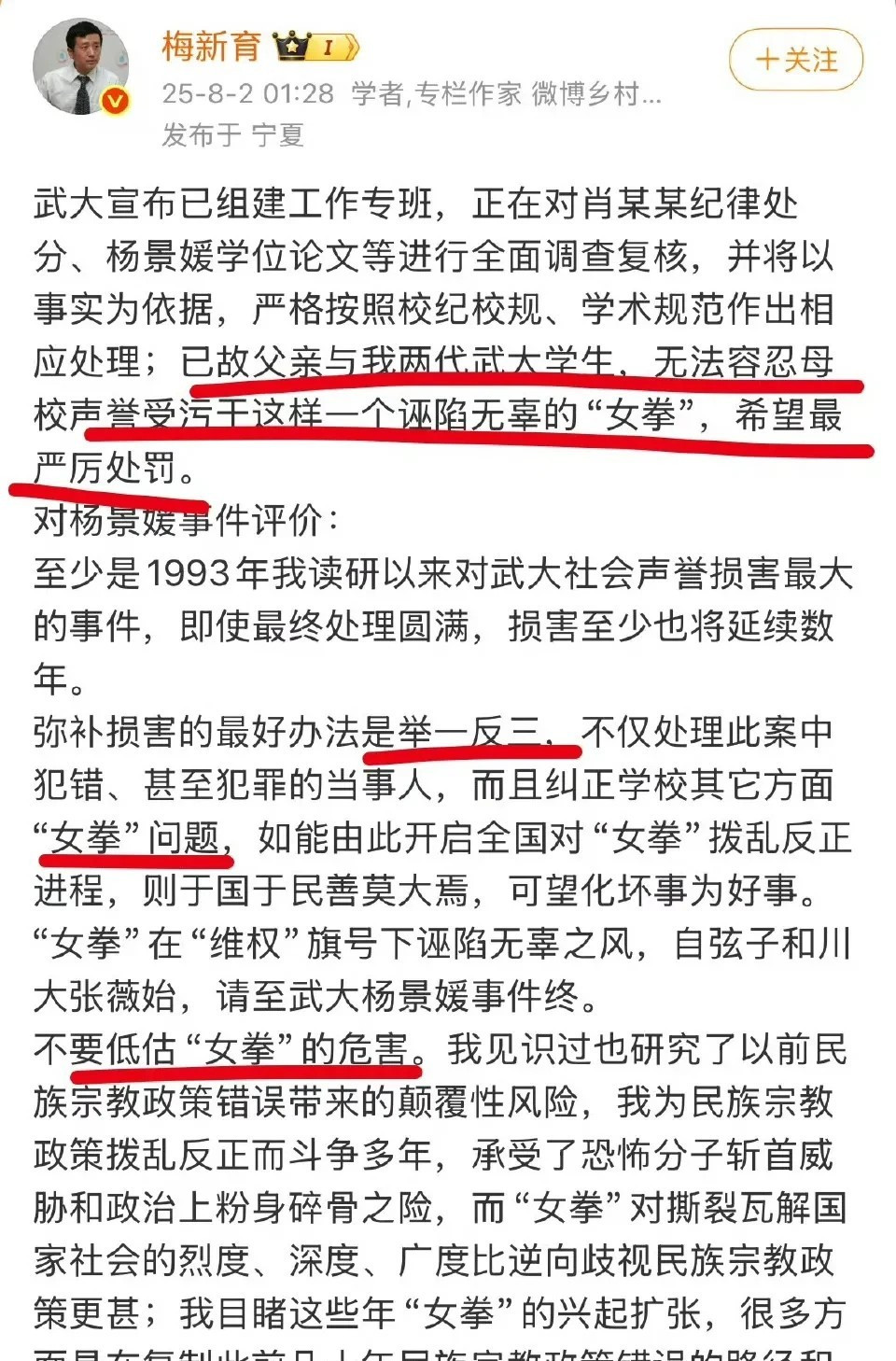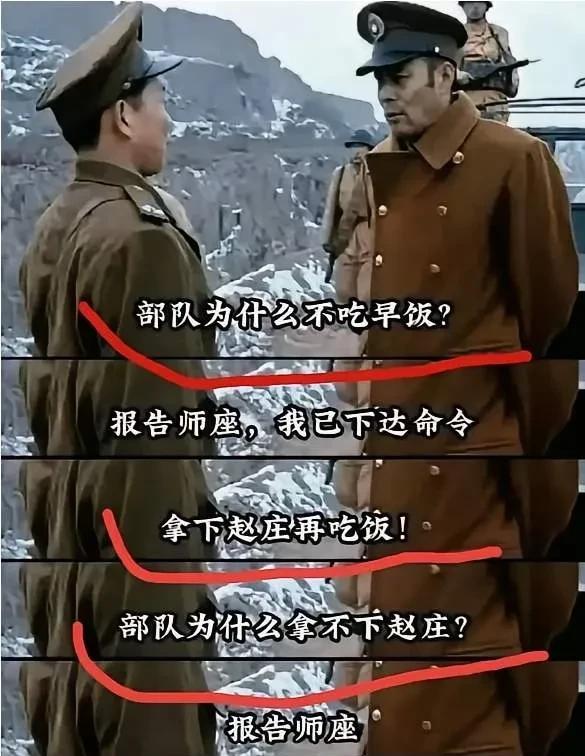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子里付之一炬。
在当时,我心里是不同意这些做法的。但我却自嘲自解:许多珍本古籍,本来用处不大,至于名人字画,我本来反对附庸风雅,不感兴趣,多年来都不曾挂出。
因此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场不可理解的‘革命’的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
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
因为这两部书是布面精装,又很厚,一时烧不着,便挑出来一页页撕着烧……
我站在旁边,心中十分难过,心想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忍受下来了,为什么这两部普通的工具书也不放过,是我无法物归原主,铸成终生的遗憾呢?”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2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