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雅加达街边摆摊的梅州夫妻,收养了一个印尼弃婴,谁料这个男孩越长越凶巴巴,活像金刚狼,给夫妻俩不断带来惊险,动荡和梦幻般的传奇,甚至影响了中国梅州。 熊德龙这家伙,出生在1947年印尼,几个月大就被扔在孤儿院门口,生母是印尼人,生父据说是荷兰人,反正没人要他。孤儿院条件差,他营养不良,身体瘦弱,性格还挺孤僻。 幸好碰上熊如淡和黄凤娇这对从广东梅州过来的客家夫妇收养了他。 熊如淡夫妻俩是1938年从梅州梅县迁到印尼的。那会儿国内战乱,老家的田地被洪水冲了,家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才跟着同乡挤上开往印尼的货船。 到了雅加达,没本钱租店面,就把摊子支在老市场的拐角,天不亮就得起来磨米浆、炸油角,黄凤娇的手常年泡在冷水里,冬天都裂着口子,涂再多猪油也不管用。可夫妻俩从没抱怨过,总说“客家儿女不怕苦,有手有脚就能挣饭吃”。 收养熊德龙后,家里日子更紧了。黄凤娇每天多蒸一个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全剥给熊德龙; 熊如淡晚上收摊后,会抱着他坐在摊子旁,用生硬的印尼语教他数数,偶尔还哼几句客家山歌。刚开始熊德龙怯生生的,总躲在黄凤娇身后,可没过半年,就露出了“凶巴巴”的性子——有次邻居家的孩子笑他“没爹没妈”,他抄起地上的木勺就冲上去,把人打得哭着跑回家。 黄凤娇没骂他,只是拉着他的手,用客家话慢慢说:“咱不惹事,但也不能受欺负。可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得让自己变强,别人才不敢小瞧你。” 这话熊德龙记了一辈子。十几岁时,他就帮着养父母看摊,算帐分毫不差,遇到故意找茬的顾客,他也敢站出来理论,语气硬邦邦的,却句句在理,久而久之,连市场里的老商户都知道“熊家那小子不好惹”。 可他对养父母从来软和,每天收摊后,都会主动帮黄凤娇捶背,帮熊如淡清洗摊子,有次熊如淡感冒发烧,他守在床边熬了一夜的姜茶,天亮时自己倒在床边睡着了。 1965年印尼时局动荡,排华风波突然起来,不少华侨的店铺被砸,熊家的小摊也没能幸免。有天夜里,几个当地人拿着棍子冲过来,嚷嚷着要“把中国人赶出去”,熊如淡想冲上去护摊子,被熊德龙死死拉住。 他把养父母推进里屋,自己拿着菜刀守在门口,眼神狠厉得像头小豹子:“这摊子是我们靠血汗挣的,要砸先砸我!” 就这么对峙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巡逻的警察赶来,才把人赶走。事后黄凤娇抱着他哭,他却笑着擦去她的眼泪:“妈,我长大了,该我护着你们了。” 风波过后,熊德龙知道光靠小摊不行,得做更大的生意。他先是跟着同乡去卖布料,每天背着几十斤的布包跑遍雅加达的大街小巷,脚上磨出了血泡也不歇着; 后来又涉足烟草贸易,刚开始没少碰壁,有次被合伙人骗走了所有本钱,他躲在出租屋里几天没出门。熊如淡找到他,没说别的,只递给他一碗温热的客家腌面:“客家男人不怕输,输了再挣回来。” 就凭着这句话,熊德龙重新振作,从最小的订单做起,慢慢积累客户,到70年代末,已经在雅加达开了三家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甚至把养父母的客家小吃改良成包装食品,卖到了东南亚各地。 1980年,熊德龙第一次跟着养父母回梅州老家。站在梅县的老房子前,听着街头巷尾熟悉的客家话,尝着久违的酿豆腐,他突然明白了养父母常说的“根”是什么。从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回乡,先是捐钱修了村里的小学,又出资建了梅县华侨中学,还专门设立了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困的客家孩子读书。 后来他牵头成立了印尼梅州同乡会,带着一批又一批印尼华侨回梅州投资,建工厂、修公路,把东南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了回来。 有人问他,为什么对梅州这么上心,他总说:“我虽然生在印尼,身上流着荷兰和印尼的血,但养我的是客家父母,教我的是客家道理。 他们没给我金山银山,却给了我做人的底气,这底气的根,就在梅州。”这些年,在他的带动下,梅州和印尼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不少梅州年轻人也去印尼发展,把客家文化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熊德龙的一生,哪是什么“金刚狼”的莽撞,不过是被爱养出来的坚韧——养父母的爱,让他从孤僻弃婴长成有担当的人;对养父母的孝,让他记挂着梅州的根。他的传奇,从来不是靠运气,是靠客家人“敢闯敢拼、不忘本”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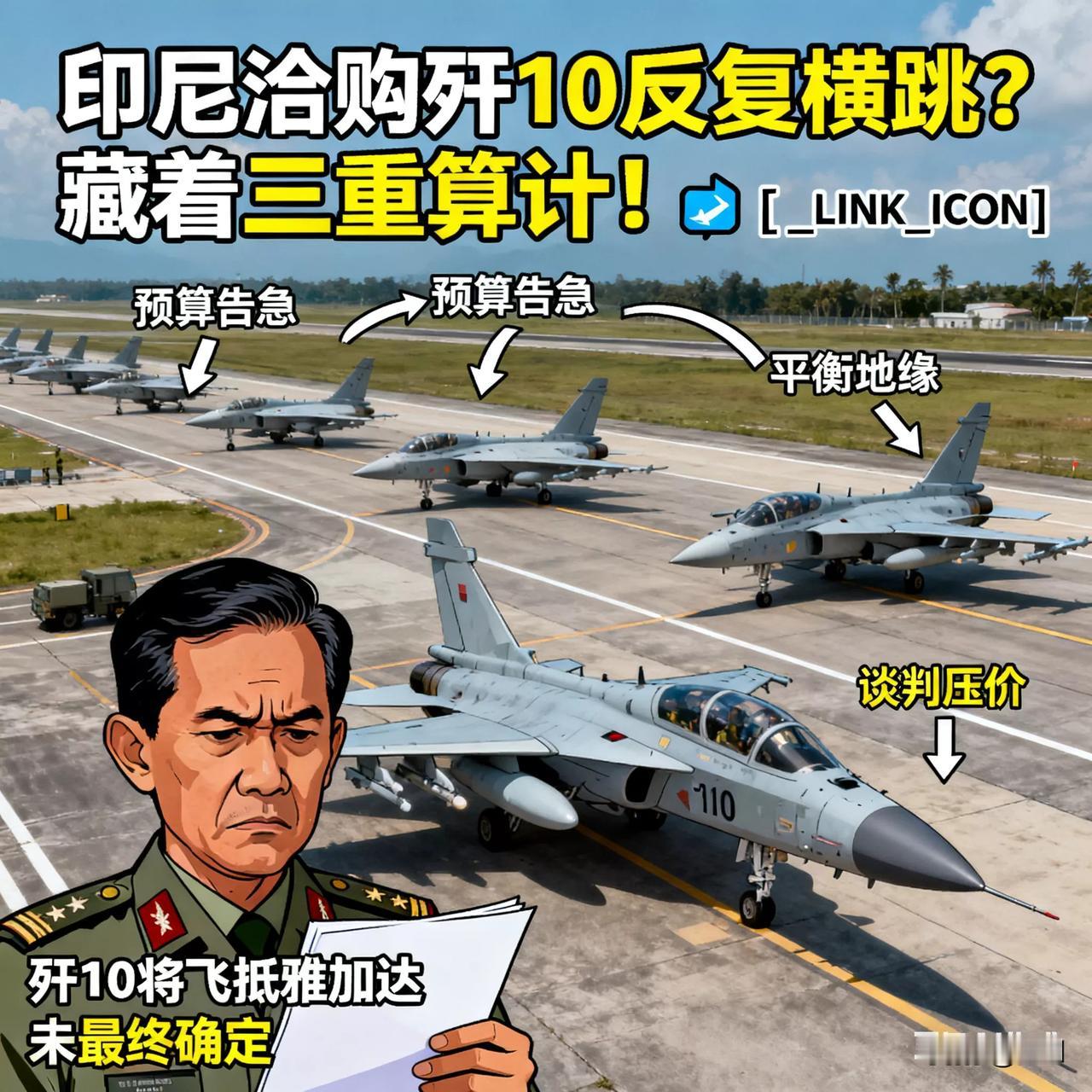





冲锋陷阵
知道感恩的人[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