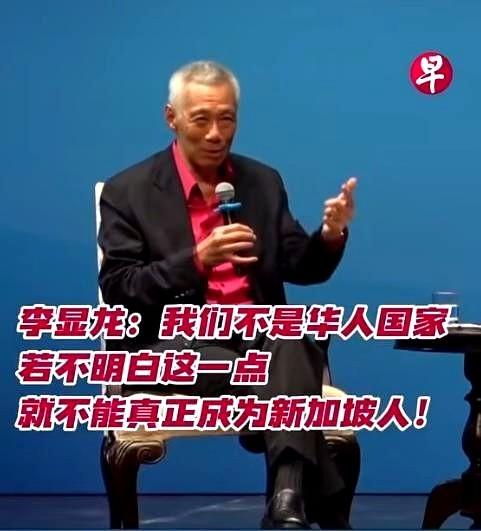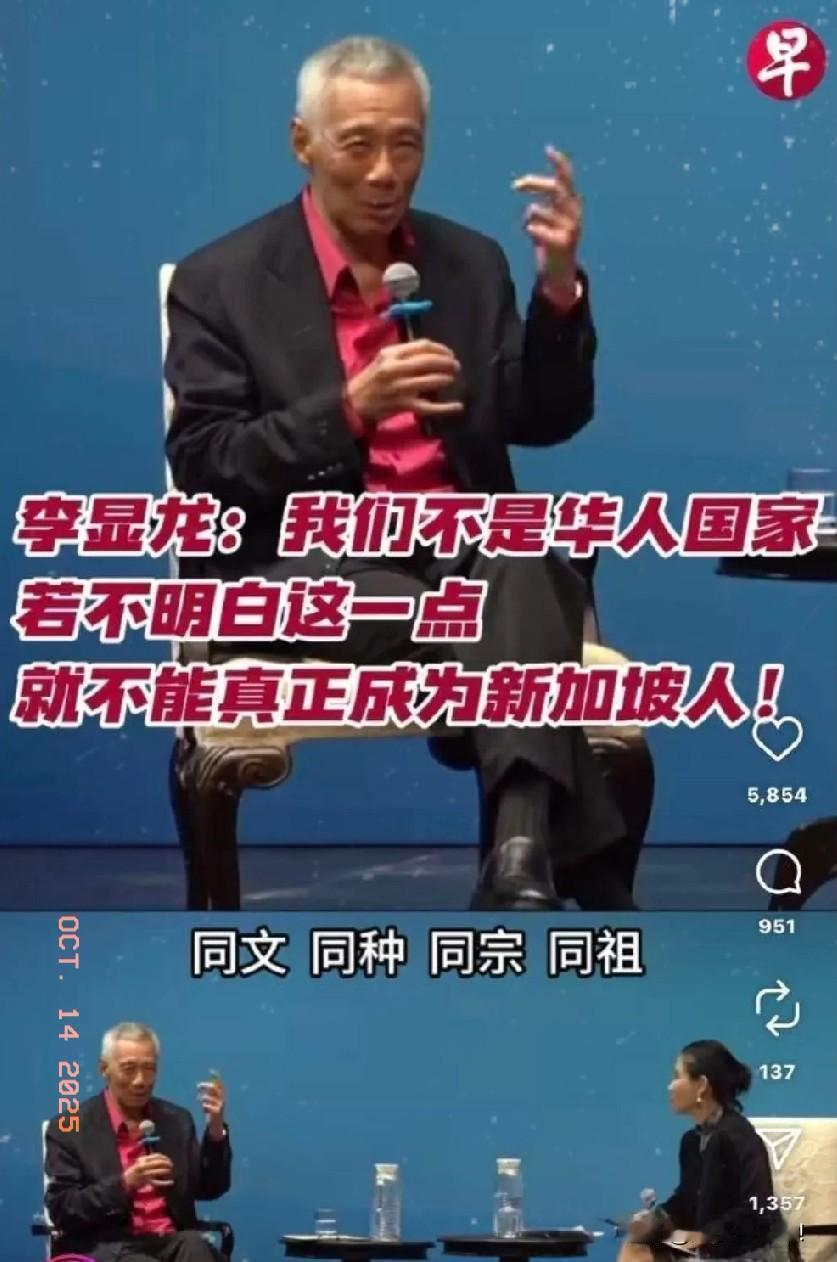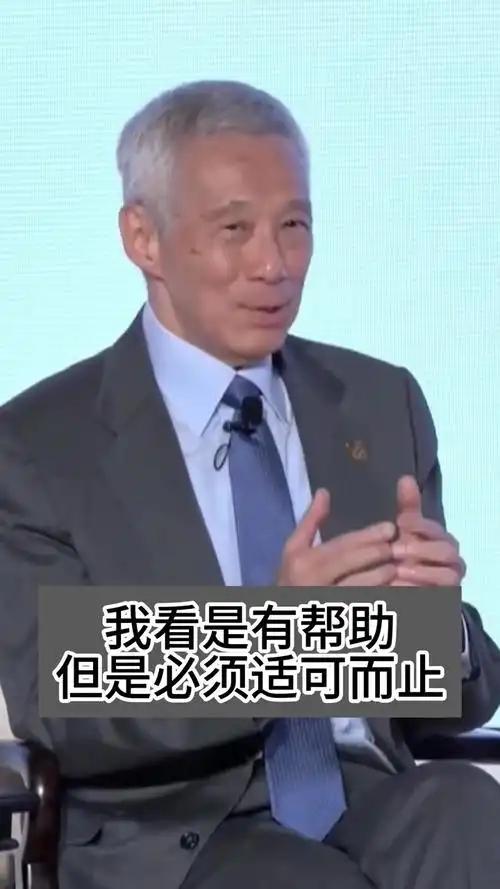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一家三口来自东北,移民新加坡多年,住在组屋。父母都是高知,女儿在新加坡名校就读,曾是学霸,拥有剑桥博士学位,但后来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10月6日清晨,新加坡勿洛一栋组屋7楼的曾先生接到母亲的电话:“你家天花板漏水了,味道很奇怪。” 他赶回家,仰头一看,天花板上渗出的不是水,是一滩暗红色的粘液,混杂着令人作呕的异味。 他立刻报了警,几个小时后,警察撬开8楼那户紧闭的门,现场令人震惊:屋里一男一女双双倒毙,男子已化为白骨,女子则瘦得皮包骨。 屋内没有挣扎痕迹,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一切,像是“安静”地死去。 死者是父女,来自中国东北,移民新加坡已近30年。 父亲徐建国,曾是大学讲师;女儿徐娜,曾是新加坡文教界的传奇人物。 1997年,她是全国华文写作冠军;2001年,她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2003年,完成硕士学位;2008年,她拿到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 剑桥博士死在组屋里,死因疑为长时间得不到照顾、饿死;她的父亲,早已死去数月,遗体腐烂殆尽。 整个社区,直到尸体渗出的体液和恶臭蔓延到楼下,才察觉到这对父女的存在。 2016年,母亲因病去世,此后,徐家的门几乎就没再打开过。 起初,大家以为他们只是伤心,父女依旧住在一起,父亲偶尔出门买菜,戴着帽子和口罩,很少说话;女儿则几乎不再出门,时间久了,邻居们习惯了“这家人沉默寡言”的状态。 这场悲剧并非毫无征兆。 徐娜从剑桥回来后,曾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过几年,但后来突然辞职回国,在那之后,她的履历断了。 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有熟人说,她精神状态“像变了一个人”;也有人说,她开始迷信,甚至怀疑周围人要害她。 她曾尝试找工作,却屡屡失败,她的Facebook在2014年后再无更新。 母亲去世后,家中只剩她和父亲,父亲年事已高,本身就有慢性病,但为了照顾女儿,他独自扛起了生活的全部。 邻居曾看到他一次拎着重物上楼,喘得不行,有人想帮,他摆摆手:“不用,我们很好。” 这是“体面”的代价。 徐娜可能不愿被外界看到她如今的样子,她是曾经的“天之骄子”,她的名字写在奖项里、毕业证书上、学术论文中。 她不想被看见她崩溃、失控、需要帮助的一面,于是,她选择了沉默,选择了不伸手。 她父亲也一样,一个高知家庭,在新加坡这样一个福利完善的国家里,硬是活成了“隐形人”。 “不是制度不够好,而是他们不配合。”这是很多人在看到这个新闻后的第一反应。 可这真的是“配合”的问题吗? 这场悲剧,也是现代都市邻里关系的一面镜子。 在新加坡,组屋是邻里制度的核心,大家住得近,低头不见抬头见,但这种“近”,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不打扰”,越来越害怕“多管闲事”,哪怕闻到臭味、听到奇怪的动静,也常常选择“装作没看见”。 “万一是误会呢?”“人家可能不喜欢被打扰。”——总是用这些话说服自己,最终让一个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徐娜的死,也敲响了另一个警钟:精神健康,是幸福大厦里最容易塌陷的一块基石。 她是新加坡教育体制下的“优等生”,是无数人梦想的终点,但她的精神崩溃告诉我们,教育和学历不是心理健康的保障。 尤其是高知群体,他们的精神压力常常被忽视,成功、光环、责任,这些词汇在某些时刻,不是荣耀,是枷锁。 人们太容易为别人的“体面”鼓掌,却忘了体面的背后,可能是无声的崩溃。 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老人被迫照顾比自己更需要照顾的人,一个80岁的父亲照顾50岁的女儿,看似可行,实则危险。 一旦这个“照料者”突然倒下,整个系统就崩了。而这个系统,仅仅是一个两人的家庭。 没有支援,没有替代方案,也没有预警机制。 老年人不是万能的,他们本身就是需要照顾的群体,这个问题在新加坡,甚至全世界,都越来越普遍,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徐家的门已经被打开了,但无数个“徐家”,可能还在沉默之中,他们不哭不闹,不求助不呼救,只是安静地,从社会的边缘,一点点滑落。 这不仅是一场悲剧的终点,更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否的试金石,不能等到臭味飘出天花板,才知道隔壁有人死了。 信源:中华网——男子在家中死亡 女儿疑伴尸多月后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