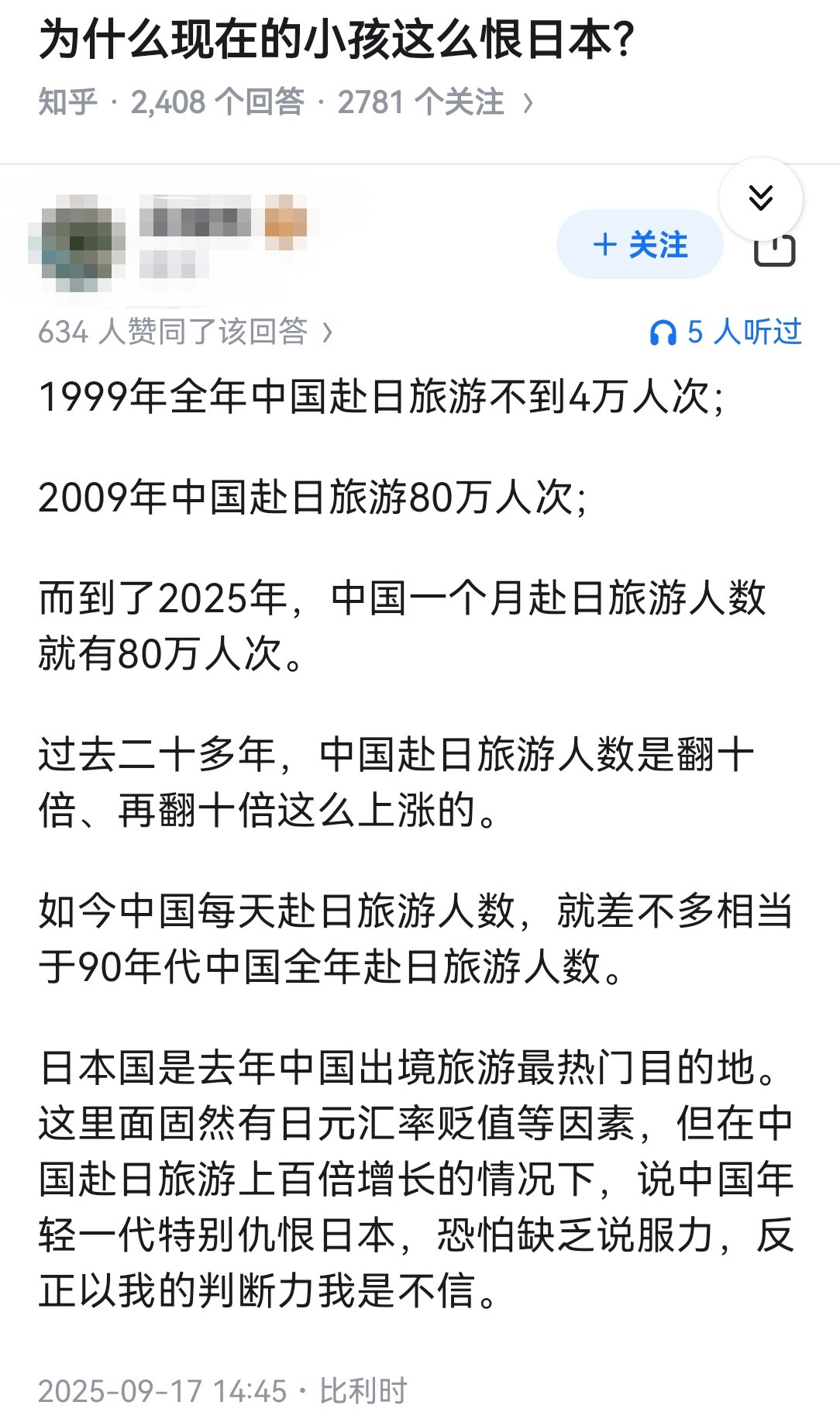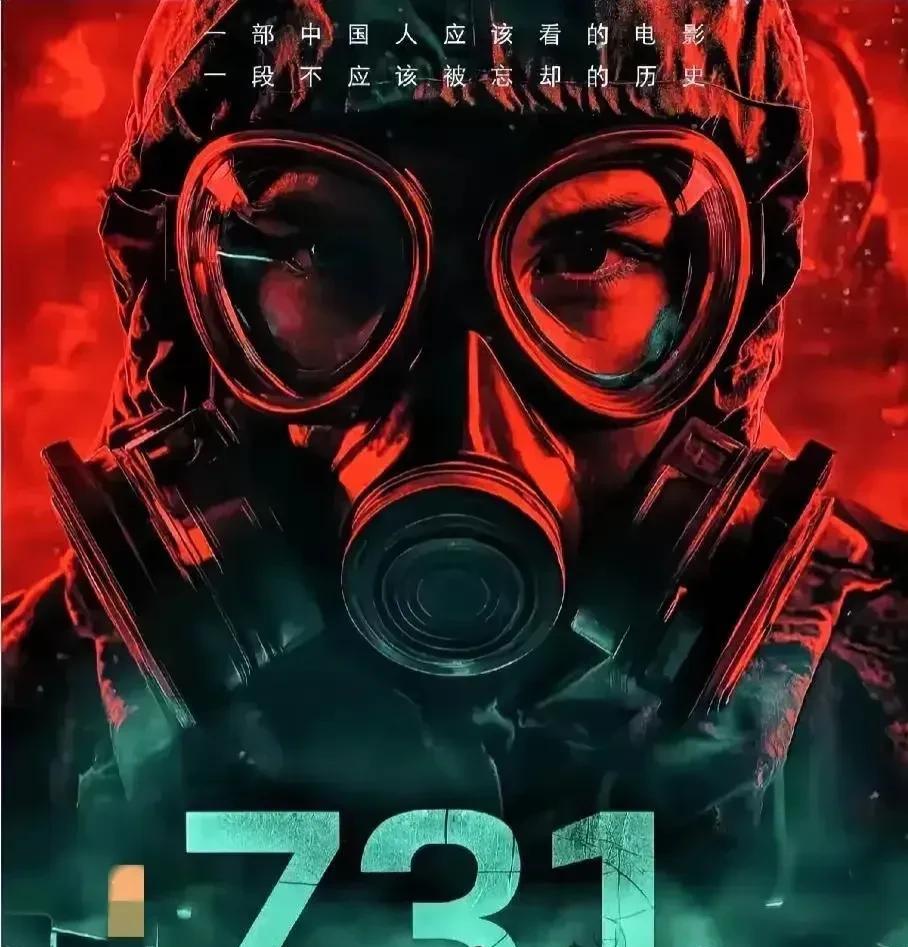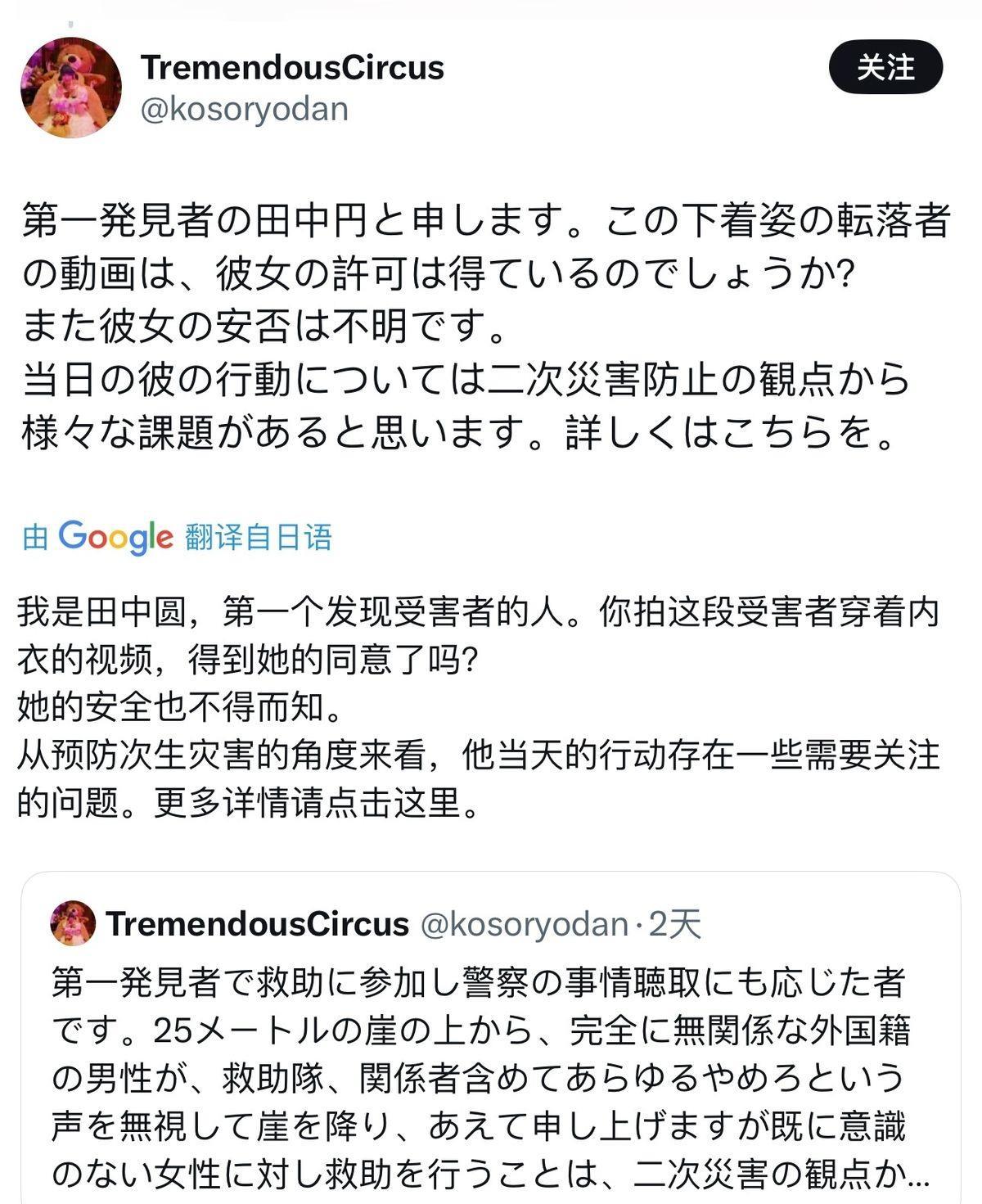她为了让日本亲口承认对华发动的细菌战,散尽百万家财,与日本打了41场国际官司,最终让日本不得不承认731对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随着9月18日《731》电影的热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好奇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曾经的经历如同跑马灯一般再次在我们的眼前炸开。 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女士,一直在为当年的历史真相奔波。 台灯下的稿纸堆得比老花镜还高,73岁的王选右手捏着红笔,左手食指反复摩挲着纸上“1943年金华潭头乡”这行字。 “陈老说,1岁那年嘴烂得吃不了米糊,娘就把米汤抹在他嘴唇上,一擦就是血。” 王选的红笔在“陈有升”三个字旁画了个圈,圈住的不仅是个名字,更是一段刻在身体上的历史。 她总说,细菌战的记忆最顽固,它不藏在档案馆的铁盒里,而在受害者的皮肤上、骨头里。 就像衢州柯城区的杨银花老人,92岁的她床头总放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每天要换三次——左腿的溃烂伤口会渗液。 布上的黄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80年下来,那块布的纤维里都浸着化不开的痛苦。 这些“身体档案”,是南香红写《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时最不敢细写的部分。 2002年第一次跟着王选去崇山村,南香红在村民自建的纪念馆里看见一堵石碑,400多个死难者的名字刻得密密麻麻。 “有个老人说,这碑是用5角、1元凑钱立的,就怕后人忘了1942年村里死了一半人。” 南香红后来在书中写,那天她蹲在碑前,手指顺着“王阿木”的笔画走,突然明白王选说的“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 王选最初被拉进这场“记忆打捞”,是1994年冬天的一顿晚饭。 叔叔王焕斌把一碗义乌土烧推到她面前,说村里要告日本政府,“你在日本待过,会说日语,得帮衬”。 那时候她在日本有年薪50万的工作,住带阳台的公寓,周末还能去看樱花。 可当她翻到叔叔整理的《崇山村鼠疫死亡名单》,看到“王樟木,13岁,1942年5月死”。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叔叔,和父亲说的“13岁没了的弟弟”对上号时,她把辞职申请放在了老板桌上。 最初的调查比想象中难。1995年去哈尔滨参加731国际研讨会,王选想找日军投放细菌的证据,却只拿到几张模糊的老照片。 直到她通过共同社找到森孝正和松井英介,这两位日本和平人士掏出一沓调查笔记,里面记着崇山村村民说的“1942年飞机撒东西后,老鼠变多了”。 “那时候才知道,证据不在档案馆,在村民的嘴里。” 王选后来带着日本律师团跑遍浙江,在衢州江山,毛水达老人撩起裤腿,碗口大的溃烂伤口让年轻律师红了眼。 1997年在东京地方法院递诉状那天,王选特意穿了件深蓝色外,那是父亲生前常穿的颜色。 法庭上,日本政府律师说“细菌战是谣言”,她掏出村民画的“飞机撒药图”,还有《井本日志》的复印件。 那本日军参谋的日记里,明明白白写着“1940年11月,投鼠疫菌于常德”。 2002年一审判决下来,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细菌战事实,王选在电话里跟崇山村的乡亲说:“咱们没白跑,爹和叔叔的事,有人认了。” 诉讼结束后,王选把家变成了“史料仓库”,书架上摆着6册《日本生物作战调查资料》,那是她和日本学者花3年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抄回来的; 。 现在她最着急的,是12卷本的《战争时期浙江省境内的“烂脚病”分布调查报告》。 校对到金华部分时,她总会想起陈有升老人,老人说“牙床烂掉后,一辈子没吃过硬饭”。 2025年9月,林山寺侵华日军细菌战遗址馆开馆那天,王选站在“活体解剖室”复原展区前,墙上的投影闪过受害者的名字:王阿木、王樟木、毛水达…… 她突然想起1994年冬天,叔叔王焕斌说的“不能让他们白死”。 近30年过去,她从青丝变成白发,可每当摸到那些史料,摸到展馆里受害者的遗物,就觉得力气还在。 有人问王选,都73岁了,为啥还这么拼?她指着展馆里的一块粗布。 “你看这布,它记得老人80年的痛;这些书,记得村民说的每句话;这座展馆,记得那些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 王选说,她怕的不是自己老了,是这些“活着的证据”慢慢消失,是后人忘了“烂脚病”不是普通的病,是战争的伤。 受害者的苦难不能忘,这是王选们用半生时间,写给这个世界的“记忆说明书”。 信息来源:潮新闻2025-09-18发布:永不妥协的追问!73岁王选仍在调查细菌战真相:受害者的苦难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