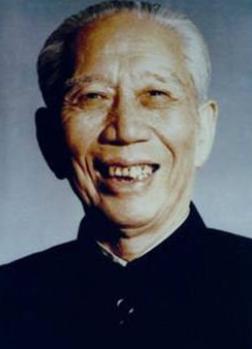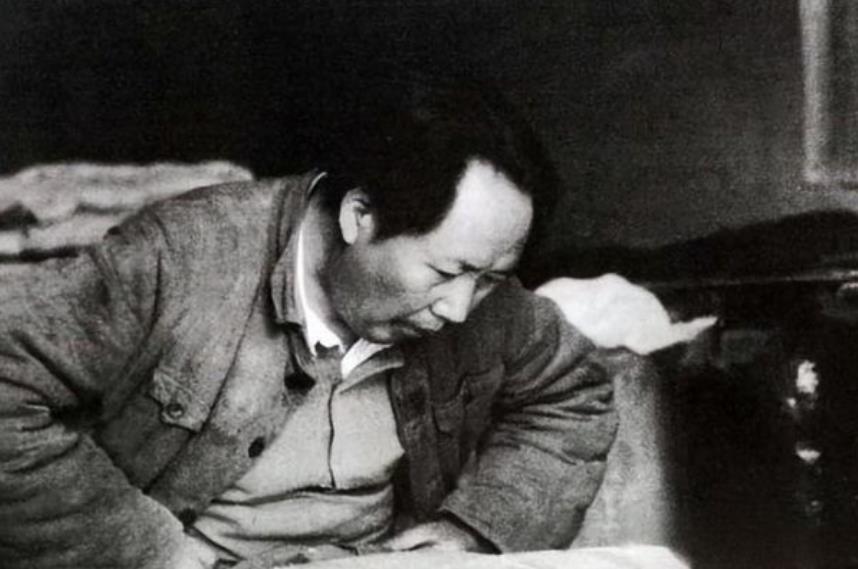这是1956年,陈毅夫人张茜手拿扇子,斜躺在树下椅子上休憩的老照片。 张茜那张照片,被说得很多。是一张1956年的照片,她坐在树下,靠着藤椅,手里摇着扇子,眼睛半眯,像是休息,也像是在想什么。那时候她的生活,才不像照片那么悠闲。你要知道,照片背后有多少的奔波与劳碌,多少个夜晚她一个人守着战友的遗稿,多少个清晨她强撑着身体,坐在桌前整理陈毅的诗。 她是汉口人,家境普通,也不算特别出色。1922年出生,家里人说她小的时候就有些不同,不安静,眼睛里总是有些急切的光。她喜欢唱歌,喜欢在舞台上站着,人群中的那个小小身影,从来不怯场。长大后,1938年,她去加入了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那时,战争的硝烟远远地笼罩着整个江南,没什么华丽的舞台,没什么正规的排练,很多时候就是拿着麦克风,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唱歌给那些疲惫的士兵听。 你想,那个时候,她多大?十六岁。她很年轻,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充满了理想,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路。她唱得好,演得也不错。台下的那些战士,每次她登场,都为她鼓掌,甚至笑得有点傻乎乎的。可就在那一场,她注意到了台下那个一直在鼓掌的男人——陈毅。 大家都知道他,当时的新四军司令,名气大得很。坐在那儿,穿着军装,眼睛里有着几分锐利。她下了台之后,悄悄打听,才知道,这位男人是个不简单的角色。不是单纯的将军,他不仅能带兵,还能写诗,还能做文章。听到这些,她心里立刻就有了那么一丝好奇。 后来的事情,就像很多故事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写信了,交流了,渐渐地,两人就有了更多的联系。张茜会写信,说些打心底的话。她写过一句:“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简单的几句话,却触动了陈毅的心,后来的诗里,他还特意引用了这句话。那时候,他们的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生根发芽,打破了战火的隔阂,成了相互支持的力量。 1940年,他们在一个简陋的指挥部里结婚。没有大操大办,也没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简简单单的一顿饭,几个战友就算是祝福了。结婚之后,他们的日子开始变得更加艰难。战争让他们几乎无法在一起,陈毅常常出征,张茜也忙着自己的工作,虽然心里想着对方,可是真的能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 有一次,陈毅因为黄花塘事件几乎气得摔门而去。他一度想离开新四军,那段时间他脾气暴躁,心里负担太重。张茜看在眼里,没说一句话。她就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给他倒水,递毛巾。她没有任何道理,只是陪着他。等到他终于平静下来,事情才慢慢过去。她那时候心里明白,很多时候,爱并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默默陪伴、用行动去支撑。 后来,陈毅进入了新中国政府,成了副总理,负责外交事务。张茜没有停下,她去学俄文,去充实自己。三十几岁了,重新捧起书本,每天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背单词、做笔记。别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学这么难的语言,可她知道,这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自己能在外交场合里更有话语权。 1956年,张茜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巴基斯坦,她被列为中巴友协的理事。她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手里拿着扇子,坐在树荫下的藤椅上,那时的她,似乎和很多忙碌的日子有些脱节。照片里她放松了一下,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身边没有人打扰,世界看起来很安静。可是你再想想,她身后的一切,都是从无数个飞奔的日子里走出来的。 她出国访问过不少次,二十次,三十次,去过十几个国家。每一次的出访,除了背后的政治任务,还得处理各种繁杂琐事。她常常在幕后默默工作,帮助组织接待、翻译,协调各方事务。她是外交场合中的坚强后盾,从不出风头,但却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存在。 生活里,她和陈毅也有过小打小闹。记得有一次,周总理请大家吃饭,陈毅喝了点酒,脸红了,眼睛有些迷离。张茜在桌下轻轻踩了他一脚,意思是别喝太多了。结果,陈毅大声叫了一声:“别踩我脚!”场面立刻变得轻松,周总理也笑了。那一刻,大家都看到了他们的亲密和默契,没什么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也没有什么背后的权力斗争,只有夫妻之间的小互动和人性的一面。 1972年,陈毅因病去世。消息一出,全国为之震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毛主席亲自到场,周总理哽咽着读悼词,刘伯承鞠躬到几乎无法站立。张茜站在台下,看着眼前这一切,眼泪没能止住。那一刻,她站得笔直,眼睛却没有离开过陈毅的遗体。那时的她,身体已经不行了,常常咳血,但她坚强得像个什么都不怕的人。 回到家,她一个人坐在陈毅的办公桌前,手指摩挲着桌面。房间里的灯光柔和,静得出奇。她没有哭出声,只有那些年,夫妻一起走过的岁月,在她心里浮现。就那样坐了很久,直到天色亮了,才轻轻说出一句话:“是该进入新的生活了。”这话说得不急不缓,就像她的心情,也平静得让人心疼。 张茜最终去世了,1974年3月。那时她才五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