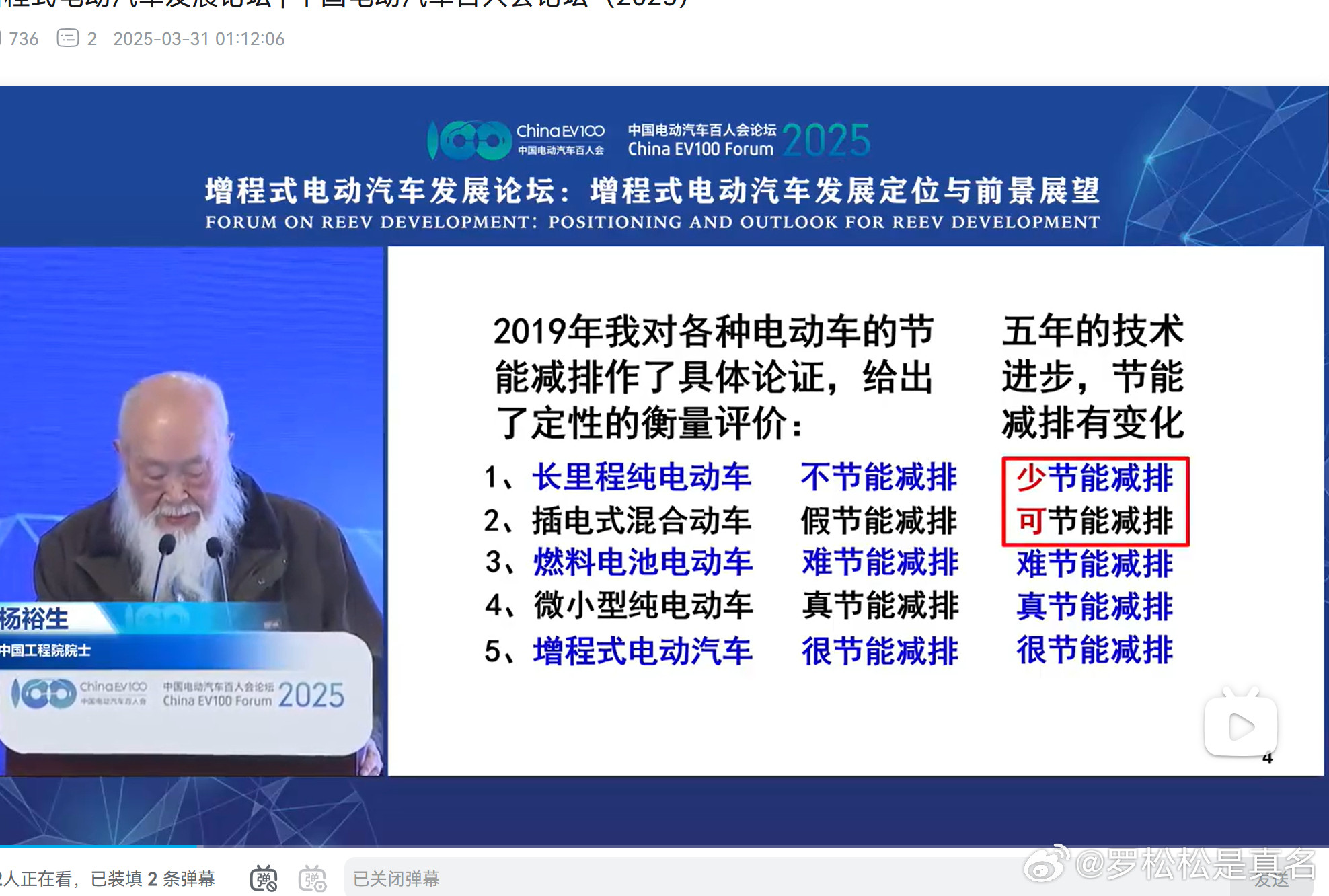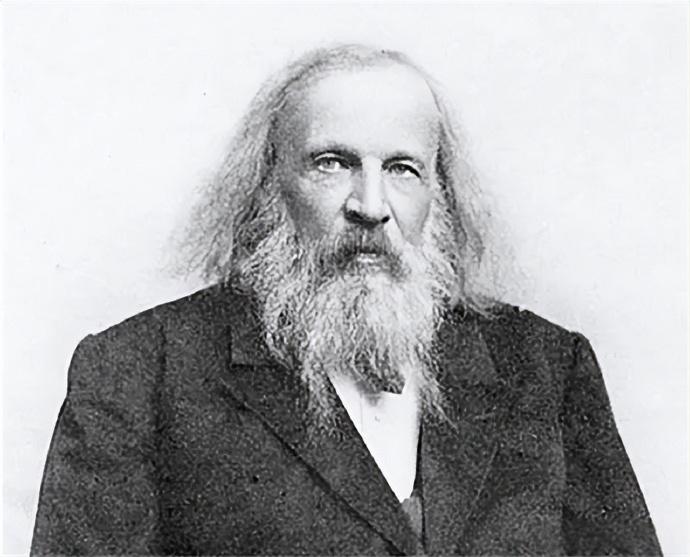缅怀! 核物理学家徐洪杰逝世,享年70岁。 9月15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发布的一则讣告,让科技界陷入惋惜,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钍基熔盐堆开拓者徐洪杰,于9月14日上午在上海逝世,享年70岁。 人们缅怀他时,多会提起上海光源和钍基熔盐堆这两项“国之重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徐洪杰留下的不仅是技术成果,更是一套能让科研事业延续的“传承体系”,以及一种跨越领域的“科研方法论”,这些无形遗产或许比具体装置更影响深远。 1995年徐洪杰接手上海光源建设时,国内同步辐射领域几乎没有成熟的专业团队。当时国际上做同步辐射的专家多集中在欧美,国内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寥寥无几。 徐洪杰没有等“现成的人才”,而是提出“边建设边培养”的思路,他从所里抽调物理、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年轻科研人员,组成“学徒式”团队,让每个人跟着国外专家参与具体环节,从磁铁调试到光束线设计,手把手带教。 52个月建成上海光源的过程中,这支团队不仅完成了工程任务,更成长为国内同步辐射领域的“种子部队”。 后来,这批300多人的队伍里,有人成了合肥先进光源的总工程师,有人牵头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探测器研发,还有人投身北京高能同步辐射装置的升级改造。 徐洪杰曾说“做大事要留种子”,上海光源的人才培养模式,后来成了中科院大科学工程的范本,这比52个月的世界纪录更具长远价值。 2009年转向钍基熔盐堆研发时,徐洪杰又把这种“传承思维”带到了新领域。当时钍基熔盐堆在国内几乎是“无人区”,他从上海光源团队里挑选了12名核心成员,再联合清华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材料、化学专家,组建跨学科团队。 不同于传统科研项目“各做各的”,徐洪杰要求团队每周开一次“跨界沟通会”,让核物理学家懂熔盐的化学特性,让材料学家明白反应堆的安全要求。 这种打破学科壁垒的做法,解决了钍基熔盐堆研发中的多个关键难题,比如熔盐腐蚀反应堆材料的问题,就是材料团队和核物理团队共同研发出新型合金才攻克的。 后来,这支团队逐渐壮大,形成了我国钍基熔盐堆领域唯一的“全链条研发梯队”,从基础研究到工程设计再到运行维护,每个环节都有能挑大梁的人。现在甘肃武威的钍基熔盐堆实验平台能稳定运行,正是这种“传帮带”体系的成果。 徐洪杰的科研方法论里,还有一个鲜明特点,“不追热点,只解真问题”。今年4月他在“报国讲坛”上说“中国人不能一直跟在别人后面”,这句话的背后,是他对科研方向的精准判断。 上世纪90年代,国内科研界更关注论文数量和短期成果,大科学工程因周期长、投入大,很少有人愿意牵头。 徐洪杰却认准同步辐射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设施”,坚持花15年做上海光源。 2009年时,全球核能领域更追捧三代核电技术,钍基熔盐堆因“离商业化远”被视为“冷门”,他却看到了其在安全性和核废料处理上的长期优势,硬是用16年做成全球领先。 这种“跳开短期利益看长期需求”的眼光,在当下追求“快成果”的科研环境中尤为难得。 更难得的是,徐洪杰能把一个领域的成功经验,灵活用到另一个领域。 上海光源建设中,他摸索出“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的协同模式,中科院出技术,上海市政府出土地和资金,国内企业参与设备制造。 这种模式后来被复制到钍基熔盐堆项目中,甘肃武威的实验堆就是中科院与甘肃省、企业共同投资建设的。 他还特别重视“用户思维”,上海光源建设时就提前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需求,预留了20条光束线,建成后很快成为“最忙的大科学装置”。 钍基熔盐堆研发中,他也提前和西北干旱地区的能源部门沟通,针对当地缺水特点优化反应堆设计,让技术更贴近实际应用场景。 这种“从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技术出发”的思路,让他的科研成果总能落地生根,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 现在人们谈论徐洪杰的贡献,常聚焦于钍基熔盐堆对“双碳”目标的意义,这种反应堆发电碳排放极低,核废料仅为传统核电的千分之一,还能利用我国丰富的钍资源,摆脱对铀资源的依赖。 这些优势的背后是徐洪杰团队16年里无数次的试错。比如为了找到适合熔盐环境的管道材料,团队测试了上百种合金,为了验证反应堆的安全性,他们在高温熔盐泄漏模拟实验中,连续值守72小时记录数据。 这些“看不见的努力”,才是技术突破的真正基石。 网友在缅怀徐洪杰时,有人说“他就像科研界的‘铺路石’,自己走最难的路,给后来人留平坦的道”。 确实上海光源培养的人才还在支撑更多大科学工程,钍基熔盐堆的研发团队还在向商业化目标推进,他留下的协同模式和科研思维,也在影响着更多年轻科研人员。 这种“让事业比人更长久”的追求,或许是对“科学家精神”最生动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