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女知青张菊芬热恋时,男友哀求说:“你就把自己交给我吧,我会对你负责!”谁料,事后不久,男友就抛弃了张菊芳,几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2010年的上海,秋阳透过梧桐叶在地上晒出光斑,张淑凤捏着那支钢笔站在纺织厂家属院门口。 笔身上“芬”字的刻痕被磨得发亮,像一道浅浅的伤疤。 三天前,她在讷河老家整理养母遗物时,从枕下摸出这个小东西。 养母临终前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找你妈去……上海……张菊芬……” 联谊会的老人翻到1969年相关名册时,指尖在某一行顿了顿:“张菊芬,上海和田中学,到黑龙江讷河县鲁民屯插队。” 旁边附着的登记照上,梳麻花辫的姑娘眉眼清亮,和镜子里的自己有七分像。 舅舅打开姐姐房门的瞬间,积灰的空气里飘着旧时光的味道。 书桌角落的铁盒子锈迹斑斑,里面一毛两毛的零钱用橡皮筋捆着,最大面额是1973年的五块纸币。 最底下压着张地图,讷河县鲁民屯的位置被红笔圈了又圈,老李家的院子标得格外清楚。 “你妈总说攒够钱就接你,可她怕……”舅舅的声音发颤,指着床头柜上的日记本。 1976年8月那页写着:“看见个扎小辫的姑娘追蝴蝶,应该是她。不敢叫,怕她跑。” 纸页边缘的泪痕已经发黑。 张淑凤突然想起十岁那年,王大娘颤巍巍塞给她块水果糖:“你妈托人带来的。” 当时她把糖扔在地上,喊着“我没有妈”。 现在想来,那糖纸该是上海的花样。 1970年腊月的鲁民屯,大雪把天地染成一片白。 村支书家西屋的油灯下,王大娘正把剪刀在火上烤得发红。 炕上的张菊芬咬着毛巾发抖,棉裤已被血浸透——三个小时前,有了可以回城的消息,她的名字在名单里。 “是个丫头!”王大娘裹起红通通的婴儿时,张菊芬的目光落在炕角的钢笔上。 那是上海家里给的东西,笔帽上刻着她的名字,此刻成了唯一能留下的念想。 来接孩子的老李媳妇把一篮鸡蛋放在桌上,看着襁褓里的小家伙直抹泪:“就叫淑凤吧,盼她顺顺当当。” 张菊芬把钢笔塞进婴儿衣襟,指尖触到温热的皮肤时,眼泪砸在蓝布襁褓上。 谁也没提之前的事。 那时她身体出现了变化,在田里总觉得不舒服,背后也有不少议论。 是村支书王大爷把她拉回家:“住西屋,让老婆子照看你。” 王大娘的小米粥里总藏着鸡蛋,夜里就着油灯教她纳鞋底:“娃出生得穿暖。” 那些日子,她总想起一个人,那个曾帮她干活、说过会好好对她的本地青年,后来却离开了,没了音讯。 1973年春,张菊芬坐着车回城时,怀里揣着王大娘连夜做的小棉鞋。 鞋面上的梅花绣得歪歪扭扭,针脚里藏着东北的霜。 她进了一家纺织厂,机器声从早到晚,她把工资的一半塞进铁盒,抽屉里的钢笔总在夜里发亮。 1982年托人带话想看看孩子,传回的话说“不想见”。 那天她把棉鞋摩挲到天亮,梅花绣线磨出了毛边。 日记本最后一页停在2004年冬:“疼得厉害,怕是等不到了。淑凤,要好好的。” 张淑凤在上海待了五天,带着日记本回了鲁民屯。 老李头拉着她往老槐树下走:“你妈常蹲这儿,看你跳皮筋就偷偷笑。” 王大爷家西屋还保持着原样,土墙上有模糊的刻痕:“她在这儿给你划身高线,说等回上海要带你吃红烧肉。” 站在当年母亲躲着看她的地方,张淑凤给女儿发了张钢笔照片。 风吹过稻田,沙沙声像极了多年前那个月夜,树叶替他们藏着的心事,终于在四十年后长出了形状。 她摸了摸笔身上的刻痕,突然明白有些思念从来不需要说出口,就像黑土地里的种子,隔着岁月也能发芽。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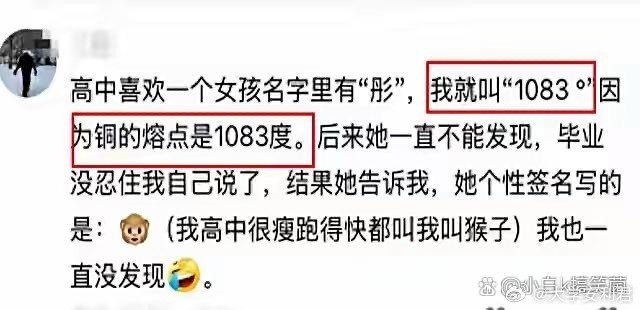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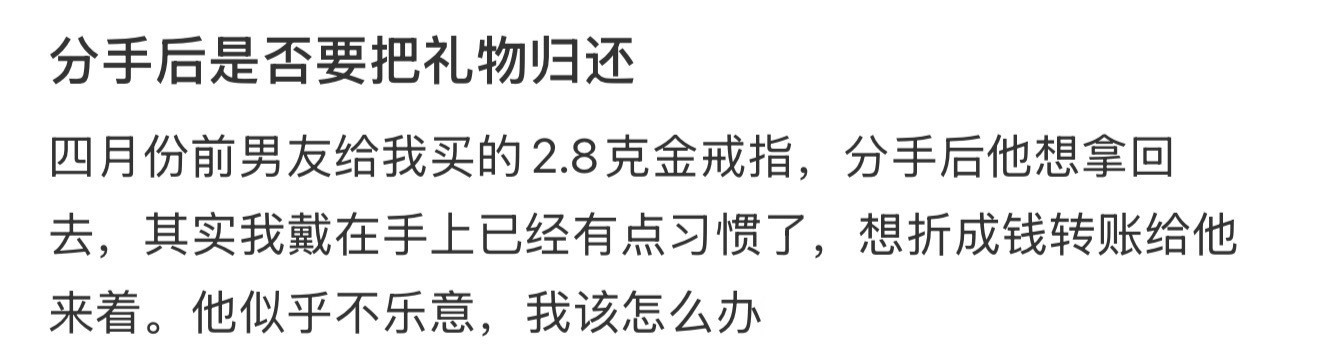
![“我想你了,暧昧一点要怎么说”[点赞]](http://image.uczzd.cn/2209033800927278044.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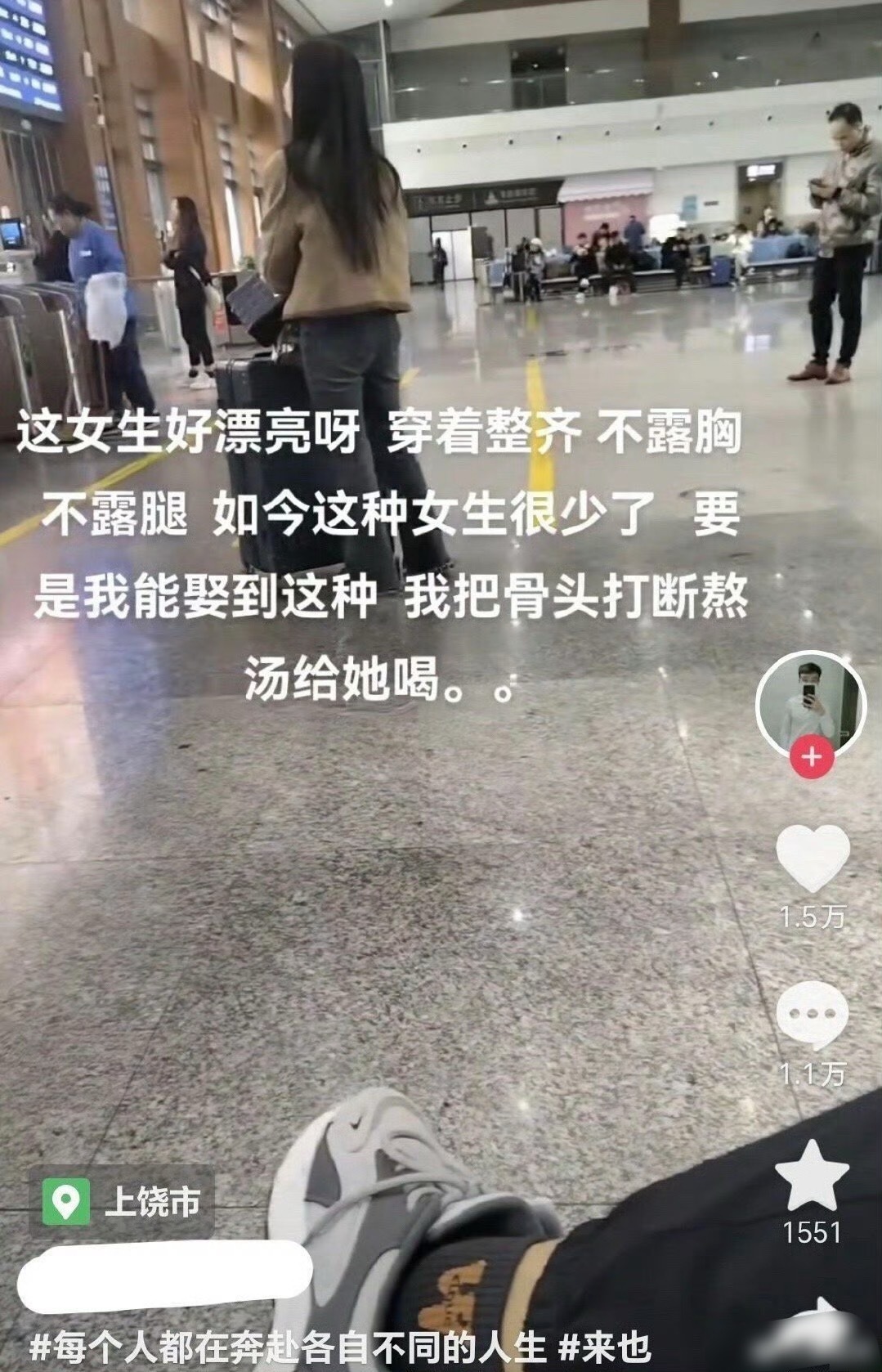
![你有遇到过这样的爱情吗?[玫瑰]](http://image.uczzd.cn/6400553449892559484.jpg?id=0)


智者荣耀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