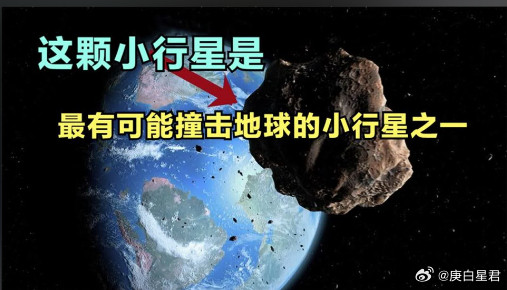他是国家用了11名美国战俘,才换回来的天才科学家,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他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就是著名航天技术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两弹一星”功勋——杨嘉墀(chí)。 飞机落地那天,天刚蒙亮,他拎着几只沉得发死的铁皮箱子,从舱门走下来,鞋跟在楼梯上咔咔响,像踩着某种倒计时。别人提着皮箱装衣物,他的箱子里塞的是高压电源、示波器、真空管,还有一沓用英文手写的技术图纸,箱子口缠着三层胶布,为了防止中途爆开。他脸色发白,一路上没吃几口东西,连飞机餐里的橙子都原封不动。 他走之前,在纽约郊区卖掉了带院子的房子和那台还能开的雪佛兰,邻居听说他要“回老家”,以为他不过是回去探亲几周。可他把花园里的铁艺秋千也拆了,说那玩意能当废铁卖钱。卖房那天,买主问他:“你回中国干嘛?”他盯着草坪上的狗啃骨头,没回答。 北京的实验室比他想象的还要穷。有人还在用铅笔手绘线路图,玻璃板上擦不干净的粉笔灰像积了十年的尘。仪器不够用,一个研究所排不上队就来借他的,有的机器要连轴转48小时,一出问题就来找他拆。他几乎没真正睡过整觉,枕头旁放着两把改锥,一个扳手,和一个掉漆的工具箱。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江苏吴江出生,父亲做绸缎生意,家境宽裕但从不铺张。他读交大那年,日军正炸虹口,他骑车过苏州河,有时能看到水面飘着尸体。他从不说那些事,直到晚年也没人听他说起过他在上海的遭遇。 1950年代他在哈佛实验室拿了博士,导师想留下他,开出一份年薪是中国教授五十倍的合同,还给了绿卡。他说不。他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我在这儿学的是技术,可心不安。”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封锁理工类留学生出境,他走不了,干脆一头扎进实验室研究,白天干活,晚上编资料,不跟人多说话。 等到1956年,国务院传来消息,说中美之间要交换战俘,顺带把“科技人”也算进去,他的名字在那张黄纸的第8行。他听说的那天正在校准一台高频振荡器,听完没说话,把台灯关了就出了门。别人问他去哪,他回头说:“回家。” 实验室分给他一间在旧庙里改的屋子,墙皮掉得厉害,一下雨就潮,电线从窗台上绕一圈才接上。他就在那里,带着那几口旧箱子重新拼出了一整套自动控制系统的雏形。后来有人说,那些仪器早该报废了,能修好的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制造商,另一个是杨嘉墀。 到了“东方红一号”发射那年,他负责的是姿态控制部分。没有电脑,他用算盘和纸笔,每个变量手动推导,一天最多算出几个公式,还得逐个验算。他把验算记录贴满整间屋子,外人看不懂,那些数字像咒语一样绕着墙壁转了一圈。他说:“不怕慢,就怕错。”发射那晚,他躲在角落里抠手指关节,广播里响起《东方红》时他没哭,眼镜片后却全是雾气。 1975年返回式卫星出问题,很多人慌了,他在角落里重新推了十几页演算,一直没说话。钱学森转头看他,他把纸递过去,说:“别改,按计划走。”那天晚上他一个人拎着望远镜上山,带了两瓶热水和一把破棉被,凌晨三点多,卫星按他算的轨迹从西北方向滑过去,像划火柴一样。 他后来还搞过假肢技术,唐山地震后没人指派他,他自己报名,说能让假肢“动起来”。用的还是他那套姿态控制理论。他把假肢当成微型卫星,一点点调节角度和反应速度,他说这是“人的备用系统”。 他80岁时还在写报告,每天早上七点半坐电梯上楼,连秘书都觉得过分。他说:“你工资发我一天,我就要干这一天。”他走路喜欢快走,说:“我得跑在时间前头。” 2006年他去世那晚,八宝山门口站满了人,有年轻的博士生,有退休的技术员,有人拿着他当年讲座用的投影图,纸都发黄了。 有一颗小行星,编号11637,现在叫“杨嘉墀星”。它绕太阳跑一圈要四年多,在火星和木星之间走一条不太起眼的轨道,就跟他一辈子一样。 知道他的人少了,但他做的东西,头顶那片天还在用。欢迎你留言,说说你第一次听说他,是哪年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