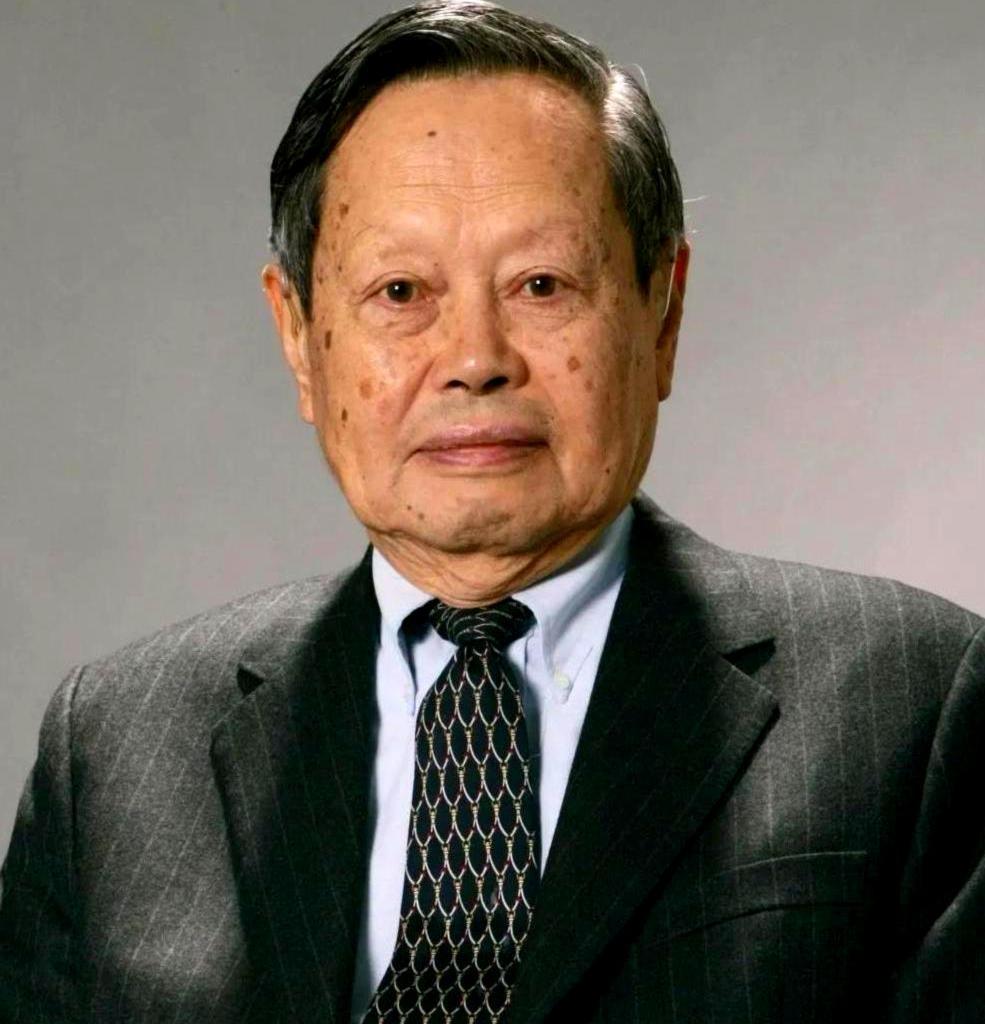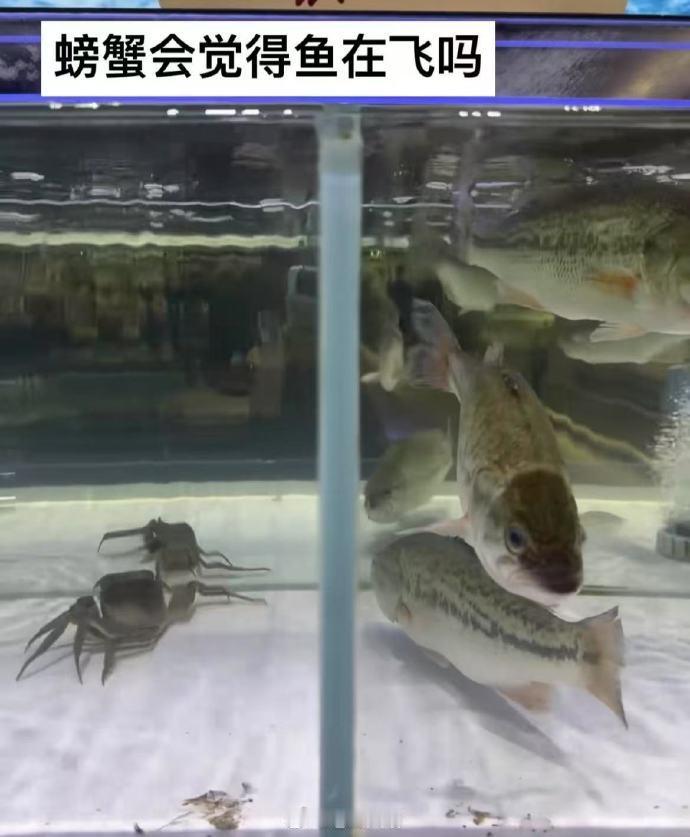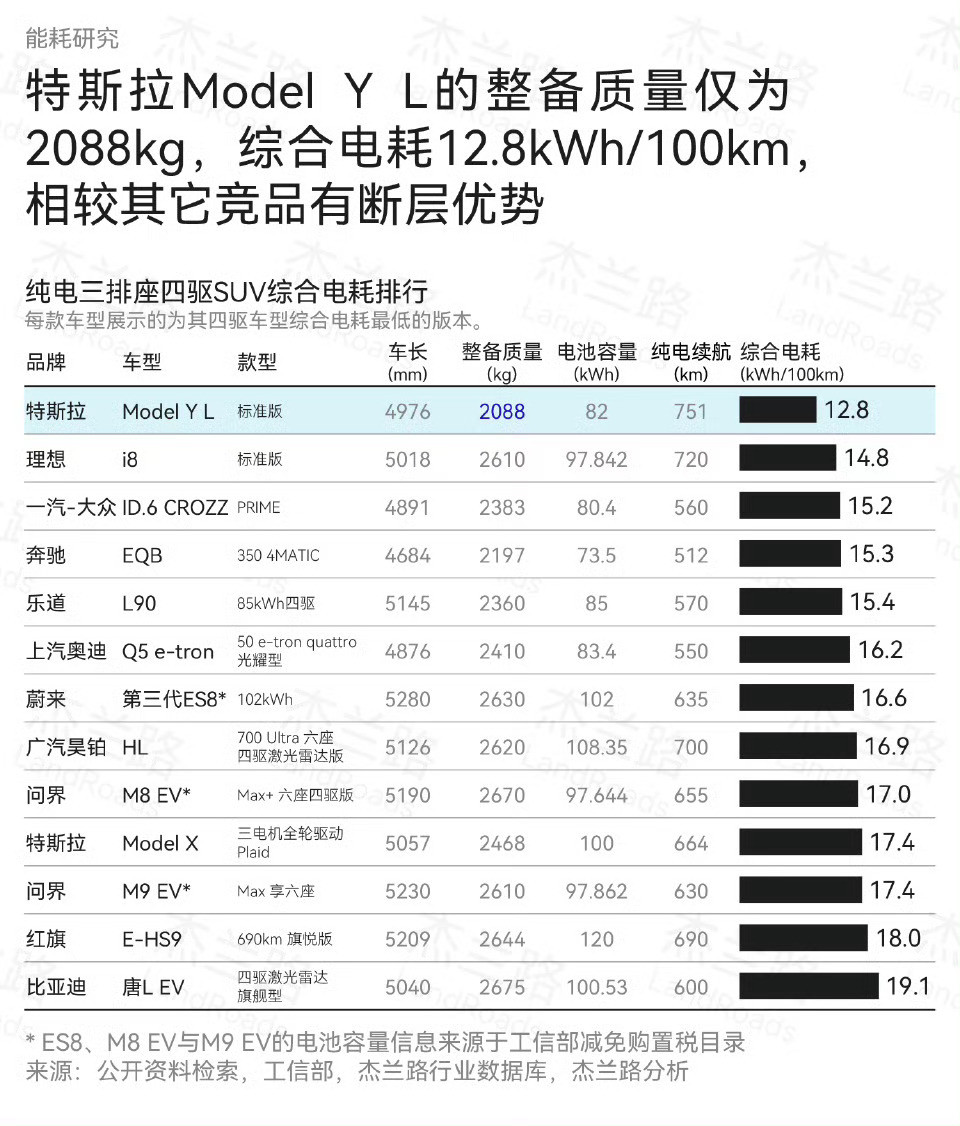2012年,杨振宁顶着舆论压力公开反对耗资2000亿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项目,这一举动直接激怒了中科院院士王贻芳,令其当场失态怒吼:"必须建造对撞机!否则中国科研将落后世界三十年!"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启之际,全球科技竞赛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消息源自:《中国科学报》2015年9月特稿《一票之差:中国对撞机计划背后的科学博弈》,《自然》杂志2016年3月期《东方实验室的十字路口》,以及王贻芳院士2019年在清华大学专题演讲《高能物理的中国路径》】 实验室的日光灯管在深夜依然亮得刺眼,王贻芳把第三杯浓咖啡推到旁边,电脑屏幕上的预算表数字已经模糊成一片蓝色光斑。这位53岁的高能物理所所长突然抓起橡皮狠狠砸向墙壁——橡皮弹回来时,他注意到上面印着"LHC"三个字母,那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缩写。 "王所,杨先生的文章又刷屏了。"助理小张捧着平板电脑站在门口,屏幕上正是杨振宁最新发表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王贻芳扯松领带,想起上周在香山科学会议上,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好比让小学生开航母,我们的物理学家队伍还没准备好。" 咖啡杯在桌沿晃了晃。"杨老,您当年在西南联大做研究时,用的可是比现在落后五十倍的设备。"王贻芳对着空荡荡的实验室自言自语。墙上的世界粒子物理实验室分布图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像个金色太阳,而中国的标记还只是零星几颗黯淡小星。 争论在2015年夏天达到白热化。某次闭门会议上,支持派的年轻教授拍着桌子吼:"欧洲人发现希格斯粒子用了三十年,我们凭什么不能赌一把?"反对派的老院士则抖着手里的报表:"这笔钱够建三百所希望小学!知道贵州山区..." 最戏剧性的时刻出现在9月16日的表决现场。中科院会议室里,11位专家面前的投票器闪着红光。前10票5:5平局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最后那位白发老人。杨振宁的拐杖在地毯上敲出闷响,他投下的反对票让显示屏最终定格在6:5。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后来有参与投票的专家在私下透露,"杨老最后说了句'别让中国科学家变成高级仪器操作工',这句话比所有数据都重。" 尘埃落定后,王贻芳的团队转向了更务实的方案。他们发现广东某处废弃矿井的岩层结构意外适合建造小型粒子探测器,这个被戏称为"地洞计划"的项目,预算骤降到原方案的零头。2018年冬天,当第一批暗物质探测数据传回时,研究组的小伙子们用实验室的液氮罐冰了啤酒。 "慢有慢的走法。"王贻芳某天深夜巡视实验室时,突然对值班学生说起他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的经历,"知道CERN餐厅为什么二十四小时供应牛排吗?因为他们建对撞机那三十年,总有科学家通宵工作。"学生看见所长摸了摸墙上那张泛黄的CEPC设计图,轻轻关上了储物柜的门。 如今走进高能所大楼,还能在走廊尽头看见当年论战的剪报。有年轻人问起那场着名投票,保安老李会指着杨振宁题词的"格物致知"匾额说:"瞧见没?这四个字重着呢,比两千亿还重。"而在三楼的某个办公室里,最新版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技术预研报告》依然静静躺在抽屉里,扉页上印着2025年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