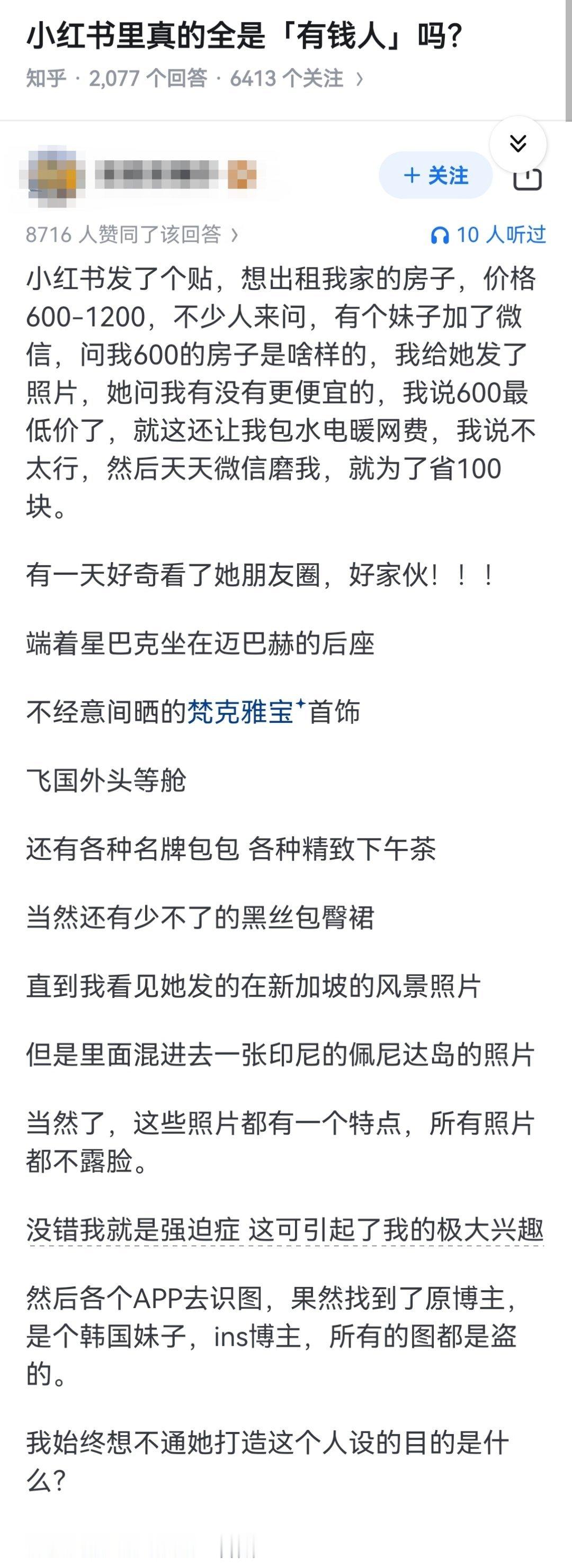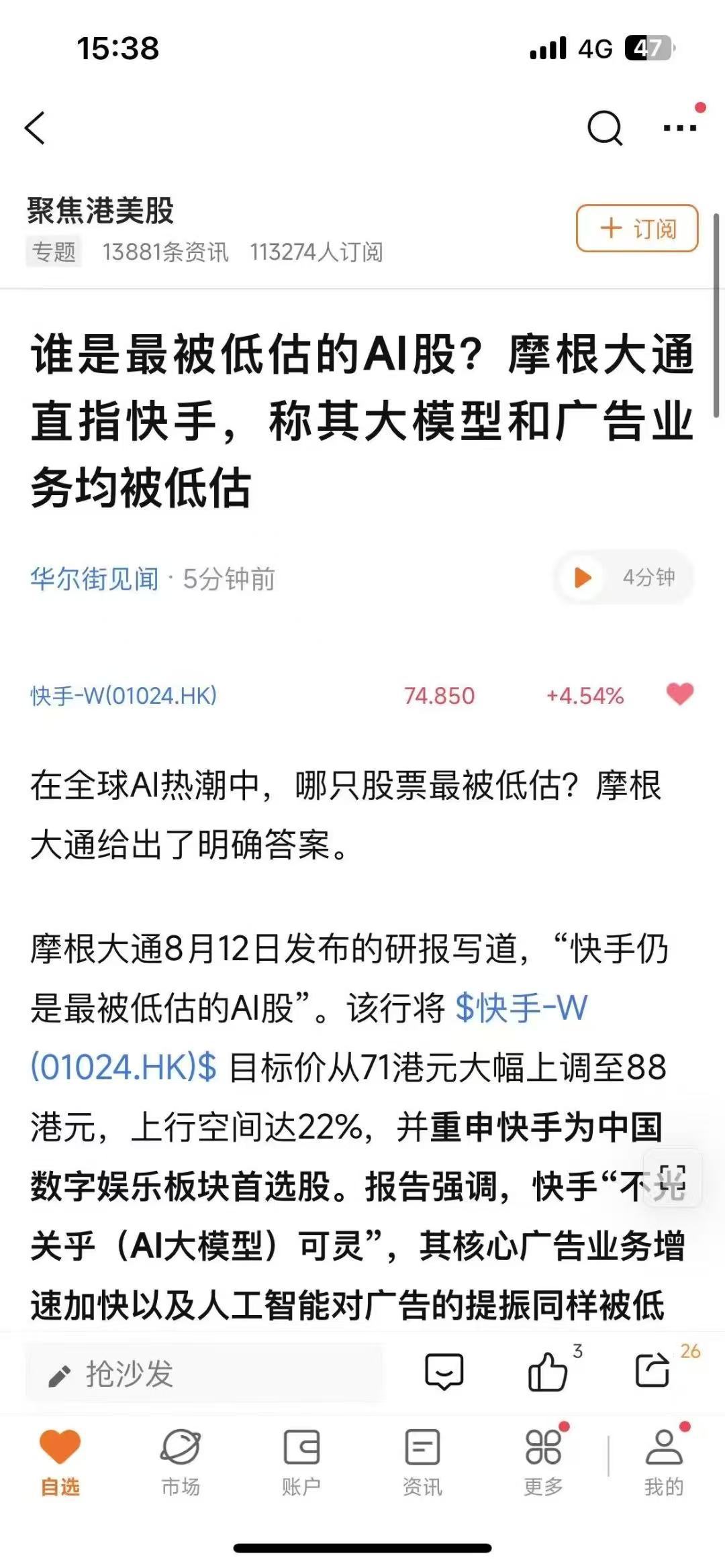我翻开手机,满屏都是“YYDS”“绝绝子”。突然刷到一条朋友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配图是凌晨三点的办公室灯光。手指一顿,文言文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上了便装混迹在我们的生活里。 古代中国一直运行着两套文字系统:精英阶层的文言文与底层百姓的白话文。科举考试清一色用文言文,普通百姓根本看不懂官府告示,得靠地方官用大白话解释才明白。这种割裂持续了上千年。 但转机在宋元易代时意外降临。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兴趣寥寥,公文常是蒙语混着汉语口语写成,白话文地位竟被抬高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更是带头写大白话诏书,白话文趁势冒头。 真正让白话文走进千家万户的,是明代书商和落魄文人。当江南丝织业繁荣造就大批有钱有闲的市民时,白话小说成了明朝人的“网络爽文”。《水浒传》《西游记》这些畅销书被福建建州的印刷作坊批量生产,书肆遍地开花。可别小看这些“通俗读物”,它们悄悄撼动了文言文的千年霸权。 但文言文真被拍死在沙滩上了吗?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白话文大旗”,胡适们高呼“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1920年教育部一纸命令,白话文正式挤进国民学校课本。 然而当我们今天说“总而言之”“闻过则喜”时,脱口而出的仍是文言基因。就像一位学者点破的,“文言不是死亡,而是戴了现代面具隐身幕后。” 有学者在研讨会上抛出一串问题:“雾霾仅仅是科学问题?瑞士钟表只是技术活?诚信无非伦理选择?”台下年轻人举着的手机亮成星海。他解析《大学》“止定静安虑得”六字真言时,现场有人喃喃:“这不就是专注力训练指南嘛!” 在人工智能呼啸而来的今天,儒家“仁爱”“中庸”思想反而成了稀缺资源。当算法不断推送信息茧房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老智慧,恰是击穿认知壁垒的利剑。 汉语教育专家看得透彻:“汉字象形文字从自然出发,即使万年后的我们,仍能通过文字触摸到自然与人的统一。”当孩子在诵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时,他们获得的不是过时的音节,而是中国人特有的生命韵律。 王小波被称作“白话文第一人”,高晓松说读他文字时心会漂浮,“始终保持在离地不高不低的地方”。这境界恰似文言与现代汉语的完美交融,文言是深扎大地的根,白话是迎风舒展的叶。 下次当你按下“社畜”表情包时,不妨想想“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孟子;用“摆烂”调侃时,耳边或许响起“朽木不可雕”的夫子训诫。文言从未离场,它只是借白话之口,继续讲述中国人永恒的生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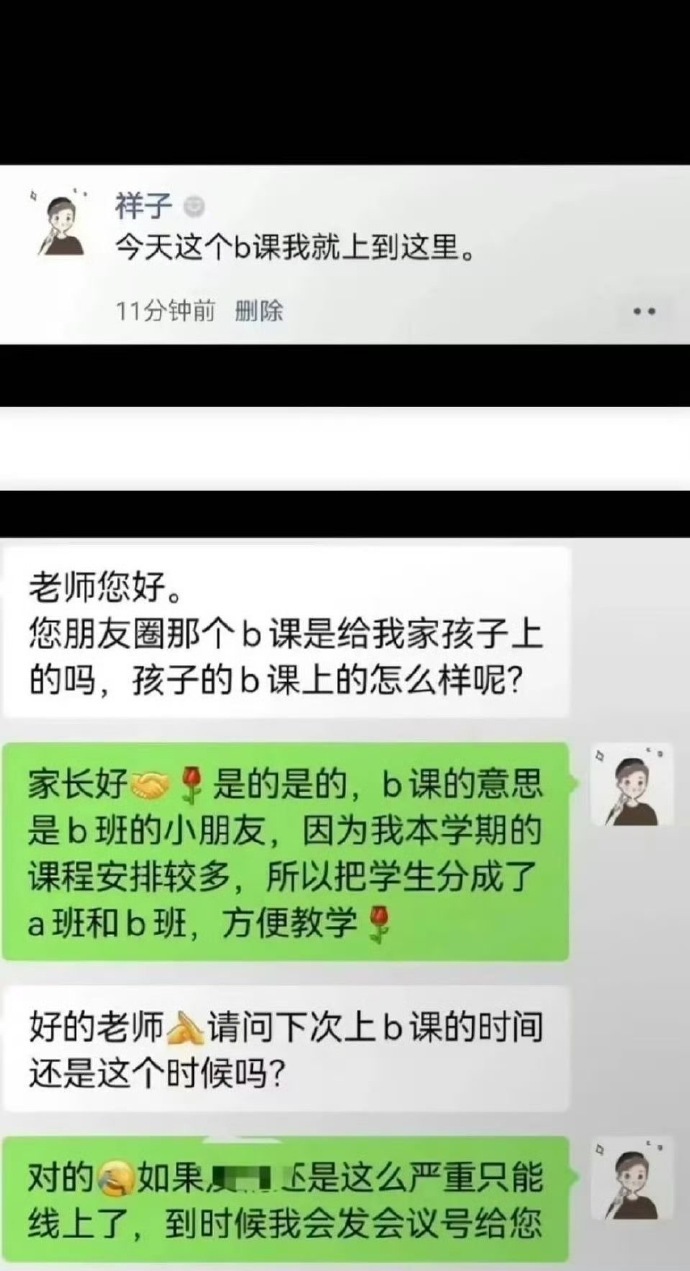
![网友的嘴从不让人失望[doge][doge]](http://image.uczzd.cn/17798010063588389441.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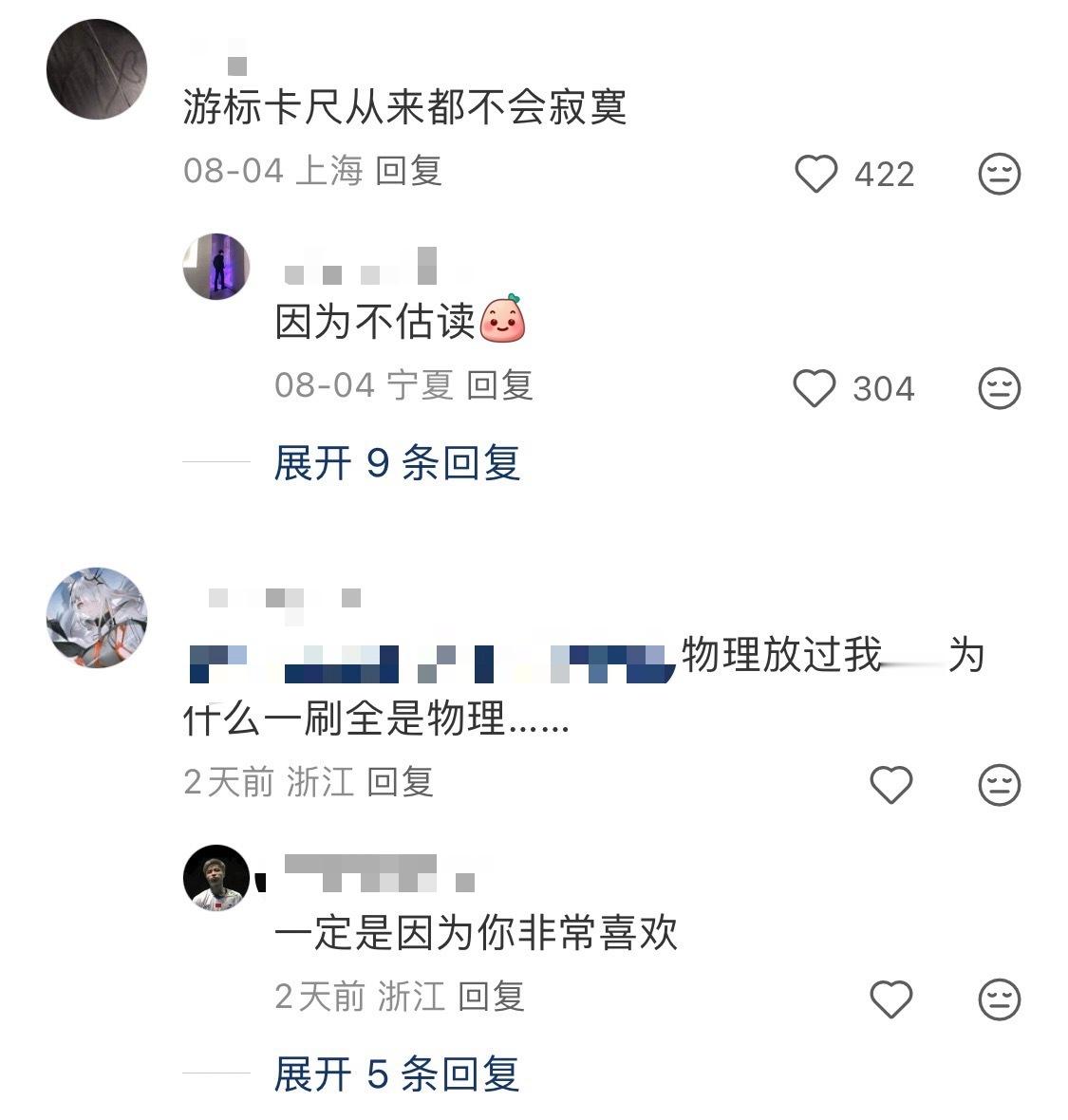
![吃个晚瓜,过于离谱了,售后权力这么大吗?[doge][doge][doge]科技数码汽场全](http://image.uczzd.cn/102708747344449769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