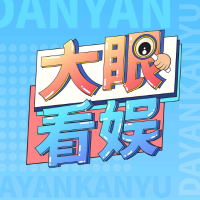2007年,“林黛玉”陈晓旭因病去世。这时,有人想让“贾宝玉”欧阳奋强来送“林黛玉”最后一程。谁知,欧阳奋强接通电话后,不仅没来参加葬礼,还直接关机。
济南片场的雨丝斜斜打在道具车上,欧阳奋强挂电话的手还在抖。
听筒里陈晓旭家人的哽咽声未散,导演已在喊他拍戏。
望着监视器里自己的古装扮相,他忽然恍惚——三十年前大观园里,陈晓旭总叫他 “宝玉哥哥”,说他笑起来眼里有星星。
而那个捧着手炉念 “葬花词” 的姑娘,再也回不来了。
消息传开,网络骂声铺天盖地。
“戏里情深似海,戏外薄情寡义”“连最后一面都不愿见”,评论像针一样扎人。
有人翻出宝黛诀别剧照,配文 “现实比戏凉薄”。
可没人知道,挂电话后他躲在道具车后,肩膀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
他与陈晓旭的交情,早已超越 “宝黛”。
1984年拍《红楼梦》时,两人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陈晓旭念黛玉台词时泪如雨下,收工后却偷偷往他口袋塞奶糖;
他镜头感差,她就举着小镜子教他:“眼睛睁大些,像受惊的小鹿。”
剧组都知道:“欧阳奋强的戏服口袋,永远有陈晓旭的零食。”
杀青后两人各奔前程,却从未断联。
陈晓旭转型做广告公司老板,欧阳奋强成了导演。
他每次去北京,必绕到她公司,看她穿职业装谈生意,笑称 “林妹妹成了女强人”。
2006年最后一面,他见她瘦得脱形、脸色苍白,反复叮嘱 “别熬夜”,她却笑说 “在忙大项目”。
后来他才知,那时她癌症已到晚期,只是不愿他担心。
接到葬礼通知时,欧阳奋强正在赶拍年代剧,剧组进度卡得死死的。
他冲进导演办公室:“我得去北京,陈晓旭走了。” 导演指着拍摄计划:“转场山东,每天赶三个景,走不开。”
查机票才发现,当天无直达航班,辗转到京至少两天,葬礼早结束了。
“请三天假,回来我通宵赶戏”,他几乎哀求,得到的答复只有 “不可能”。
那晚,他把自己锁在酒店房间。
媒体追问、网友谩骂、朋友不解,像乱线缠得他喘不过气。
拔掉手机卡的瞬间,他想起最后一次见面,陈晓旭站在银杏树下挥手:“宝玉哥哥,有空再来。” 那时叶子还是绿的,如今该黄了吧。
葬礼后第七天,欧阳奋强赶到北京参加追悼会。
他站在人群后排,望着照片里眉眼弯弯的陈晓旭,致辞时只说出一句 “晓旭,一路走好”,声音沙哑如砂纸磨过——太痛的时候,人反而哭不出来。
他后来在博客写道:“很多人说我薄情,可有些痛,不能拿出来晒。” 每年忌日,他都会发张剧组旧照。
有年发的大观园合影里,少年欧阳奋强穿红马甲,陈晓旭梳黛玉髻,背景桃花灼灼。配文只有一句:“三十多年了,桃花还在,人却散了。”
有人说,陈晓旭或许本就不愿他来。
那个戏里追求完美的林妹妹,怎会让 “宝玉哥哥” 看见自己被病痛摧残的模样?
她宁愿留在他记忆里的,永远是葬花时泪眼盈盈的少女。
正如欧阳奋强所言:“或许这就是命,戏里没能圆满,戏外也错过了最后一面。”
如今《红楼梦》已播出四十多年,每当 “阆苑仙葩” 的旋律响起,仍有人想起这对 “宝黛”。
欧阳奋强偶尔翻出当年的剧本,里面夹着陈晓旭的字条:“奋强,演戏要用心,做人要真诚。”
他懂,有些情义从不需要葬礼送别来证明,它藏在三十多年的牵挂里,在每年忌日的思念里,在那句没能说出口的 “再见” 里。
就像大观园的桃花,开了又谢。
见过那年春天的人会记得,曾有两个年轻人,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了彼此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