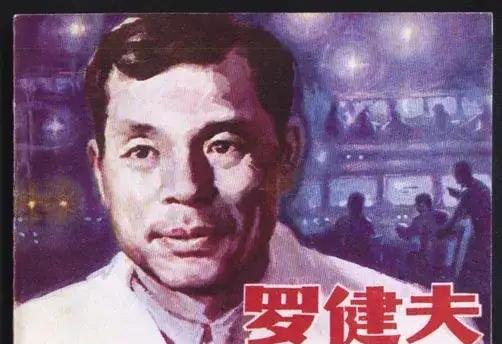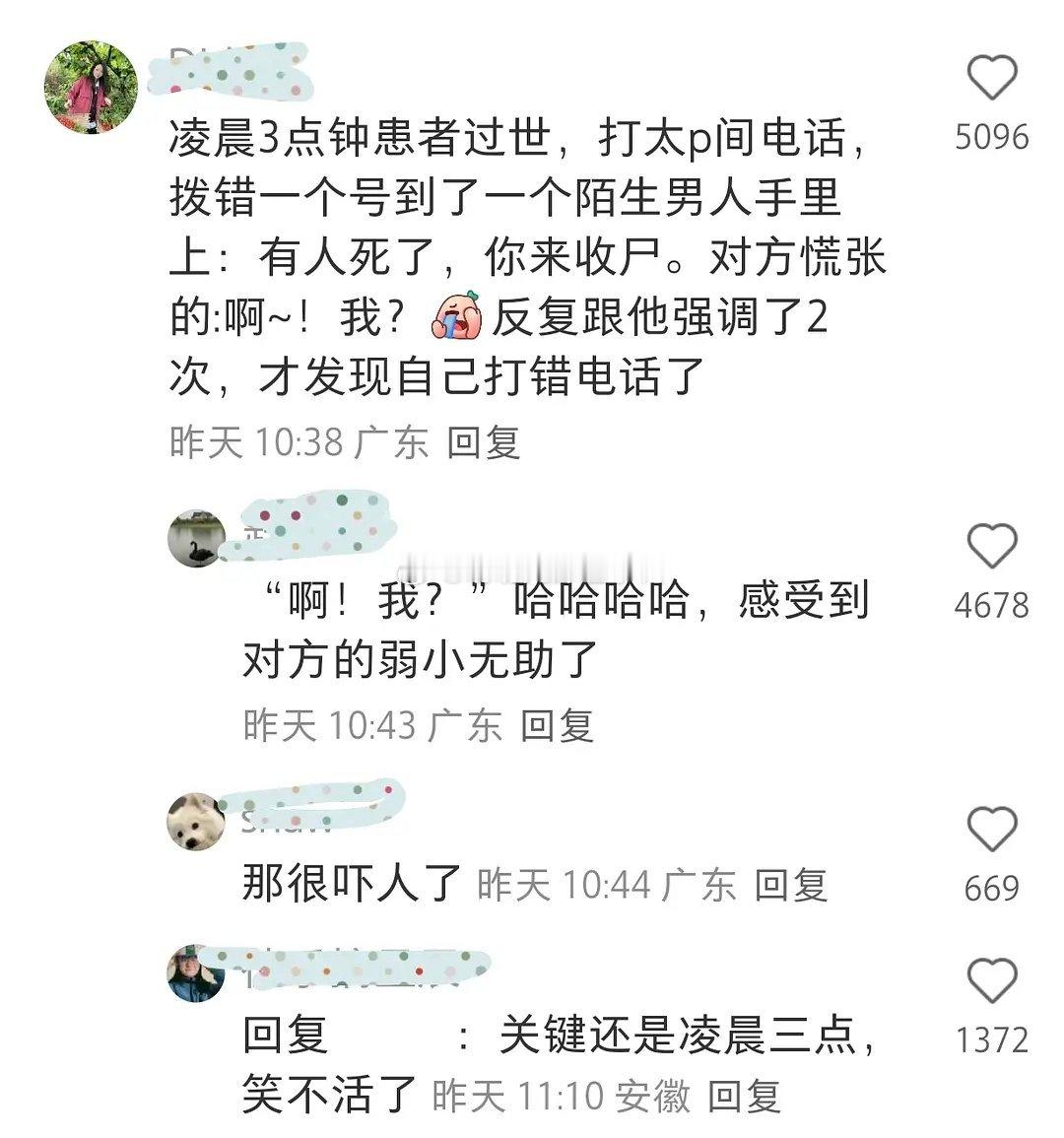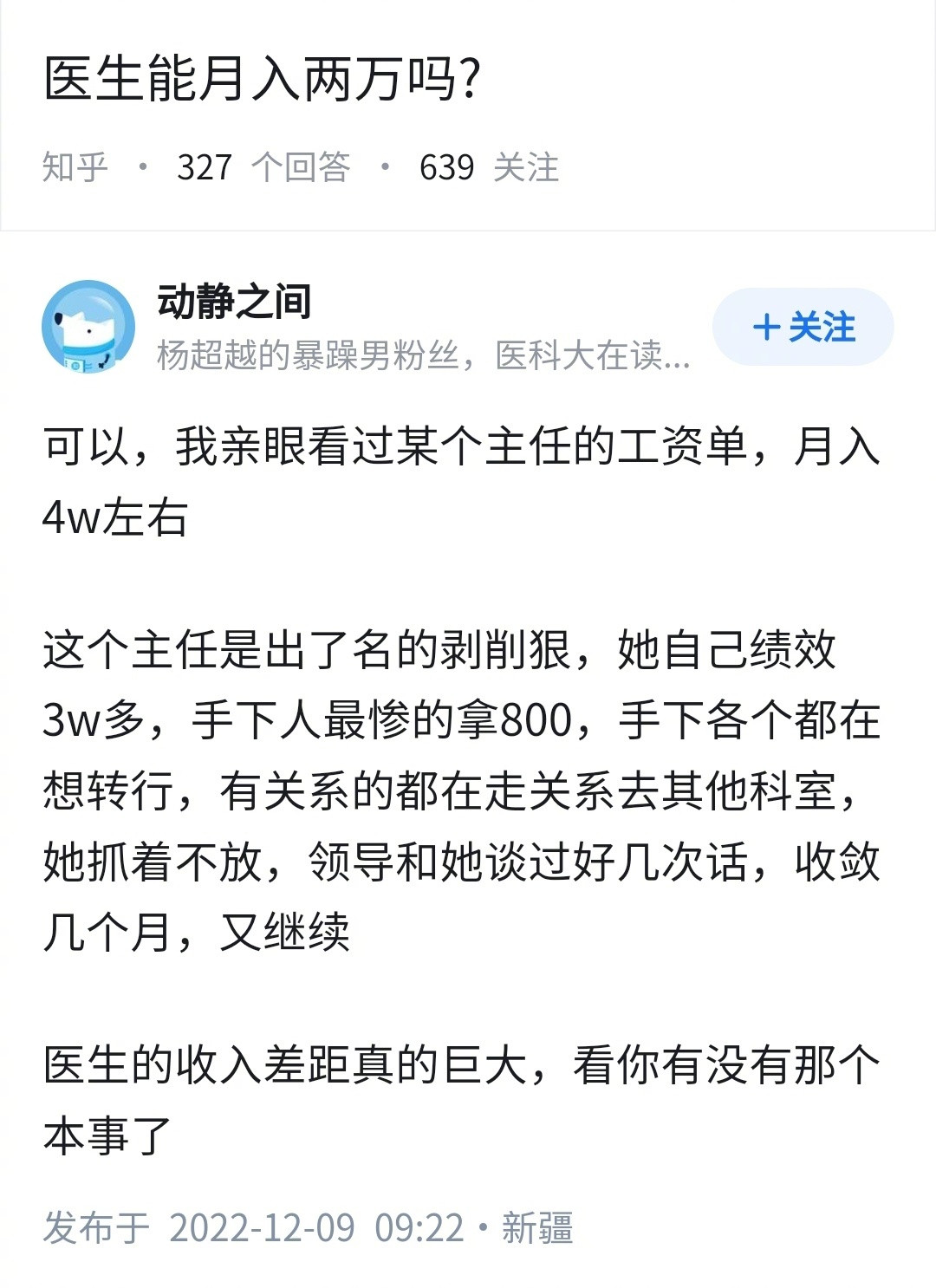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流泪。 没人能想到,这个被癌症吞噬的身体,竟支撑着中国航天史上最关键的科研攻关。解剖台上,医生发现他胸骨酥脆到“一碰就碎”,后背溃烂成片,低分化恶性淋巴瘤像藤蔓般缠绕全身,癌细胞至少潜伏了两年,而他直到生命最后四个月才被确诊。 更让人震撼的是,就在确诊晚期后的日子里,他白天捂着胸口做实验,深夜疼得蜷在工作室地板上,硬是把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电控设计全部完成。 时间倒回1970年,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那间简陋实验室里,罗健夫正面临双重压力:国际技术严密封锁,国内“文革”动荡未息。图形发生器是制造“航天芯”的核心设备,当时中国连张设计图都找不到。 他带着团队白天被拉去参加“思想改造”,夜里偷溜回实验室啃英文资料,一个俄语专业出身的人,硬是靠着惊人的毅力自学掌握了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等五门全新学科。 同事蔺振声忘不了那些画面:罗健夫口袋里总塞着冷馒头充饥,机器故障时直接躺在地上检修,棉袄袖口磨出破洞也浑然不觉。整整三年埋头苦干,中国首台图形发生器终于在他们手中诞生,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 当Ⅱ型机拿下1978年全国科学大奖时,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申报书最后一位;组织上两次要给他评高级职称,他摆摆手说“水平不够”;领导安排去香港考察的宝贵机会,他转手就把名额让给了年轻同事。 在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年代,他的个人生活更是清贫,全家挤在十几平米的旧屋里,顿顿离不开咸菜,该得的奖金分文不取。妻子想给他买件新衬衫,他指着旧衬衫上的补丁说:“这还能穿五年!” 1981年深秋,Ⅲ型机攻关到了最紧要关头。他胸口疼得直冒冷汗,却偷偷用伤湿止痛膏捂着,连朝夕相处的妻子都瞒着。 直到次年春节咳出血才被强行拖去医院,诊断书上“晚期癌症”四个字如同晴天霹雳。医生要求立即住院治疗,他却攥着病历本扭头就往实验室跑:“我的时间得论秒算了,课题等不起啊!” 癌细胞疯狂扩散时,他强忍着剧痛给同事写下详细的技术建议;刚经历完化疗的剧烈呕吐,立刻又摸出图纸修改参数。 护士们至今记得那个画面:他床头堆着翻开的《电子学理论》,被纱布裹着的手颤抖着还在做笔记。临终前三天,他拉着所长的手,用尽力气恳求:“遗体捐给医学研究,肿瘤这么大,或许能帮后人找出点办法……” 他走时年仅47岁,个人存折里只有82块钱,却给中国航天事业留下了三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争气机”。 如今在771研究所的大厅里,静静矗立着他的铜像。新一代的工程师们走过时,总会驻足凝视基座上的刻字,那上面写着:“他燃尽了自己的生命,点亮了祖国迈向星辰大海的征程。” 新华社权威报道:“罗健夫身处逆境仍投身科研,面对荣誉先人后己。他研制图形发生器的历程,是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的缩影。”(新华网《“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罗健夫》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