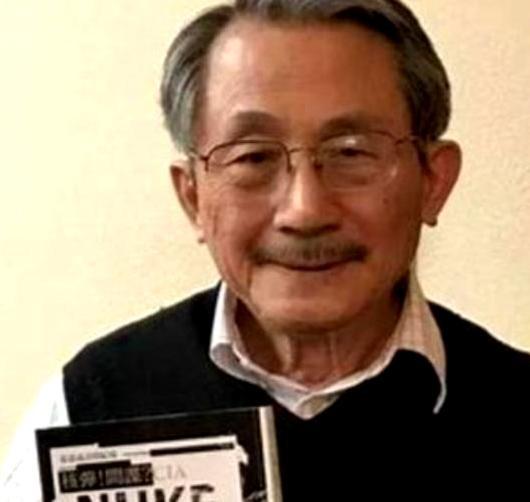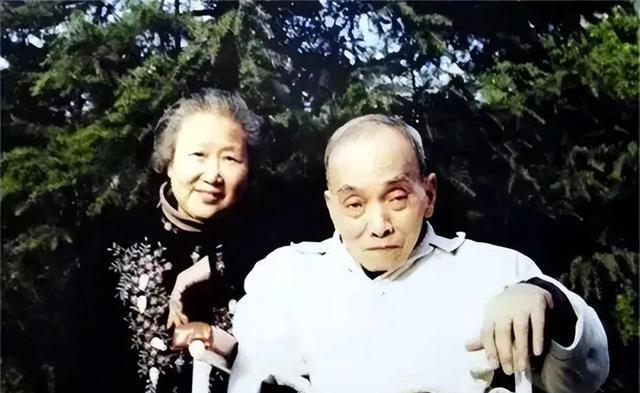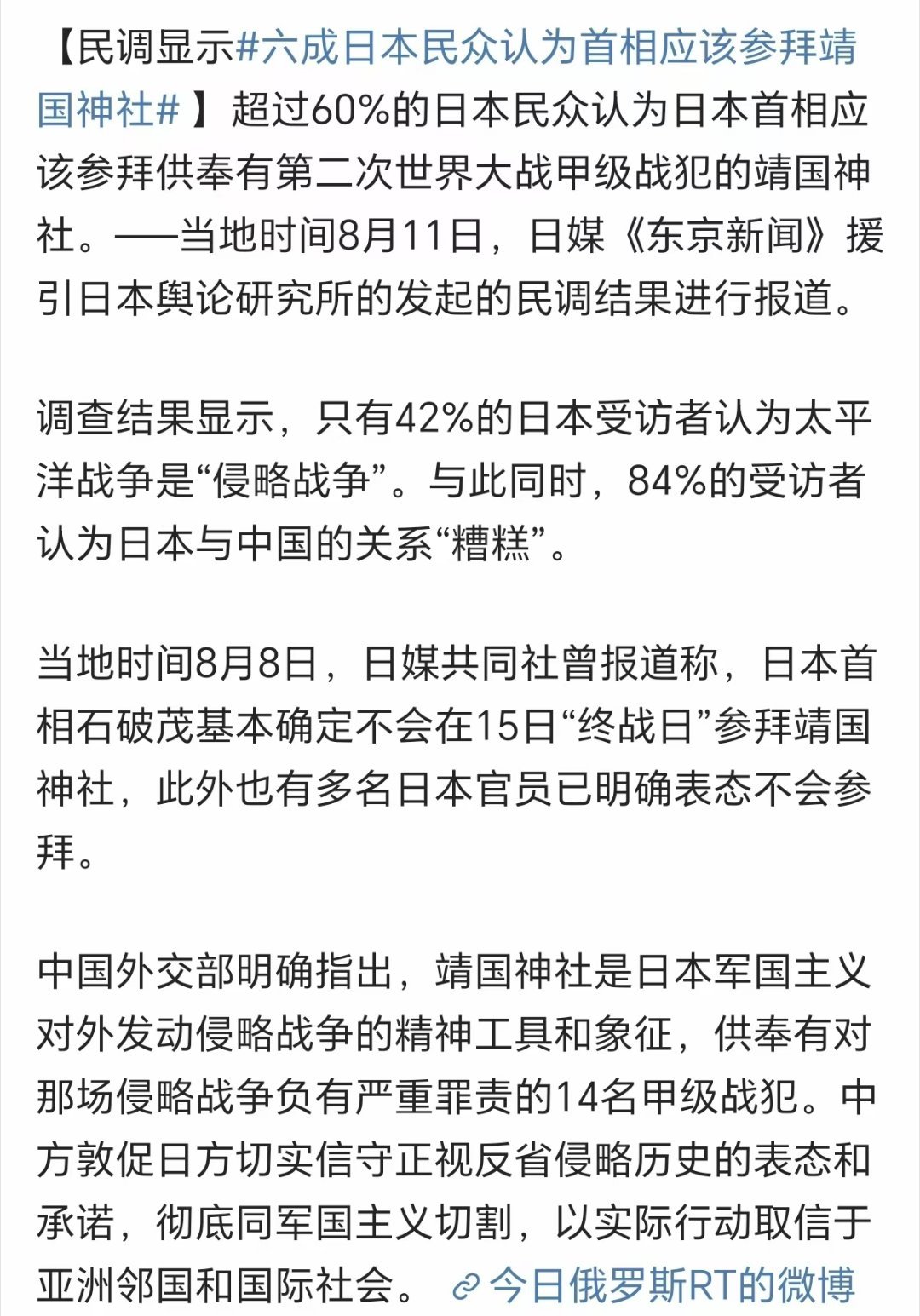1988年,核武专家张宪义怀揣原子弹机密叛逃美国,从此被打上"汉奸"烙印。面对铺天盖地的骂声,他选择销声匿迹。然而29年后,当这位"叛徒"再度现身时,舆论却陡然反转,无数人竟将他奉为民族英雄…… 【消息源自: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1988年台湾核武危机处置报告》(2011年部分公开);张宪义访谈录《我所知道的台湾核计划》(《亚洲周刊》2017年专访);中情局前官员回忆录《影子战争:冷战最后的秘密行动》(Simon & Schuster, 2019)】 1986年冬天,台北的雨下得又冷又密。张宪义站在核能研究所的窗前,手里攥着刚收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照片。那些扭曲的钢筋和溃烂的皮肤让他胃里翻腾,就像三年前在美国实验室里,李敏给他看南京大屠杀史料时的感觉。"老张,你脸色比反应堆的冷却剂还难看。"同事拍了拍他肩膀,"所长催那份钚纯度报告呢。" "马上好。"他推了推眼镜,抽屉里藏着昨天刚用显微相机拍下的燃料棒数据。这个动作他重复了十年,但今天胶卷的重量突然变得烫手。下班后他钻进巷子里的面馆,老板照例端来不加香菜的牛肉面——这是中情局联络员定的暗号,意味着安全屋有新指令。 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正在椭圆办公室争吵。"蒋经国这是要把航母开进瓷器店!"中情局局长把卫星照片摔在桌上,"他们上周试爆的常规炸药当量,正好是广岛原子弹的起爆触发器。"国务卿转动地球仪,台湾海峡在指尖下泛着蓝光:"我们给台湾的核反应堆,不是让他们煮茶叶蛋的。" 张宪义的公寓里,电视机播着蒋经国新年讲话:"...捍卫自由中国的决心..."画面突然跳成雪花,藏在收音机里的加密接收器亮了红灯。他拧开第三个旋钮,短波里传来《绿岛小夜曲》——这是紧急撤离信号。两天后他"偶然"接到国际原子能会议的邀请函,妻子往行李箱塞进五件衬衫:"多带点,波士顿可比台北冷多了。" 1988年1月9日的桃园机场,海关官员翻着他的护照:"张博士这次去几天?""五天。"他扶了扶眼镜,西装内衬口袋里,三卷微缩胶卷正贴着心跳。飞机爬升时,他看见核能研究所的穹顶在云层下闪着金属光泽,像颗蓄势待发的核弹头。 华盛顿郊外的安全屋里,中情局技术员用镊子夹出胶卷:"上帝啊,他们把钚239纯度提到了92%..."张宪义看着自己十年的研究成果在显影液里浮现,想起李敏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大陆放弃核电站钚循环?老张,有些路走上去就回不了头了。"三天后,美军特种部队降落在台中港,焊枪切开重水反应堆的外壳时,蓝光映亮了士兵防毒面具上的冷凝水。 台北的清晨,蒋经国把茶杯砸向晨报头版《美方强制拆除核设施》的标题。茶水浸透了张宪义的照片,那双温和的眼睛在茶渍里模糊成两个黑洞。而此时的波士顿,张宪义正盯着超市货架上的台湾罐头,生产日期显示它们来自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岛屿。收音机里主播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台湾地区已无武器级核材料。 二十年后,某个潮湿的夏夜,退休的张宪义在后院点燃烧烤架。火苗舔着美式汉堡肉时,邻居小孩举着学校作业跑来:"张先生,历史课要采访移民——您为什么来美国?"老人翻动烤架,油脂滴在炭上滋起青烟:"因为有人往厨房里藏了炸弹。""那您是...消防员?"孩子眨着眼。"不,"他递过烤好的汉堡,"只是个不想闻焦味的老头。" 台北故宫的解说员现在会这样介绍1988年:"...这一年我们失去了核武能力,但避免了成为亚洲的广岛。"玻璃展柜里,当年拆除反应堆的扳手静静躺着,标签上没写它曾被谁握在手里。而在太平洋另一端,张宪义总在牛排烤到五分熟时关火——这个温度不会产生任何致癌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