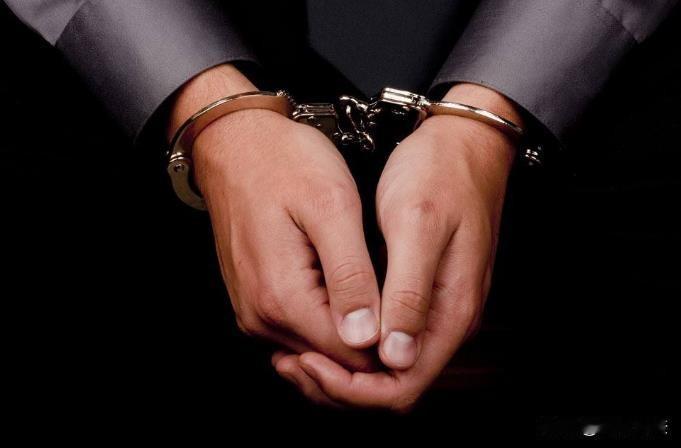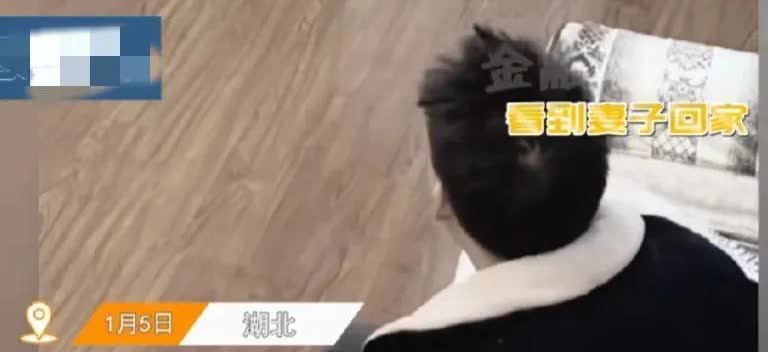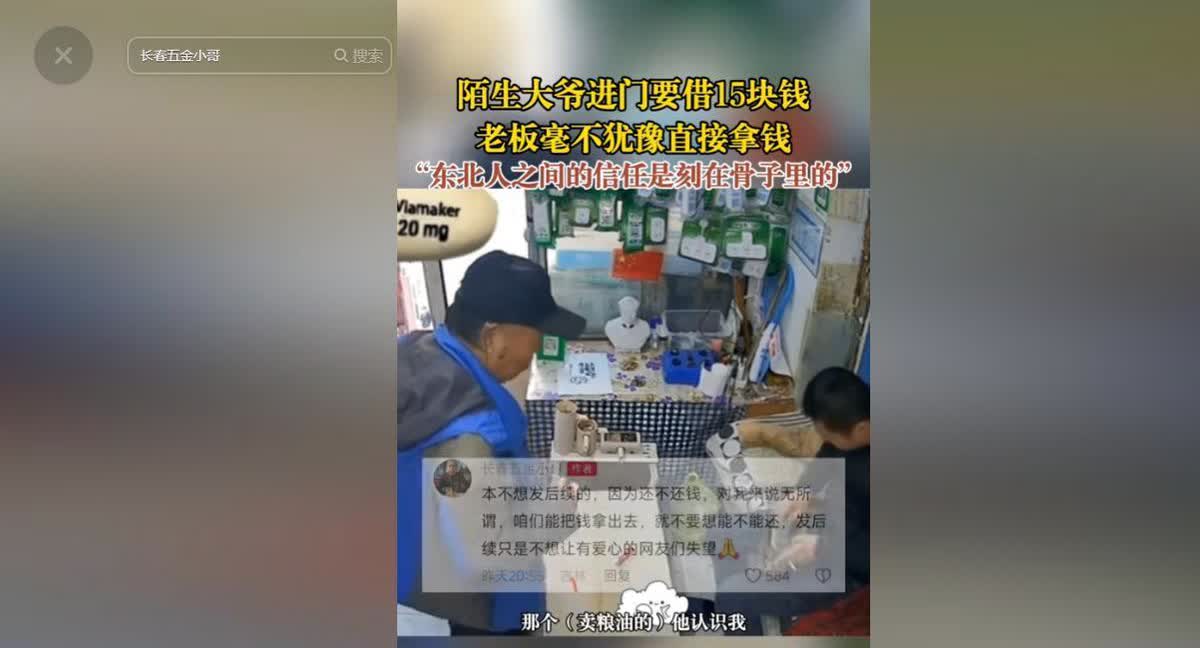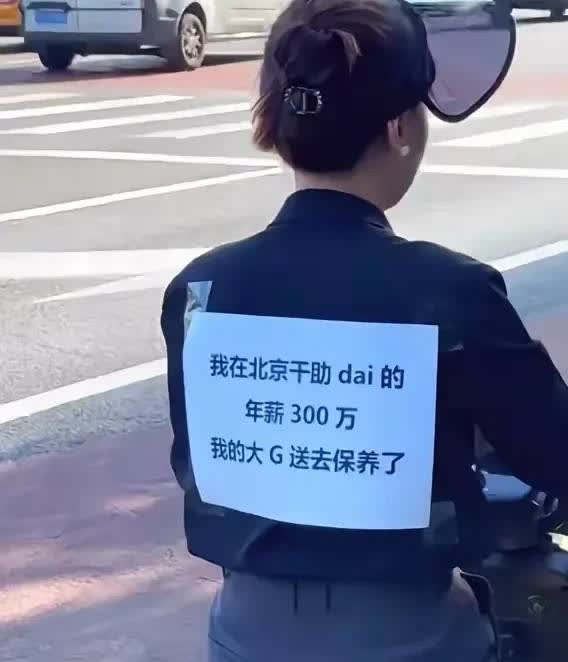南宋年间,宋理宗赵昀一觉醒来,发现搂着自己的女子又黑又瘦,气得他要处置女子。没想到女子接下来的一句话,让宋理宗顿时没了脾气。 龙涎香的烟气还在帐顶缭绕,宋理宗猛地推开身边的人,锦被滑到腰间时,他看清了那女子的模样——脸颊上有层薄晒斑,手腕细得像能被风折断,粗布内衣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这哪是宫里的人?他昨夜喝了些酒,明明记得拉进帐的是新晋的淑妃,那姑娘生得粉白,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来人!”宋理宗的声音带着宿醉后的沙哑,龙床的帷幔被他扯得哗哗响,“把这刁民拖出去,杖……” “陛下要杖死我,总得先看看这个。” 女子的声音不高,却像块冰锥扎进喧闹里。 她没跪,只是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解开,露出半块焦黑的麦饼,饼渣子簌簌往下掉。 宋理宗的话卡在喉咙里,盯着那麦饼发愣。 宫里的点心不是蜜糕就是酥酪,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糙的吃食,边缘硬得能硌掉牙。 “这是……”他皱眉,帐子晃得更厉害。 女子抬起头,晒斑下的眼睛亮得惊人,倒不像怕他,更像憋着股劲:“这是浙西灾民今天的早饭。” 殿外的宫人刚要冲进来,听见这话全僵在原地。 宋理宗的酒意醒了大半。 他想起上月浙西报了水灾,朝臣们在朝堂上说“已妥为安置”,还递上灾民领粥的画像,画里的人个个面有红光。他赏了负责赈灾的官员,转头就忘了这茬。 “你是谁?”宋理宗的声音软了些,指尖捏着帷幔的金线,线头刺得他手心发痒。 女子低头抹了把脸,露出胳膊上的几道划痕:“民女阿翠,是被抓来的。” 原来昨夜淑妃宫里的掌事太监,见皇帝醉了,怕淑妃伺候不好惹祸,又想讨个巧,竟从宫外抓了个“干净”的女子顶包。 阿翠本在临安城外给地主割稻子,被捂住嘴塞进马车时,手里还攥着给弟弟留的麦饼。 “陛下觉得民女黑瘦,”阿翠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可浙西的女子,十个里有九个比我还黑。去年大旱,今年大水,地里的苗全烂了,能有口焦麦饼填肚子,就算好年成。” 宋理宗望着帐顶的龙纹,忽然觉得那金线扎眼。 他想起淑妃昨天说新制的胭脂用了西域的珍珠粉,一小盒够寻常人家过半年。 他想起昨夜喝的酒,一壶抵得上十户百姓的赋税。 这些事,他以前从没细想过。 “淑妃呢?”他问,声音轻得像怕惊了谁。 门外的太监哆嗦着回话:“淑、淑妃娘娘……在偏殿候着,说怕扰了陛下安歇。” “安歇?”宋理宗笑了,笑声里带着点涩,“我在这里睡锦被,她在偏殿熏香,倒是都安歇得好。” 他掀开被子,赤着脚踩在冰凉的金砖上,走到阿翠面前。 这女子比淑妃矮半个头,肩膀窄窄的,却站得笔直,像田埂上倔强的野草。 “你刚才说,浙西的灾民……”他没说下去。 阿翠把麦饼重新包好,揣回怀里:“官府发的粥,掺了沙子,一天就一勺。民女的爹,上月没熬住,就死在河堤上,临死前还念叨着,说官家是真龙天子,总会可怜可怜我们。” “可怜?”宋理宗的指甲掐进掌心,“我连你们吃什么都不知道,谈何可怜?” 他忽然想起登基前,被权臣史弥远圈在府里,那时他也吃过粗粮,只是当了皇帝,就再也没碰过。 “陛下,”阿翠抬头看他,眼睛里没了刚才的硬气,倒添了点怯,“民女不是故意闯宫的,只是……只是想让陛下知道,外面的人,活得不容易。” 殿外的天光大亮,透过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格子影。 宋理宗挥了挥手:“放她出去,给她些银钱,送她回家。” 又对太监说:“把淑妃宫里的掌事太监拖去杖责三十,发去浣衣局。” 阿翠被宫人领着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一眼,那半块麦饼还在怀里鼓着。 宋理宗坐在龙床上,龙涎香的烟散了些,他忽然觉得这香气闷得慌。 他叫人把淑妃送来的胭脂、新酿的酒全搬下去,又让人取来浙西的赈灾卷宗。 卷宗上的字密密麻麻,写着“赈灾银十万两”“粮食五千石”,可阿翠说的焦麦饼,一个字也没提。 他忽然明白,那些官员递上来的画像,怕不是画的灾民,是画的他们自己想让他看见的“太平”。 那天下午,宋理宗下了道旨,让御史台去浙西查赈灾实情,又开了临安的粮仓,给城外的灾民发粮。 淑妃来请安,他没见,只让人传了句话:“以后别弄那些珍珠胭脂了,省下的钱,买点麦饼吧。” 没人知道阿翠后来怎么样了。 只听说浙西的灾民,那年冬天真的领到了不带沙子的粥。 而宋理宗的寝殿里,再也没烧过龙涎香,换成了最普通的艾草,说是“接地气”。 其实哪有什么突然没脾气。 不过是当皇帝的,终于从锦帐里探出头,瞥见了人间的真实模样。 那模样或许黑瘦,或许粗糙,却比任何龙涎香都更能让人清醒。 信息来源:南宋笔记《武林旧事》《宋史·理宗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