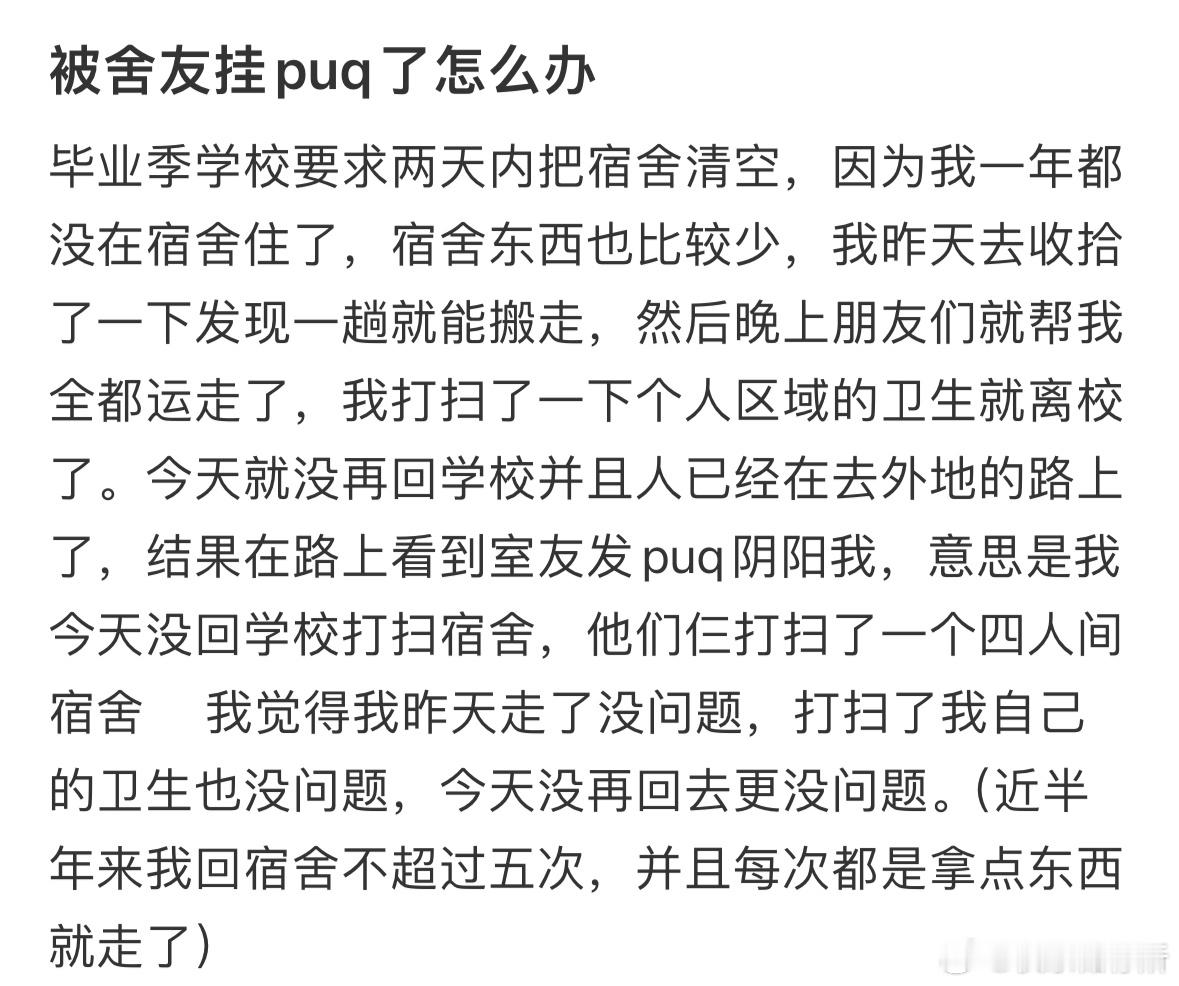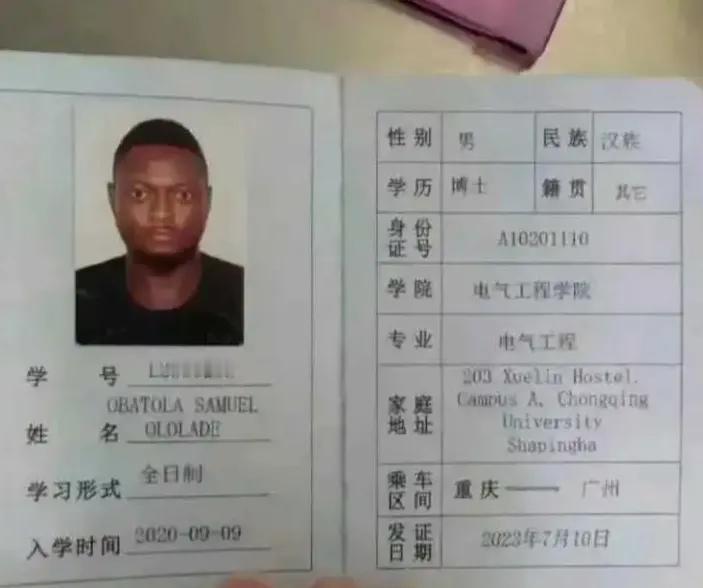有些反对莫言的人认为:莫言作品中对乡村愚昧、人性丑陋的刻画,容易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的 “文化标本”,从而强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观点认为,在中西文化话语权不对等的背景下,莫言的 “暴露” 式书写无意中成为了西方凝视下的 “他者叙事”; 而反对者则强调,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充当文化宣传工具,莫言以 “高密东北乡” 为支点的创作,本质上是对地方性经验的普遍性提炼,其作品中的苦难与救赎、欲望与克制,是人类共通的生存命题,不应被简单贴上 “民族性” 标签。复旦大学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社会中各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的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且客观的,不存在献媚、讨好的问题。 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管贻范是个性格刚强的人。这位在村里担任会计的老实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已经算是半个知识分子了。村里人都知道,管会计做事一丝不苟,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出了名的严厉。 莫言的哥哥管谟贤回忆说,父亲管教孩子的方式近乎苛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用最传统的方式来教育子女,稍有差错就是一顿打骂。这种教育方式不仅让莫言兄弟几个害怕,就连村里同辈的大人也对这位严厉的会计心存敬畏。莫言小时候天性活泼好动,自然没少挨父亲的责罚。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那次偷萝卜的经历。那年头粮食紧缺,小莫言在地里干活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偷拔了个萝卜充饥。结果被生产队的人发现,罚他跪着认错。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抄起家伙就要往死里打,要不是六婶及时把爷爷请来,后果不堪设想。 这段经历给莫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他在创作中多次提到这件事,还专门写过一篇《狼一样的反叛》的散文。文中他表达了对敢于反抗父母权威的孩子的敬佩,特别提到了鲁迅先生对父亲们需要接受教育的呼吁。最让莫言印象深刻的是邻居家一个四岁的小男孩,那孩子在挨打时不仅不屈服,反而像狼一样反抗。被父亲踢倒后,这孩子抓起地上的沙土就往自己嘴里塞,呛得直翻白眼。这个举动把大人都吓坏了,从此再也不敢打他。每次见到这个孩子,莫言都会肃然起敬。 与父亲的严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亲的温柔宽容。莫言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从不打骂孩子,总是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担。在莫言因为长相被人嘲笑时,是母亲的开导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在他因为"懒惰"被父亲责骂时,是母亲的理解给了他安慰;在他因为贪吃惹祸时,也是母亲的包容让他感受到温暖。更重要的是,母亲是莫言最早的听众,总是耐心地听他讲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从不打击他的想象力。 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让莫言对她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他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这种渴望后来转化成了他当作家的动力。心理学研究表明,像莫言母亲这样充满爱心、懂得理解孩子的教育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心理韧性。正是母亲的鼓励和支持,让莫言逐渐建立起自信心,学会用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可以说,莫言后来能够成为作家,与他特殊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父亲的严厉让他学会了在逆境中坚持,母亲的慈爱则给了他创作的动力和信心。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教育方式,却在莫言身上形成了奇妙的平衡。一方面,他渴望通过写作获得母亲的认可;另一方面,父亲的严格教育又培养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正是这种"严父慈母"的家庭教育,塑造了莫言独特的性格特质,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学王国。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创造的"马孔多镇",这些虚构的地理空间不仅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根据地,更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熠熠生辉的坐标。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文学地理版图同样精彩纷呈: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李锐描写的吕梁山脉,阎连科虚构的耙楼山脉,毕飞宇塑造的王家庄,以及莫言创造的"高密东北乡",都成为作家们独特的文学标识。 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曾精辟地指出,伟大的小说家都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既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因其内在的逻辑自洽而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魔力的文学世界。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远离现实的虚构空间,但实际上,作家从未真正逃离历史和现实的羁绊。相反,这个文学世界承载了更多沉重的命题:战争的残酷、人性的复杂、欲望的挣扎、孤独的煎熬、饥饿的痛苦、生命的顽强......这些沉重的主题让"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空间显得格外厚重。